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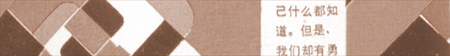 |
|
|
|
|
|
|
|
|
|
||
|
三、清谈之方式 (四) 口谈与佛家“讲经之制” 上文所引《世说新语·文学》五五,以“盛德”称支、许、谢等名士,显然是佛家的口气,这可能与《世说新语》的编纂者刘义庆笃信沙门有关;而在清谈方式上,东晋名流也已吸取了僧徒讲经的方法。《世说新语·文学》五七: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 所谓“唱理”,即发出论题,以便讨论。这种说法正源于内典。《高僧传》卷一三《唱导·“论曰”》: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 慧远“躬为导首”之时,已近东晋之末,王修、僧意早于他,故不会受其影响。但僧意是佛教徒,他对“唱导”之法不可能一无所知,“使其唱理”一语,便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当时玄学与佛学已逐渐交融,故唱导之内容不仅有“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的成份,也有玄学、清谈的因素。裴頠《崇有论》“唱而有和,多往复返”(《全晋文》卷三三),亦指“唱理”而言。《世说新语·文学》四0: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 “都讲”之称,后汉即已有之。《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鸿年十三,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此“都讲”指主讲学舍的人。新版《辞源》(页3112)释云:“魏晋以来,佛家讲经之制,开讲之时,以一人唱经,一人解释,唱经者谓之都讲,解释者谓之法师。”“都讲”、“法师”属于佛家“讲经之制”,但支、许是在谈玄(下文云“不辨其理义之所在”一语可证),显然佛门“讲经之制”已渗透到清谈之中,亦可视为一种“谈玄之制”(参见本书页105)。这种情况的产生并非偶然。当时名僧与名士交往频繁(参见孔繁先生《从〈世说新语〉看名僧和名士相交游》),名僧学习玄理,名士亦读佛经,乃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世说新语·文学》二三: 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 殷浩认为佛理与玄理是相通的。在东晋的清谈名士中,殷浩在沟通玄、佛方面贡献是很大的。除殷浩外,清谈名士研读佛经者还有王珣、王珉和王坦之等人,但他们的佛学造诣都不如殷浩。玄学在东晋时代达到鼎盛,因而也就逐渐成为一种封闭的体系,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勃勃生机。殷浩等名士迅速、及时地接受和吸纳了佛学这种外来的异型文化的营养,从而为玄学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支遁(314~366)是佛门中的玄论大师。他在勾通玄、佛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可以和殷浩并驾齐驱的(参见本书页105)。东晋末年的慧远(334~417)大师也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佛学巨子。《世说新语·文学》六一: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本条刘孝标注引张野《远法师铭》曰:“沙门释慧远,雁门楼烦人。本姓贾氏,世为冠族。年十二,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学,道阻不通,遇释道安,以为师,抽簪落发,研求法藏。释昙翼每资以灯烛之费。诵鉴淹远,高悟冥赜。安常叹曰:‘道流东国,其在远乎?’襄阳既没,振锡南游,结宇灵岳。自年六十,不复出山。名被流沙,彼国僧众皆称汉地有大乘沙门,每至,然香礼拜,辄东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终。”又引《东方朔传》曰:“孝武皇帝时,未央宫前殿钟无故自鸣,三日三夜不止。诏问太史待诏王朔,朔言:‘恐有兵气。’更问东方朔,朔曰:‘臣闻铜者,山之子;山者,铜之母。以阴阳气类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钟先鸣。《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应在后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书言山崩,延袤二十余里。”及《樊英别传》曰:“汉顺帝时,殿下钟鸣。问英,对曰:‘蜀
山崩,山于铜为母,母崩子鸣,非圣朝灾。’后蜀果上山崩,日月相应。”慧远与殷仲堪讨论的是《周易》的本体问题。他的“以感为体”的思想即来源于佛家的感应理论。他曾以心的感应来说明三报先后之不同: 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感事而应。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三报论》,《全晋文》卷一六二) 在他看来,人是通过心灵来感受报应的,心要受到事物的感召,对事物有所感受,才有反应活动,感应有迟速,报应也就有先后。远公以佛理阐释玄理,以此为佛学争地位,其他名僧如康僧渊、于法开等人也都曾致力于玄、佛的沟通。在名士与名僧的共同努力下,玄学与佛学渐趋融合。在这种情况下,佛家“讲经之制”渗透到清谈之中,成为清谈家广泛采用的清谈方式,当然也是意料中的事。
|
国学网站,版权专有;引用转载,注明出处;肆意盗用,即为侵权。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2917824
010-62917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