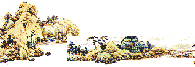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Ƴ��¶��ˡ� �����ְ����ƴ����ˡ� ������·�ڵ���һ�����£����˼���������˼�����ĭ���ȵ��ļ�����Ҳû�ȵ�һ��Ը�������Ů�ˡ����죬����������ȵ��������ˣ�Ҳû�ŵ�һ��Ů������������Ų���ط�����˳����ǰ����·��ǰ�ߡ���ͷ̫����ɹ�����������ۣ�����·�ߵ�Сͩ����ժ��һƬҶ�ӣ��־�����ס��ͷ����������õĹ�ͷ���չ��·�����ɫ��Զ�㿴���Դ�������˰������Ƥ������һ����������һ��ɽ�������ȵù�Ǻ������ÿ��ë�������СȪ�ۣ���ס������ð�������������ˣ�վ�ڰ�ɽ����������Ȼ������Զ��һ��������ֽ��ɡ��Ů������������������������ﰵ����ϲ���ɿʵ������ʱӿ���ɹ���Һ�����ȼ���Ǽһ�����˻��ż������������к�һ�¾�֧�������ˣ��ѿ��ö��ö�ߡ���������Ů�˿������Źջ�ȥ������è���������·������������أ���ſ�ڵ������һ��������ţ���ֻ�۾������ض��ż������ڵ����͡���Ů���������߹����ˣ�������Խ��Խ���ˣ����Ƶ���Ҳ����Ů�˵��ٽ��ӿ������������˵�ײ���ź�ʵ�����š��������ڿ������Ǹ�Ů�ˣ���һ������ϱ����Բ�ٴ�����ͷ���Ƕ���ë��������������Ŷ��䡣������ë�²�������������һ����ɫ���ӡ�һ�ֳ���ɡ��һ�ֿ���С������һ����֪���Ǵ����ݵġ��������룬���϶������ˣ����������϶����С�������ȥ���������ſ�ˮ��������Ӳ���Ķ�������ʾ���ر�ʾ������顣�����ڡ���ǹ���������������ˣ���ǹ��ָ���������ж�����Ů���ߵ�������ǰ������һԾ�������ð�شܳ����أ������Ƶ�������ȥ����Ů��ֻ����·����ǰ�䲻����ð��һ������ͻ�������ľ���ʹ������������һ��̱����ȥ�������������ϰ���Ū�������أ���Ů�˼���û�н��з��������ƾ͵ó��ˡ����ƹ������ɿ�����Ů�ˡ���Ů�˲���û���������ӳ������ó����������ɵݸ����ƣ�˵���ֵܣ�����ˣ��������������ԣ��Ҽ��ﻹ�����ӵ��ų��̣��ҵøϽ���ȥ�����������������������ڵİ����ɣ��������Ǹ�Ů�˵��ģ�����������Ů�����������˲�����������÷ŵ�������ͷ����ͨ������ȥ�����������Ứ���䶯���˵����㣬���ĺý�㣬��а����ˣ�����һ���Ӷ��������㡣�������Ҫ���ˣ���֪��ɶʱ�����ټ����㡭����Ů��˵������ţ������ӡ������ʣ�ɶʱ����Ů��˵������ʮ����£����������졣����˵������̫���ˣ����Ȳ�������Ů��˵����˵ɶʱ������˵����������Ů��˵���У������㡣����˵���������Ů��˵���������������ǧ����л��������Ů�ˣ�������֡���Ů��˵���ֵܣ����ɿ�����֪������ð�������ȥ������ι���̾�������������ɿ����֣�˵���ǰ�����������š���Ů��˵���У������������š���Ů�����ˡ����ƹ����Ƕ�������������Ů�˽���Զȥ�ı�Ӱ����Ů�˲��뿪����ʱ�ߵú�����������һ��ͷ�ؿ�һ�����ƣ���������ʮ�ָж���ÿ����Ů�˻�ͷʱ�����ƶ��̲�ס�����������ᡣ��Ů��������Զ�ˣ��ߵ�Խ��Խ���ˣ���Ҳ����ͷ�������ˡ���Ů�˵ı�Ӱ������ʧ�ˣ�����ɶҲ�������ˡ��������ڵ��Ϲ���û�����������������ڸղ���������˵�������С���ò������ΰɣ����ƶԸղŷ�����һ�в����˻��ɡ������˿�����İ����ɣ������������ͣ����ܸò��Ǽٵİɣ������ſ���һ�ڣ��ţ�ζ������������˿˿�ġ�û�����ǰ����ɡ�����İ����ɡ����µ��¶�����˵���壬������һ�����£����¶����ڻ��ǽ����ȵ��ˡ�������ɶ�¶������к��ģ������ԣ�������ֵ����죬ǰͷ�����Ӳ��Ͱ�����ˡ����ư���������������һ����Ů�ˡ����룬���Ů��Ҳ�����������ˣ�Ҫ�������������Ƕ��������������¶������Ƕ�ϲ˵�öԣ����˸�Ů�ˣ�������Ҳ����ֻҪ��������˭Ҳ����˭�����ƿ��Ű����ɣ�������Ʒζ�š���������һ�������ϻ�����һ��������óԡ����������û�ȥ����Ҳ��������þ�Ҳû�Թ��������ˡ��뵽���������ͦ�ѹ����Դӵ����˼࣬���ͷ����һ�һ縵ذס���˵ɶ���������Ҳ���ø�����ưѰ�����װ����������������Ů�˸ղ��߹���·����������Ů�˿������·�ľ�ͷ���ڳ�������Ӱ����������һ�����Ƕ�����֧�������ˡ�һ������������������������һȺ�ˣ�������һ����������Щʧ���ˡ��������ţ���Ů�˻�������ȻҲ������������ɡ���Ⱥ�������ƽ��ˣ����Ʋſ�������Щ�˵����ﶼ���żһ���DZⵣ����ͷ���ߵ÷�죬����Ҳ���������ġ�����������Щէ������������Ǹ�Ů�ˡ�����վ���������������ߣ�����㿪��Щ�ˣ��������߹�ȥ�����ٳ��������Ƹ�̧�ţ�������ǰ����Ǹ��˾ͺ������������յģ����Ķ��ܣ�����һ�������ƣ�������ɽ����ȥ��������������ŭ��ʨ�����͵������������������ŵ����ӷ�Ҳ�Ƶķ���ɽ�£���һ��س��ɽ����������˽����ᡣ��ʱ���Ƶ�����ֻ��һ����ͷ��һ��Ҫ�ܽ�������έ��ֻ���ܽ�έ�������п������ѣ��������������Ǽ����˷�ŭ����ȭ�±�����������ɽ��ͨ������έ�����ƾ�һֱ˳��ɽ����ǰ��ɱ��� �ܿ죡��ǰͷ�ء�һ���˻��������Ǵ��������� �ϵ���������Խ��Խ���ˡ����Ƶ�����ֻ��һ����ͷ���ܣ����깵���������Ӿ��ˣ��̻�����ˮ֮����������ɥ��֮Ȯ�����������ӵ��˱������������Ƭãã��έ�������������������έ�����������˵�������̶�ߡ����Ƴ����س���һ��������̶���ॵ����ţ�ˮ�ں��ںڵġ����������˺��£���������̶���ˮ����ſ����̶����ţ��ع��˹��˵غ������ں��ںڵ�ˮ��Ȼ��ѹ�ͷ����ˮ����˼��£�̧��ͷĨȥ�����ϵ�ˮ�������һ�¸е���ˬ�����ࡣ��������һƬέ���ܼ��ĵط�����������ߴ�Ϣ�߹۲�����Χ�Ķ����� �������������˲���έ�ӡ�������Զ�����Ʋ�δ���š� ���յģ��������ٲ��������Ǿ�ȥ�������֡���Щ�˱ߺ��߲�����έ���������ߡ�������Щ��զ�����������ž��Dz����������û��������ȵ���һ̧ƨ��Ū����έ�ӵ��ڸ�������Щ������ĵط�������������������ڡ�����ˣ��Ǽ����˿϶�Ҫ���ˣ��Ǽ��������ˣ����Ϳ��Իؼ��ˡ����������������š����ǣ�����үƫƫ�������ԣ���ͷ�����Ƕ�һ�����Dz������䡣��������έҶ������İ߰������⣬��һ����������һ������������������������������ҹ�������������ǡ�����ɨ���ǣ�������Ҫ��ù�ġ�δ����Ӧ�˷���˵����仰������Ҳ�����ˣ���զ����ù�� ��ͷ��б������������έ�ҡ�έ�����������������Ƶ���Ҳ������ͷ����б�ɽ��ǡ���������������ƽ���ˡ���ͷÿ��һ�ߣ����Ƶ�Σ�վͼ���һ�֡��Ǽ������Ҳ������ƣ��߳�έ��վ�ڹ��رߣ��Ӳ�ͬ�ķ�����έ������ʯͷ����ͼ�����Ƹϳ�έ���м���ʯͷ�������������ߣ���������Ȼ��˿δ�������±�¶�Լ�����Щ������һ���ʯͷ���Բ���έ�����κ��춯���������˸������ط�����ЪϢ��һ���˴���˵�������������߰ɣ��ȵúܡ���һ��˵���߾��ߣ������ִ���ס���⻰��˵���������ģ������������ƭ��������ʵ���������ܵؼ�����έ��Ķ�������������զ˵�����ƾ��Dz�������������ڣ���������ų�ȥ����ʱ��ű��ա� �չ֣�һ�����Ǹ�Ů���յĹ֡������롣��Ҫ�չ־Ͳ�Ҫ���Ұ����ɣ����˰��������չ֣������Ļ��¶������ƶ��ˣ��ڿ�����ͳ���������Ǹ������ɣ������Ϸ�Ū�š���¡¡������������һ���������̲�ס�ˣ�����һ����������� ����û�в´������Ǹ�Ů���յĹ֡��Ǹ�Ů��Ϊ����ס���ƣ����������������ɣ���������������ͷ����Ů���ܻؼ�һ�ѱ���һ������������˿����˱�������·�ľ����������ˡ�ž���ظ�����һ���ƣ��������W���˼����֣����ⲻҪ���Ļ���Ȼ��������Ǻ��˼��������ֵ�ȥ�����ơ� ���Ƶİ����ɲų��꣬έ��������˻���������������������Զ��������С����������������һ���ط�����������˷��������кܶ��˰�Χ��έ����ΧȦ�ڽ�������С�����Ƶ��Ķ�ʱ����������ͻȻһ�������������������������ϣ�������������ǹ����ֵġ����״ӿ������ܴ��ϣ�������úܽ�����һ����������������ŵû���ɸ�����²�ֹ��ҹ����С�챻�����ˣ�����һ�ȣ�һ����˳�ȶ��¡����������������������ֵ�������Ѻ�ţ����������ϵ����ŵ�̱�ڵ�����վ�����ˡ����ƺ����ˣ������Ҹ������ֵ��˶Կ��������ֵ���������Ӳͨ�����Ƕ����ǻ�����˵ġ���������ֻ��Ͷ���������뵽��Ͷ���������ֳ��ŵ���վ���������첲��������ȥ�˹�ͷ����������ͷ��һ�㾢��Ҳû�С���������������ϡ�������������̱�ڵ��ϡ�������˵��������ͷ��Ӳ��һ���Ҳ����ʹ������������ë�������ȣ���Ƥ�����ž��Ƿ�����������������Ͷ���������Ȳ��ܶ����ֲ���˵���������¹����ֵ���˵�������⿹�ܣ������ˣ�˵������Ҫǹ�С�ǹ�У��Ƕ��ۣ��ԣ�ǹһ�죬ǹ�Ӷ�����Դ�������������������ˣ���������ˡ������ˣ�˭������ʰ�����û�˸�����ʰ�����������ɶ��û����������Ҫ�����������˻�û������˵��������Ҳ����Ҳ�������Ǹ�Ů���ˣ��Ⱳ�Ӹ��Ǹ�Ů��Ū��һ�أ��ŵ��������۾�����ɶ��Ҳû���������ɶ��ɶҲ��֪���������ټ����Ǹ�Ů�ˡ����У�������Ҳ�Ͳ��ܸ���ϲ�ͷ�����Сɽ��һ��ˣ�ˣ���Ҳ����������˵��Щ�¶��ˡ����뵽��Щ�����ƾ���Ͷ�����������˵�Ӱ�ﻵ��Ͷ�������ӣ��Ѱ���ҵ������ϣ��еĹҵ��̵��ϣ�����������Щ���˾Ͳ��������ˡ�������ѧ�Ż��˵�����Ͷ��������û�аײ���û�аײ�Ҳ�������ɰ��죬û�а����û��Ͷ�������Ƹ��ż��� έ�ӻ������������ţ������ֵ���һ�����������Ʊƽ��� Ͷ�����ٲ�Ͷ�����������ˡ���ʱ���������·��֣������IJ����ǰģ��ײ������Ե����죬��Ȼ������֯�Ĵֲ���������ô�ף���������Ҳ���С����Ƴ����س���һ�����������ڿ���Ͷ���ˡ�����Ͷ���ˣ�����û����ô�����ˡ��������߲�Զ����һ�ض��˵�έ�ӣ�����ǰ�����������������Ѱײ�������έ���ϸ߸ߵľ��š���ʱ�������������һ�����¶���һ��׳�٣���ʤ���ˣ�������һ������ �������ƾ�������ʱ������Ա��վ����������ǰ�� ������һ��������ʱ�����Ѿ�����˵���ˣ���Ϊ���Ѿ�Ͷ���ˣ�����û��ѹ��û�и���Ҳ�Ͳ��ٺ����ˡ� ����Ͷ���������������������³��������֡� ���������װʲô�⣡��һֻ���Ż���Ь�Ľ����ص����������Ƶ�ƨ���ϡ� ��������������һ���������Ǹ��ˣ��������Ʒ���������ź����ڣ���üŭĿ�ص������� ����˵����������ס�ë��ϯ˵����Ű����²���� �����������Ƶ��Ǹ����̲�ס����Ц�ˡ�վ��������ǰ�Ĺ�����ԱҲ��Ц�ˡ� ���Ʊ�������������û��������������ϵ���������������Ͷ���ܵ����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