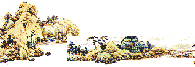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죬������أ�������չ�������糱���سǵĴ�������ж���߾��š�����ίԱ��á��ĺ�����ߺ��š������Ӧΰ������ë��ϯ�ĺ��٣�ʵ�и����Ĵ����ϡ��Ŀںţ���������㳡ӿ�������죬�����ظ���ίԱ����������������С� �㳡�ı������һ����ϯ̨����ϯ̨�Ϸ�ǣ��һ������ĺ������д�������ظ���ίԱ�������ᡱ���ִ��綷�����Ž�⡣��ϯ̨��Ļ������������ΰ������ë��ϯ�ľ����������˼�Ц�Ŵ�������Ż�������Ⱥ���㳡����ɽ�˺������������������룬���컹���Ʋ������������ɣ�ҹ��������ΰ������ë��ϯ������ָʾ�����ڹ��˽��ڲ���û�и�����������ͻ��û�����ɷ��ѳ�Ϊ�Ʋ���������������֯������֮��һҹ֮������ͬһ��ս�����ս�ѣ����������ֲ��ż�վ����ʥ�ĺ����¡� ̫���Ӷ���ȽȽ������ҫ���纣���ĺ��졣���������ﲥ���š����Ƕ�����������ĺ���Ϊ��һ����ͬ�ĸ���Ŀ���ߵ�һ�����ˡ���������ʹ���˶��е������Ҷ��������ë��ϯ��¼�衣�ڸ����У���λ���Ų�ͬ��ɫ��װ�ĸɲ���������ϯ̨�������������ź����ε���λ�ϡ����߸����У�����λ���Ų���ɫ��װ����ͬ���ǣ���һλ��������ͷ�ϴ��������ĺ�������ߣ���������װ������ί������һλ�Żƾ�װ������ȫ�غպ��������췴˾���Źⴺ��������Źⴺ���֣����ִ�������д�õģ�������̫���Ż���̫�����ֻ������߶��е�Ե�ʣ�����ò���ô̩ͨ�������������ظ���ίԱ�������Ա����������ίԱ�����������壬�������Źⴺ����������ϣ�����һƬ�����ţ�������죬�����������㳡��������Ũ�صĻ�ҩζ������ڡ�����ίԱ��á�����ΰ������ë��ϯ�������������꣡���Ŀں����н������㳡�ϵ�����̤�š����п����֡������Ľ��ĺ��ſں��뿪�˻᳡�� �������ίԱ������ˡ���������Ծ�죬����ɽ�����˸����Ρ���˵��������Źⴺ���Ҫ����ɽ�����εģ����ظ���ίԱ��������λ��Ա������Զ�δ��ɡ� ���������Ҳ�����˸���ίԱ�ᣬ������Ծ�����ʶ���Ź�Դ�������Ρ� �������ĸ�ҵ��ij��˸�ҵ�ӣ�Խ��Խ��𡣶����έ�ӱ����ˣ��͵����������������ֵ����Ҹ��������Ҹ������ϯ�����������ͳһ���������硣������������Ǯ����Ա�ǵĻ����Կ�ǰ���ǡ� ���꣬ɱ��έ�ӣ��Ź�ԴΧ��έת�˰��죬��ͻȻ������έʩ�ʣ����ڴ��������˲�С�ķ��졣 ����έ���Ϸ࣬����ٵأ��ӹŵ�����û��˵�������δ���������������˵�� �������Ÿ�ˮ��¶���ܡ�ׯ�ڵ�������������έ���ӡ�����һ�˸��͡� ��˵����ô��Ūɶ����װ��¶�ܲ�¶�ܣ���ʱ���֪���ˡ�����ϲ���չ���վ������ȵ���Щ���ͷ��� ���Ƶ���������������ˣ��δ������������̫��û����װ���� �������壬������������˵�� �����ӣ���������̫���������������δ���˵�� ���Ѱɣ���������������˵�� ���Ƶ����ѵ������ģ������ϼ磬����ѹ�ú���������֨ѽ֨ѽֱ�С�����˵�������첻�ϵ����ģ��������첻��Ҫ���ġ�����Խ���ߵ�Խ�졣���Ƶĵ����أ���Ҳ���ᣬ�������ǣ�����һ���������������ǰ��Ķ�ϲ�� ����ϲ�壬�߿�㡣�����ƻ��������������ײ��һ�¶�ϲ����𣬰Ѷ�ϲ�����ײ�õ������ת�� ��ðʧ��������ǰͷ������û�㾢������ϲ�������ÿ���·�� ��������ǰͷ����ϲ����������ƨ�ɺ����˱�˵���ߣ��ܿ쵽�˱�����έ�����Ʒ��¹�����˫���������ѣ�������һ���������ķ���һ���������ڵ��ϡ� ��������ϲ�壬�Ұ������������������ϲ���ڵ��ϵ���������������ͣ�һ�ȷ��µµ��������̶���˵�һ����������ƽ����ˮ�浴���˵������ơ�����ϲ�壬��˵��̶���й�����˵������û�У��� ����˵�У���˭Ҳû�������� ����˵������������� �����������˼Ҵ������ϴ�ţ���֪����ɶ�ѽŲ�ס�ˣ��ŵ������ʹܣ���Ҳû�������� ��˵��ʮ����Ϳ������ˣ�С���Ӳ��ܿ�������ϲ�壬ʮ����զ���ɴ��������� �����Ǿ���ᣬʮ�����Ȣϱ���ˣ�Ȣ��ϱ���ͳɴ��������� ���Ʋ�� �����ƣ����ʮ���˰ɣ��� ���š��� ��Ҫ�������㶼Ȣ����ϱ���ˡ��� ���ƺںڵ����Ϸ����˺��Ρ� ��������˵����ϱ��û�С��� ������������ɶ�á��� ������������ϵĴ�ɲ�������Ȣ��ϱ������ɶ�ѡ��� �����������˵˵���� ��������˴�ɲ���æ��������²�����һ�ˣ���զ���õ������� ������ɶʱ�����������˵˵�������Ƶ�Ŀ��������� ���У������������ϡ�����ϲ����ͬ���˵�� ����ɼ�ס������ϲ�壬�����ˡ��� έ���Ϲ�����Ź�Դ�ֽ���Ա�ǰ�έ�����������ɣ������������һ����Ҳ����Ա�ǹ�ȥ��û�����������顣 һ������֮��έ��ӱ��ɹ��������к������������˳�����������׳�����缦�����ں����������ҫ������Ͳ�����Ƶ���ˢˢ�����ϴܡ���ʱ����Ա�Dz������������Ź�Դ��û���έ�Ӿͳ���һ�˶�ߣ��������飬˿�粻���Ź�Դ�������ɱ��ϸС��έ�ӣ�����έ���ܱߡ��Ź�Դ����һ�ٴ���ȻҲ�����˲��ٻ��ɵ�Ŀ�⣬���վ�û��˵���Ǻ������������֮�����ڵ��µ�Сέ��ÿ���ڰ��϶�������һ�������Ƶ���ѿ��έ�����ˡ�ϸС��έ�ӱ�����έ�����˸���������ռ䣬έ�˳��ø��߸��֡�έ�ӷ����ˣ���Ա�����ﶼ��������Ź�Դ�� ��ҵ����æ�ű�ϯ����ʱ������ɽ���Ź��硰��β�͡�С�������˻�����������ɽ����ε�����ͬ��ǰ����Ծ��ʱ����������������������������顣�ڶ��ε�������������������Ⱥ�ڸ㡰�ĸ����ʱ�ҵ��ǹ����췴˾�˾���ͷ�Σ��������������ǹ�������Ա����εĵ���������ɽ�����ݱ��ˣ�����һ������ͨͨ�ĸɲ����ǹ������ίԱ�ḱ���Σ�����������������Ա������ɽ�ǵ�����ץ������͵ġ��ڴ����ʱ����壬���˶�˽���Ľ��죬�Ź�Դ��Ȼ����֯��ҵ�Ӵ���ʱ����壬��һ���к�̨���������ڸ�Դ�ġ��Ź�Դ���ʱ����壬��Ծ����֪���ġ���Ծ����һֻ�۱�һֻ�ۣ��Ȳ�����Ҳ����ֹ�����䷢չ�����ϸ��ʱ�����β��ץ����ô�������ǿ����������ļ�������Ծ��ֻ�ڹ����ٿ������������磬��ӣ������ӣ��ɲ��������赭д��˵�˼��䣬���žͲ���ʲô��������������ɽ��Ϊ����Ծ������ִ���ʲ���·�ߣ�����������Ծ����Ÿɡ�����ɽ���ظ���ίԱ������������㱨�õ����������֧�֡�����ɽר�ų�����һ������β�͡�С�飬��Ҫ���������ظһ����һ���ӵظֱ�������ꡣ����ɽ��һ����ѡ����������ԭ��ġ�����Ϊ����һ�����������ʱ������������ԣ�����β������ץס���ڶ����Ź�Դ�ı�������֧�֣��Ǿ�����Ծ�죬���Ź�Դ��Ŀ���Ǹ���Ծ�졣 ����ɽ�Ǻȹ�īˮ���ˣ����ʱ�����β������һ�ġ������������ĵ������Ͼͽй����Ӱ��������һ����Ӱ�����硷��ɽ����ŵ�Ӱ��ʮ���ѷ������µ��£���Ȼ�˵��ú��롣�ȹ��껹Ҫ���֡������������۴��˻������ӣ������ŵ�������ɹ��������ռ�����ط�����Ů���������ˣ��е�����Ҳû���Ϻȣ���������Ҳû�������룬������Ȧ��ߺߣ�����Ҳ��ȥι��������ܵ���ɹ��������ү��ô��һ�����Ҳ���Źչ����ˣ���ȳ�Ӻδ�������һ��ɹ���������������ӣ�����һ��Ļ������պڣ���Ӱ�Ϳ�ʼ�ˡ���ɫ��Ļ����һ����������ֵ�����æµ�ţ�����Ҳ�Է���Ҳ˯����Ҳ�ɻҲ���ᣬҲ�����ʱ����塭�� ���ף����ڵ������ܣ�զ�Ű���Ū���Dz���ȥ�ˣ��㿴������һ����������ү������� �����壬�Ǿ������ˣ�զ��������һ�������δ���˵�� ���ղ��ǹ�Ů˵��ɶ��������үָ��ӰĻ�ϵ��ﴺ�磨��Ӱ�������ʡ� ����˵����Ҫ�������IJݣ���Ҫ�ʱ�������硣���� ���⻰ɶ��˼��������үŪ�����ס� ��������˼��˵��������ׯ��Ҫ����������ׯ�ڣ��������ʱ������ׯ�ڣ�Ҫ�ǰ�ׯ���ֳ����ʱ������ׯ�ڣ�����Ը��Ҫ���������ֳ��������IJݡ����δ�������˵�� ����ƨ������Ů�Ҷ�ɶ����Ҫׯ��Ҫ�ݣ����˲�������������������ү���ﴺ��ĺ�˵�˵��߷�Ȼ�� �����塭�����δ�����Ҫ˵ɶ��ͻȻĻ���ϵ���Ӱȫ����ʧ�ˡ� �����˵��۾������ŷ�Ӱ�������Ǻ���ɽ�йصġ���������Ū������զ���¶���ʱ�������ﴫ���˺���ɽ�������� ����������Աͬ־�ǣ��������ǿ����ᣬ�Ὺ���ˣ����ŷŵ�Ӱ������ ��Ⱥ�з����������������������е���������ã��ò���������Ӱ�����ܿ���أ����ֻ����������������ɽ������ ����ɽ˵������������Աͬ־�ǣ��ղŵ�Ӱ���ﴺ��ͬ־�Ļ���Ҷ������ˣ�������ׯ��ҲҪ����������ׯ�ڣ����������ʱ������ׯ�ڡ����ڣ�ũ���ʱ���������ʮ�����أ���Ҫ�������Ǹ߶Ⱦ��衣������������Ǵ壬���Ƿ�������������ʱ�����β�͡���������ɽ�������ʱ�������ũ������ֱ��ֺ��ʱ�����β�͵����壬��Ա������ʱ��������ͷ�� ��ҵ�ӱ�����ɽ��Ϊ�ʱ�����Ĵ�β�ͣ�һ�����ˡ� �Ź�Դ����ְ�ˡ� ���⳽�������ˡ��軨ǣ�Ŷ��Ӹ��ڿ��⳽������һ��һ��ͷ���뿪�˻��������軨������������ˮ�������������Ҳ������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