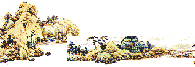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ȣ�һ˿��Ҳû�У���������������������������϶����������ӡ������������δ�¡�С�Ӷ����ˣ��ӵɺ��ˡ����ؽ��ʵñ������̡������ˮλ�����½�����������һ����һ�ڣ�������Խ��Խ�֣���ˮͰϵ�¾���Ҳֻ�ܹ����ư��ˮ����Ҷ�����ˣ�ָͷ�Ǵ�Ļ���Ҷ����˴�����ң���ס��������Ϣ������Ʈ�䡣������ֻ��һ�����ã�¶�ź����Ƶ������������긾ŮҲ���˼���ô���ˣ�����¶�����е�Ҳ������һ���ɴ�����˹���ӣ���ǰ���ŵ�������ͷ�����ǽ���ϵ���ֻ��������˿�����ر�������̰����Ŀ��������˺�������� ������үѽ���Dz���Ҫ�����ⷽ�ˡ����������������������£���ס��ҡ�ŰŽ��ȣ������������Ƶij������˵�� ����ʮ���˶�û���������죬������������������һ�������������˵�� �Դ�����ˣ����Ű��ӣ����հŽ��ȣ��������Ƶ���ͷ����������ĽŲ��н����һ˦һ˦�� ��˧���������������Զ���;����к��Դ�š� ��������ƨ�֣����Ұ�ˡ�������������˵�� ���Ҿ��ǿ�������������˵�������ո����֡����Դ��˵�����ڻ��ͺ�������Ķ��棬������ҡ�ŰŽ��ȡ� ���㿴�㣬Ҳ���������ѡ�������˵�� ������¿Ƥ��ƨ�֣��ȵø�ɶһ�������Դ�������ں��� ���㲻��������Ц������������˵�� ��Ц��ɶ��˭���ﳤ��ɶ��˭��֪�������Դ��˵�� ����������Ūɶ�֣����������Դ�š� ��Ūƨ�����ȵÿ������ˣ�������˼Ūɶ���� ��������һ����һ�������˼ҳ��� ��Ȼ��һ���ͳ������״�Զ�����������ߵ����ӿ���˴�ɽ�Ƶ���ͷ���ں��ںڣ����������״ߴ��£��������ͣ�֨֨�ϴܡ�Я�б������Ũ����ǰ��ʻ�ţ������������Ŀ�϶Ҳ�����������Ũ�Ʋ��ϣ�һ�����ڱ��˴�����ա�����ˡ���˳����������������ɫ�Ļ���Ҷ���£��ڵ��ϴ��Ź����ɶ�������ȥ���������ش��ˣ�������ϵij����Ӳ���Ҷ��ĭ���ڿ��з�����ɲ�Ǽ�ͱ�����ذ��ˡ� ���Ͳ����Դ�ż���ͬʱͣ����ҡ���ŵİŽ��ȡ� �����������������������������������ܵط����ij���˵�� ����Ž�˼������ˣ�Ҳ��Ž������������������˵�� ��Ž����ƨ���������춼�м����ˣ��Ļز��ǵ���������Ƥ�����˼������ӣ������ˡ����Դ�Ų���ΪȻ�� �Դ�ŵĻ������䣬ֻ������������һ�����죬�����˶���æ��ס���Լ���ͷ�����ը�װ����ը����һ�����ڶ�����ն�ʱ����˺�������Ļ�����ڶ�ð�ź�����������ɫ����Ƭ�����칷������һ��Ѹ�ٳԵ��˽������������죬��ձ���˹��ס���ɫ���Ʋ��в��ϴ��������˺�¡¡�ľ��죬��������ľ���Ϲ����ž�ʯһ�㡣��Ȼһ����⻮���˹��ף����˳�Ź��ķ�϶������������ʼ��һ��һ�Σ�ϡϡ���������ڵ�����ͭǮ��ô�ѵ��ϵij����ҳ�һ����С��������������С�ˣ������ˣ�������ߵ����ӡ��ٺ��������һ��������ֱк���£���৵����ء��������һ��̰������˱�Ÿ��أ�һ��֮�����ĵͰ���������һ̲̲��ˮ�����м�ɺ��Ѿõ�С�ӹ��������˷��������Ļ�Ц������Ա�ǵ�����Ҳ¶���������������ټ���Ц�ݡ� ����̫�õĺ�������ð������ѿ����һ�����ǰ�ܡ���Ա��æ�������ˣ����������Ų�ñ����˫������������ż����ں���������ؼ��ź������ӡ�Ů���������������������°Ѻ������Ӽ���һ��һ�ڵģ�Ȼ��ͨ�����������ֲ������� �����ˣ�������Ȼ�¸���ͣ������ͱ�����Ƶģ��������������㵹�Ż����Ѿõ�ˮ�����ܶ��˼ҵķ��ݿ�ʼ©���ˣ�����ǽ������ˢ���˿����Ƥ����ʱ�ط������������������������ķ�ӻ�������ˮ������֪�Ӻδ����˳��������ڷ�ӱ߿��ۿ��۵ؽ��ţ���֪��Ϊ����ү�Ĵ�����������質������Ϊ�Լ���С�ѱ���û���������˵İ�����������ͣͣ��ͣͣ���£�ʱ��ʱС��ʱ���罻�Ӵ������裬ʱ��ϸ���������������ʮ�����ȥ�ˣ���Ա�����ϵ�ϲɫ����˳��ݡ� ɽ�鱬���ˡ���ˮ������ɳ�����ι�����ӿ������������˷�������ֱ������������������С�ӱ���ˮ�����ˣ�С�����²�Ӯ�������ɶ�����ˮ�ͽ��˸��Ҹ�����Ժ�䣬�����˼ҵ�Ժ������������û���˼ҷ��ӳ�Ѱ���ſɱܺ�ˮ�İ���֮�ء���¡--����--��һ�ҵķ��ݵ����ˣ���������һ�ҡ��� �����ޣ��δ�����û��������ȥ����������ϲ���������ұ���ķ���˵�����δ����ҵĵ����ϵ͡��� ����б�����ſ��ϣ�����Ժ����������������ٲ��Ƶ��������þ�û��˵���� �������ˣ��㲻ȥ��ȥ��զ˵Ҳ��������������ϲ������˵����֪��������˼�����Ǵ������þ�����塣 ����ϲ�壬��ȥ�����������ֵ���һ��˵�����������첡�ţ��ջ�û�ˡ��� ��ϲ�ƿ������֣����˳�ȥ���ܿ���ʧ����������֮�С� �δ����ļ��빵���������ˮ���˹�������ӿ�������ļҡ���ʱ��Ժ�����ˮ��������������ˮ����û�˴��������������ӡ��δ������ڴ��ϣ����첻Ӧ���е�����������˫�ۣ�һ�����࣬���ڵȴ�������Ľ��١� �������磬�����硣��������˼��ٵĽ����� �δ������������ۣ�����Ϊ�������Ρ� �������磬�����硣�� �����뻩��������ͬʱ�����δ����Ķ��䣬��ϸϸһ������֪���Ƕ�ϲ�ڽ����� �������磬�쿪�ţ��� �δ����ľ���Ϊ֮һ�������漴ӿ�������ᡣ ����ϲ�������δ����ĺ�����������һ������˵���ϻ����������Ŵ��ط���ǽ�ڣ����ѵ��ߵ��ſ���������˨����--Ժ��Ļ�ˮ������ȱ��Ѹ��������ӿ���� �������ںδ�����ǰ����ɶҲû˵��һ���ƿ���ϲ�������ڷ�㶵ĺδ����������ߡ���������������ĺ�ˮ��������ǰ���ţ��δ�����������Ҳ����ס�ˣ�˳���۽���������ˮ�����һ�����ڷ��IJ����ϡ����ްѺδ���������ϲ���Ťͷ���ߡ��δ������ŷ�������ı�Ӱ�����е��������ޣ�����--�����Ƿ�����ͷҲû��һ�¡� ��ҹ�����µø����ˡ���ˮ�����˻�������ʮ�䷿�ݣ���������Ҳ����ˮϯ����ȥ���δ����ļҳ���һ������ɶҲû���ˡ� ������磬�δ�������˿��⳽ס�����Ǹ�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