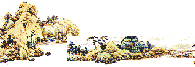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Ա��Ὺ���ˣ�����û���˯����������Աɢ��ɲ����¡�����������Ա���߳����ӣ����������˸����������������Ƕ����˸���Ƿ����ʱ���ƴ������߹�������˵�������ƣ���Ҳ��һ�¡��� ����˵�������Ǹɲ����ᣬ��������Ūɶ���� ����˵��������ȵȣ���͵ȵȡ��� ��ϲ�߳��ݣ�����������վ���������˵�������ޣ�����ɶ�¶�����˵���� �������������߽��ݣ����Ŷ�ϲ��Сɽ˵����������˿ˡ��� ��ϲ˵����������ҹ�ˣ���ɶ�˿ˡ��� ����˵�������Ǵ��̣��д����������ը������ԡ��в��У��� Сɽ˵�������̾ʹ��̣�ը��ը������С�¶����� ���������ζӳ�����ϲ�������ӳ���Сɽ�ǻ�ơ��������ˣ�������ϲ���óԣ�ֻҪ���Ͽ��ᣬ�������ŷ�����Ҫ��һ�١�����ը������dzԸ�����������Сɽ���ţ���ʱ�����Ӹ�������ڶ����˻ᣬ�������ֲ��ˡ� ��ϲ˵�����С��� Сɽ˵�������Ķ��� ��ϲ˵��������������� ����˵��������������ۻ�����ϲ���ȥ�� �ĸ���һǰһ��������ϲ�ң�֧�����Ӵ����ˡ������Ρ����˿˵�һ���淨��˭�Ȱ�������Ƴ���������Σ�˭������������Σ��� ����˵��������զŪ���� ��ϲ˵���������ӡ��� ����˵��������ޡ��� Сɽ˵�������ֲ�������ɶ��ޣ��� ����˵����Ӯ��Ҫ�������ȥ����ޡ��� ��ϲ˵�����У������Ϲ�ء��� Сɽ˵�������ƣ����С�ĵ������ ����˵�����þ��ã����ֲ���û�ù����� ����������ƿ���ͷ��ȥ�궬�죬��һ�����ϣ������ĸ�����Ҥ����˿ˣ�Ҥ��ů�͡����Ŵ��ţ����������ˣ���������ͷ���Ŵ�磬���䣬�������ȥ�����Ƿ��������������ӣ���ֽ����������˵��ȥ�ø���ޡ�����˵��զ����ȥ�ã�����˵�������ϵĺ�����ࡣ����������������ϵĺ��ӣ������������࣬����ֻ��ȥ����һ��������������������ֽ�����ȥ��������˵����ȥ������ޣ�����ȥ��������˵����ȥ��������������֣������ҵ�����ȥ������������Ҳ�ǣ�������ȥ������ˡ����ƻ��������ϵĺ��ӳ�������������˵��ֻ��һ��������˵��Ϊɶ������˵����ֻ����һ����ޡ�����˵���һ�ȥ����һ�ء�����˵�����У�ֻ����һ�ء���������������������һ���� ��ҹ�����������������˺��ӡ� �ڶ����µظɻ���Ƹ���ϲ��һ�� ����˵������ϲ�壬զ����֣��������䡣�� ��ϲ˵������Ҫ�����ÿ�����ܹ����˼����ơ��� ��������ˣ����ÿ����С�˳���ȥ�������IJ���ƨ���¡� ����˵����ÿ�̶��������������ȳ��ꡣ�� ��ϲ˵�����䶼�����ˣ��㻹����Ūɶ���� ����˵�����һ�ȥ����˯���š��� ��ϲ˵�������²�����զ���ˣ�������ϱ������ ����˵�����Ҳ�û�롣�� ��ϲ˵����������ɶ���㿴��ɽ������˵ϱ���ˣ�������Dz���һ���������ˡ��� ����˵��������ɶ�ã��㿴�۳������������˭���ۡ��� ��ϲ˵����˵��ʵ�������벻��ϱ������ ����ЦЦ˵�������Ƕ����֣��� ��ϲ˵����˵�滰�������벻�룿�� ����˵�������롣�� ��ϲ˵�������룬����϶��в����� ����˵���������� ��ϲ˵�������ɣ�������˵ʵ���ˣ������в����� ����˵����ɶ������ ��ϲ˵����ɶ������һ˵������ ����˵������˵���� ��ϲ˵��������Ӳ���� ����˵����������˵����Ų���Ӳ���� ��ϲ˵�������Ӳզ����ϱ������ ����˵����˭˵�����ˣ�����˵û�˸��ۡ��� ��ϲ˵����˵���˰��죬�㻹����ϱ������ ����˵����û�˸�����Ҳ�ǰ����롣�� ��ϲ˵�������ƣ���Ҳ������˿�������ˡ��� ����˵���������Ǹ��˿�������ˣ����˼ҿ����𰳡��� ��ϲ�����ƿ�������Ц�����Ҹ���˵�����ơ�����ׯ�и���Ů���˳��ò��������ǽ�����Ū�����Ҳ����żҡ��� ����ͣ�����еij�ͷ�����۲��Ͱ͵ؿ��Ŷ�ϲ�� ��ϲ˵������Ҫ��Ҫ��������ȥ˵˵������ǹ�Ů�����棬���в��С��� ����˵��������˵�ɣ����ǵ����֣��������¡��� ��ϲ˵�����㿴�㣬ƽ���ʰ�����Ūɶ���� ����˵������Ҫ�ǵ���զ˵���� ��ϲ˵����˭����˭�ǹ������ţ���������������ָͷ���� ����˵�������У���ȥ˵�ɡ��� ��ϲ˵�����ۿ���˵����ˣ��ǹ�Ů������Ū������ ����˵����Ū����Ū�������ֲ��ǹ�������һ�ھ���һ�ڡ��� ��ϲ�Ǹ�����˵��ˣ�ģ������Ƶ����棬�Ҵ�ææ����һ��ֽ������ϲ��˵������ϲ�壬���㣬����������ǰͷ���� ��ϲ˵�� �����ż��ˣ��� ����˵���������롣�� ������ϲ�Ǹ�����˵����Ц��������һ���棬��������ͷ�߶�ϲ����ϲ���Ƶ�����ǽ�ϣ���Ҳû��������Ҳû���ˣ���ֻ�и����ư���Ц��������ȥ�� ���˼��죬�����������ʣ�����ϲ�壬����զ������ ��ϲ˵�������ƣ��ǹ�ŮԸ�⡣���ڶ����س����߸�����棬���������ȥ���ǹ�Ů��Ը�����˿������� ����˵���������һ���ȥ���� ��ϲ˵����������զ��ȥ���Ҹ���˵�ˣ��ǹ�Ů��Ը�����˿������� �����ʣ����ҵ��Ƕ�զ˵���� ��ϲ˵������ɶҲ��˵���Ƕ�����һ����վ�ţ��������ס�����ˡ��� ����˵�����Ҳ��ҡ��� ��ϲ˵��������ɶ����������Ū�����ֲ��Ǵ��Ů���� �����ʣ�����ס����զ˵���� ��ϲ˵������ס�ˣ�ֻҪ�������㲻���㣬����Ը���ˣ���ʱ������զ˵��զ˵���� ����ˣ�����ʱ�ϵ����س���·�ڡ����Ǹ����죬�ڵ��硣����û����Ҳû���£�����û�е�Ҳû�л����ܺڹ�¡���ġ�������ϸһ����·�ڵ��Ա߹�Ȼ��һ����Ӱ���������Ȳ��������߹�ȥ���쿪˫��������ȥ����һ������������������Ļ��ŵ�����������һ�ɣ����Ⱦ��ܡ����˼�ʮ��Զ��������յ·�ƣ����Ʋ�ͣ�½Ų�����ս�ľ���Ť��ͷһ��������ʲôҲû�У�����ŷ������������������ߡ� ����ϲ�壬�㵹�������ڶ������Ƽ�����ϲ˵�� ��զ�ţ��ǹ�Ůûȥ������ϲ��װ�Ծ��� ��ȥ��������������˵������а������Ǹ������������ģ���ֱ���֡�˭֪���������ɶ���� ���϶����ǹ�Ů�������ˣ�ûȥ������ϲ�������ƣ�����Ҳ̫���ˣ�Ҳ�������������˵�����ӣ����DZ�ס��������--�췴������ĵ����ˡ��� ����ϲ�壬�������㵹���ɣ��� ���㿴�㿴�������ˡ����ƣ�����ɶʱ�����㣿��˵�����嵹��Ūɶ���϶����ǹ�Ů�����ˣ�ûȥ������ϲ�������Ƴ�����Ȱ��������¼����Լ��Բ��������ɡ������������в���ˣ������ٸ���˵���� ����ϲ�壬����ɼ�ס�����ٵ������� ��ϲ˵�����С��� �������䶷�ֵú��ף������߹��硱����ԥ���ܡ���ǹʵ���ظ���һ����ϵ�����Ҳ�ɼ��ι���֮�ƣ����������Ҳ��ĥ����ǹ�������������̶��ڶ��������ش���ì�ӡ���ϲ���ڼ�������Ҳ����ȥ���������������¶�������øɸ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