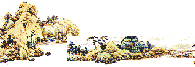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荒
|
||||
|
唐
|
||||
|
岁
|
||||
|
月
|
||||
|
□董新芳
|
||||
|
登记号:21-2001-A-(0656)-0115
|
||||||
张光源的家里忙乎起来了,大山的对象的爹要来看张光源的家。张光源老两口象迎接皇帝一样把院里扫了又扫,把屋里整了又整。院子扫得再净,屋里整得再齐,但穷是没法扫走也无法整掉的。为了瞒穷,也为了装富,张光源用席子在屋里扎了一个大圈,装了大半圈红薯片,然后在红薯片上铺了一个卧单,借了几布袋小麦倒在上面,一眼看去,冒尖的一屯小麦。猪圈里也做了精心的安排。本来张光源家里有一只断了尾巴的小白猪,张光源又连夜从亲戚家借了一头大白猪关在圈里……准备就绪了,那闺女的爹跟着媒人到了槐树沟。张光源老两口热情至极,鸡蛋茶,粉条肉,白蒸馍热情款待,饭桌就摆在那囤小麦的旁边,那闺人的爹堆了一肚子,抹了抹嘴,瞟了一眼那囤小麦,假装屙尿到猪圈溜了一圈。那头大白猪见有人进来以为有食可吃,从窝里钻出,断尾巴小白猪也紧紧跟在后面。大白猪仰着头,小白猪瞪着眼,企盼着面前这位陌生的人能给它们留下什么吃的。那闺女的爹见一前一后跑出两头猪来,扭头走了。大白猪失望地哼了两声,小白猪甩甩耳朵又一前一后慢腾腾地钻进了窝里。媒人见那闺女的爹站在门外,知其意,走到跟前问,咋样?那闺女的爹点点头,然后伸出两根指头。媒人会意。那闺女的爹走了,媒人跟张光源说,那家愿意,就是得花俩钱。张光源问得多少。媒人伸出两个指头说,那家要这个数--两千。张光源一听,懵了。问,得恁些?媒人说,不多,那闺女漂亮。张光源说再漂亮也值不了恁些。媒人说有人出的价钱比这还大,那闺女嫌那家的娃子长得闷,没成。咱这娃子(大山)长得乖好,透能,那闺女给棉花打药时见过咱这娃子,估摸着不会有啥意见。张光源说,你再跟那家说说,一千,要中,咱就订下,十五见面。媒人说那我再说说看。媒人掇合的结果,各退一步,各让五百。大山的亲事就这样订下了。 其实大山订的这门亲事还是乔大富的二闺女巧莲。自从乔大富拒绝了巧莲跟大山的亲事,巧莲就一病不起,请神婆请大夫均未见效。没有多久,本来十分漂亮的巧莲变得象一朵枯萎了的花朵,又黄又瘦。乔大富两口子十分着急。后来队长跟乔大富说,你甭乱求医了,没用。你闺女得的是心病,要想治好还得心药。乔大富明白了队长的意思,急忙给巧莲找婆家。一连找了十来家,巧莲一个也不见,病也未见轻。队长又跟乔大富说,你甭瞎忙乎了,治好巧莲的病还得槐树沟的大山。乔大富傻眼了。回到家跟老婆一说,老婆说,救咱闺女要紧,我看就依了她吧。乔大富想了想也只有作罢。于是托队长到大山家去作媒。队长悄悄给巧莲透了个信儿,巧莲的病就好了大半。乔大富对这门亲事本来就不中意,所以就狠了狠心要了个大价钱。对前面这一段,张光源老两口一无所知。 大山的亲事订下来了,但钱往哪里弄,这事愁煞了张光源。 “唉,咋弄?”张光源跟妻子惠贤商量着筹钱。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办法,张光源无可奈何地说:“要不就先把自留地的红薯刨了拉到城里卖了。” “这才几月,”惠贤望着丈夫愁苦的脸说:“还不到七月十五,我看红薯都还没结。” “我先刨一窝看看。要有,咱就刨。” “那中。”惠贤做出了无奈的回答。 张光源扛着镢头,脚步沉重地来到自留地,放下镢头,拄着镢把,呆呆地望着那片绿油油的红薯地出神。这是还未断奶的小猪,这是刚出蛋壳的小鸡,这是才落花的瓜胎,这是刚灌浆的玉米……太嫩了,太年轻了,难道忍心就这样终止它们的生命?张光源犹豫着不住地唉声叹气,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走进了红薯地。张光源弯下腰,用手轻轻拨开覆盖地面的红薯秧子,选了一棵根部微微隆起尤如刚刚发育的小闺女的乳房的红薯,用手指轻轻地抠着那隆起的泥土,然后扒开,一个小石榴大小的红薯露出了地面。张光源把这根红薯抠出,用土填上小坑,掂着镢头回家了。 “大山,”张光源喊妻子,“你看,好的就这么大。” 惠贤接过张光源手上那根粉红皮子的小红薯,仔细看了看说:“怪怜人的。”惠贤又看了看丈夫那布满忧愁的脸和紧锁的眉头,为了不使丈夫更难过,话一转说:“不过这阵儿刨了能卖个好价钱。刨吧。” 小山跟爹一同下地,张光源在前面刨,小山在后面捡。那些红薯确实可怜,成形的不多,大多都是筋筋串串,就象大跃进时张光春栽的那棵“红薯王”的根须。张光源黑丧着脸,一声不吭,用力挥舞着镢头,呼哧,呼哧,镢头发出沉闷的响声。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在张光源的脸上顺着皱纹滚动。小山边捡边摘,一根根没有成形的红薯象没有成形的婴儿通过他的手强行与母体分离,伤口处滚动着白色的血液。小山看着想着,伤心地落下泪来。 青石板似的夜空钉满了银钉,银钉闪烁,放射着银光,穿过浓重的夜色投射到大地上,黑暗的大地泛起了微微的亮色。张光源如牛般地拉着架子车,小山在前面用力地背着纤绳。坡,实在太陡了。父子俩弯着腰,脸几乎贴到了地面,呼呼喘息的大气吹起了地面上的粉尘,粉尘扑面,张光源被呛得发出两声咳嗽。架子车终于被拉上了大坡,两人的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流。 “爹,歇歇吧。”小山喘着粗气说。 “歇歇吧。”张光源取出车上的棍子支起了车提。 父子俩坐在路边,象卸了套的牛顿时松弛下来。他们的身后是一片光秃秃的坟地,那一个个黑糊糊的坟堆在微弱的星光下幽幽地惨人。小山瞟了一眼,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背脊隐隐升起,他赶紧扭过头,他心里十分害怕。小山双手抱腿,把头伏在膝盖上。张光源掏出旱烟袋,按了一锅烟,滋滋地吸着,劣质烟的味道呛得他不住地咳嗽。张光源吸完,在鞋底上梆梆地磕去烟灰,收起了旱烟袋。小山以为要走了,抬起头来,忽然他隐隐约约看见前面的路上五匹紫红色高头大马驾着一辆胶皮轮子大车,车上端坐一个彪形大汉,手中高举马鞭,照着拉梢的马啪地一鞭,五匹紫红色大马顿时飞奔起来,马铃随着飞奔的脚步哗哗地响着朝他们跟前跑来…… “爹,你看那马车。”小山惊奇地说。 张光源顺着小山手指的方向望去,前面黑糊糊的一片,急忙起身,故意咳嗽一声,说:“小山,走!”张光源想,夜半三更哪来马车?小山一定是看见鬼了。就在张光源说话的瞬间,小山眨了下眼,马车不见了。小山想到了那片坟地,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前面是下坡路,下坡路,用不着小山拉纤。架子车跑得很快,小山踮起脚跟在架子车后面跑,他心里害怕,不敢落在后面,而是身子紧紧贴着车提,这样离爹要近一些。咯噔,车轮碾在了石头上,车身一颠,有几根红薯从架子车上滚了下来,有一根还砸在小山的脚面上。 “红薯掉了没有?”张光源问。 “没有。”小山回答。 小山害怕,不敢捡落在地上的红薯,只顾跟着车跑,一不小心,飞旋的车轮从他的脚上碾过,小山忍着疼,一声没吭。 太阳升起三丈高的时候,父子俩终于进了平川市。高高的楼房,繁华的街道,拥挤的人流,穿梭般的汽车……初次进城的小山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张光源把架子车拉到农贸市场,那里有卖肉的,卖菜的,卖鸡的,卖蛋的,卖鱼虾螃蟹的,还有卖粮食的……张光源不顾劳累,大声吆喝:“红薯,红薯,新鲜的红薯,快来买哟。红薯,一毛钱一斤。” 城里人爱吃新鲜,随着张光源的吆喝声,那些提篮买菜的老婆婆和中年妇女呼啦围了过来,把整个车子都包严了。 “ 便宜点,五分。” “不中。” “ 俺再添点,六分好啦。” “ 不中,一毛。” “ 七分七分。” “不中,俺拉了一百多里地,不够脚力钱。” 那些人说话蛮里疙瘩的,不住地跟张光源讨价还价,有些话小山也听不懂,他不知道城里人说话咋是这种腔调。不管那些人咋说,张光源死咬着一毛,一分不让,就象铁板上钉钉,一点也没有走攒。那些人边挑边选边说贵了贵了。一个中年妇女把选出来的红薯放进张光源准备好的竹篮里过秤,张光源掂着秤看了小山一眼说:“看好摊。” 小山会意,眼睛紧紧地盯着十几双不停地翻动红薯的手。那些手有胖如螃蟹的,有瘦如鸡爪的,有粗糙如沙布的,也有细白如玉的。这些不同的手都在做着相同的动作,选出红薯,掐去头尾,扯掉根须,装进篮子。不大工夫,一车红薯卖去了大半。高峰期一过,买菜的人顿减,他们的架子车前也变得冷清起来。太阳升上中天,已经晌午了。架子车上的红薯在太阳下也蹙起了眉头。大的圆的没有了,剩下的都是些长条子,象红萝卜一样。皮也被翻拢掉了,变成了红一块白一块的大花脸。 “咱到街上转转。”张光源说着推起车就走。小山在太阳下站了半天,又饥又渴又累,无精打彩地跟在张光源的身后。穿过大街,钻进小巷,张光源在一个卖羊肉汤泡馍的饭铺前停下。“小山,咱在这里喝碗汤。”张光源说。卖羊肉汤泡馍的老汉见到张光源,热情地说,张掌柜你这向到哪里去了?好久都没来了。张光源说,这向不准做生意,我就没再跑南山。那老汉又问,今天咋进城了?张光源指指车上的红薯说,卖这来了。那老汉说,快进来坐,我给你泡。张光源说我捎的有馍,就要点汤。那老汉说,中。张光源跟卖羊肉汤泡馍的老汉是老熟人了,过去他做鸡蛋鸡换盐生意时,每次进城卖鸡卖蛋都要在这里喝一碗羊肉汤。这里的价钱张光源也清楚,一碗羊肉汤捏上一掇羊杂碎是一块钱,光要汤,一碗五毛钱。张光源舍不得多出五毛钱,五毛钱就是五斤红薯钱,而且要从百里之外拉到城里。所以他只要了两碗羊肉汤。张光源取出自带的干饼馍,他没有把干饼馍往碗里放,那样饼馍就会占去碗里的地方,汤就装得少了。那老汉舀上汤,捏了几颗盐续,撒了几颗葱花,端上桌。小山闻见香喷喷的味道,差点流出口水来。张光源跟那老汉说,这碗我再添两毛,你给加点羊杂碎。那老汉捏了一点羊杂碎放进小山面前的那碗汤里。小山把碗推到张光源面前说:“爹,你喝这碗。” 张光源说:“小山,你喝吧,你没吃过羊杂碎。”张光源把有羊杂碎的那碗汤又推到了小山面前。“爹以前常在这里喝,你尝尝。” 小山说:“不。爹,你喝。” 张光源说:“快喝吧,趁热。爹都喝腻了。” 小山低下头,眼泪落进了碗里。 张光源把干硬如牛皮的饼馍撕碎泡进两个碗里,饼馍在碗里慢慢变软了,但吃起来仍如橡皮。 “掌柜的,再添点汤。”张光源先把小山的碗递上。 太阳滚过中天,迅速向西边滑去,瞬间坠入山后,在遥远的天际留下了一片血染的云彩。张光源的红薯还没卖完,他推着架子车在工厂的家属区里串来串去,不停地悠着喊着。 夜幕降临了。高悬在电线杆上的路灯亮了。张光源蹲在一根电杆下,借着灯光数点着口袋里那些零碎的钱。张光源按面额大小分门别类,小山把银白色的硬币按大小分类重叠。不一会儿,一根根袖珍银柱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个两个三个……他们数着,点着,计算着,然后装在一个巴掌大的小口袋里,张光源把它紧紧系在裤腰带上。天色变得漆黑了,父子俩来到大街上。街灯明亮,行人稀少,只有那些不知疲倦的汽车还在呜呜地响着,在大街上忙碌地穿梭。张光源在一座大楼前停下,这大概是一座商店,紧闭的大门上方安有遮雨棚。 “今黑儿就歇这里吧。”张光源望着小山说。 小山点点头。 张光源把架子车推到门口,取出一个烂卧单铺在地上。小山实在太乏了,他一句话也没说便一头倒在地上,张光源还未躺下,小山就呼哧呼哧地睡着了。张光源怎么也睡不着,他在盘算着如何才能凑够给乔大富家交的第一笔钱。 夜深了。空旷的大街上既无行人也无车辆。街道两旁的路灯象牛眼柿子一样高悬在电线杆伸出的巨臂上,毫无生气地一眨不眨地放射着冰凉的光。不远处有座大桥,桥两边整齐地排列着两行大头娃娃似的柱灯,灯光炽白,不十分明亮。起风了。秋风带着寒意掠过城市的上空,吹得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树的叶子沙沙发响。小山冷得卷曲着身子,张光源把两人共盖的那个卧单叠成双层搭在了小山身上。嚓嚓嚓,清晰的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张光源警惕地睁开了眼睛,看见两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正朝这边走来。张光源立即又闭上了眼睛,他装着睡着了。脚步声越来越近,后来消失了。凭感觉,张光源知道警察就站在他们身边,但他的眼睛依然紧闭着。 “ 老乡,老乡。”警察轻轻喊道。 张光源翻了一下身,故意揉着眼睛。 “ 起来。你们咋睡在这里?”警察态度和蔼地问。 张光源坐起身说:“红薯没卖完,没地方去,就在这里过一夜。” 警察说:“在这里过夜不安全,天又冷,你们去住旅店。” 张光源跟警察的对话惊醒了小山,他微微睁开眼,见是两个身材高大的警察,赶紧又闭上了眼。 张光源说:“都半夜了,找不着旅店。” 警察说:“走吧,我们带你去。” 张光源说:“住旅店太贵,寻个干店坐坐就中了。” 警察把他们带到了附近一个小店,大房间,大通铺,只有铺板和席子而没有铺盖。一人一块钱。张光源算了算,一人一块就是两块,两块钱就是二十斤红薯,太贵了。于是张光源说都半夜了,俺们也不睡,就在这里坐坐,一人给五毛钱。店主是个老头儿,他看两个卖红薯的乡下人怪可怜,就同意了。店主收了一块钱,还是给张光源和小山一人指了一块铺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