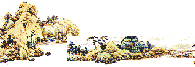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Ļ�������˶�Խ��Խ�ף������ĺ�����ӿ���ȣ����������С����˵��������ɽ����֮���������֮��ϯ�����ϱ���ϴˢ�������ÿ�����䡣ѧУ��ȫ����ͣ���ˡ��سǵ�ѧ������������ǣ�һ���һ�Ӷӣ�������û��ñ���µľ�װ�����ź����ף����Ŵ���죬�����������������������ʵΰ������ĺ��٣����и����Ĵ�������ɽû�вμӣ��������̸Ǿ��ص��˻����������������˳�ͷ������������������ׯ�����ճ����������Ϣ��������ֿ�����ζ�����ۣ�İ��������Ϥ������ʹ��ɽ��������Ϊ����������üͷ��������Ĭ���ԣ����������Ҳ���л�˵�����ص������Ͷ������Ͼ����ϵIJ���죬û��ô�ɽ�����Ե������ˡ��Ź�Դ�����ӻ��Ϳ��������ͳ����ս����ݣ�������Ц�Ķ��Ӵ�ɽ�����������һ������IJ����ͽ��ǡ����ǿ�ʼ��ĥ���ӣ���ɽ����զ������ĥ������ĥ��ȥ��������ͻȻ�����ˣ��������Ӵ��ˣ���Ȣϱ���ˡ����ϵĶ�˳�����Ǹ���ɽͬ������һ��ǰ�Ͱ�ϱ��Ȣ�����ˣ����ϱ���Ķ������ѿ�����һ�ڴ��������������֮�������Ÿ���ɽ˵ϱ����˵ϱ���ɲ��Ǽ������¶�����Ҫ��Ǯ���ġ��뵽Ǯ���������ַ����ˡ�����������Ϊ����ɽСɽ��ѧ��ѧ��Ҳ�Ƕ�ץ���裬����û�з��Ļ��ס�ķ���Ҳ��é���ݡ�ÿ�����죬���Ź�Դ���ļ��ڣ�����µľ��������꣬������£�����С�£�������ס�ˣ����ﻹ�ڵε��ડ�ÿ��������������ҹ����������˯���ġ���һ�����������������ʮ���죬���ǵ���������˹������裬���ϰ������룬�����������ﻹ�������ƴ�һ��ɵĵط�Ҳû�С���ҹ�����µø����ˣ�һ�������ĵ��������������Ȼǽ�ϵ���Ƥ����һ������һ����������Ź�Դ�ı��ϣ�һ��������ֽ��ٽ��ŵ����źں������ݶ��ͱ���ˮ��ʪ�˵�ǽ�ڡ�����˵���������ߣ��۵����˼�ȥ���Ź�Դ˵����ȥ�ɣ����ڼ������š�����˵�����ⷿ�ӵ����ӹ����ˡ����Ź�Դ���˿������ֿ��˿�ǽ��˵���ߣ����ǿ��ߣ�����֪���Ź�Դ����˼����������Ҳ�Ǹ�����ү�ǣ������߷����Dz����������ܵ��������˼�ȥ��������Щ�鲻ס������������Ҳ��ȥ������˵���߰ɣ����������˼��ֲ��DZ���˼ҡ��Ź�Դ˵��������Ҳ��ȥ������˵�����ڼ������Dz����ġ��Ź�Դ˵����ɶ�����ģ��߰ɡ����ͼ�Ȱ�����Ź�Դ��������Щ����������ɽСɽ˵���ߣ����ߡ��ۿɲ���Ҫ���ӻ������ҹ�����������ܵ��˾˼ҡ������Ժ��߷������Ź�Դ�ܶ���Ŀ�ꡣ�������ȥ�ˣ�Ŀ����δʵ�֡������ⱻ�������ʱ������β�ͣ����������Ū������Ҳ���ҳ��ˣ����ӵ�ѧ�Ѷ��������⣬���ﻹ��Ǯ���߷�����ɽҪ˵ϱ����Ҫ��Ǯ���Ź�Դ�ܲ�����Ź�Դ�Ĵ����ޣ�������ý�����ǵ�����Ǯ�������¹�ȥ�ˣ����ǰ���û��һƲ�� ���ڵ��ˡ����ӹ��꣬���˹��ء��⻰һ�㲻�١�Ϊ���ð����������������ֻ�������˼�ʮ�������մպϺ����������⣬�������������ײˣ�����Ჷ�������������Ǯ���������괩�����ѣ������緭ϴ���ˡ��µ�ûǮ�ɵIJ�ϴһ�·����浱�µĴ����������˼ҵ���취�������һ���컹û��������ı���������һ������žž��������������û����ڣ���ɽСɽ��û����ô�磬ֱ�����ͻ��ͷ�ԣ����������ۣ��Ჷ���ײ�һ���������˲��������㾴���Ⱦ���������ү������ү�������������ˮ¥̨Ҳ���ȵ��£��ο�����ү���¶�ʮ���վ������Ժ���ȥ�ˣ���һ����Żع������飬����Ҫ¡��ӭ�ӵġ���Ȼ��ӭ������ү���͵������ڡ����������˳Եģ�ǮҲ���ù��ˣ����Ծ�û������ڡ�ӭ������ү��û�б��ڣ����ֻ�ӭ��ʽ���Ե�������Щ���Ź�Դ���µ���������ү����������ү������ǰ���Ϲ�Ʒ���������㣬һ�����Ⱥ��ͷ��֮��ɽ˵��Сɽ���������Ƿ��ڡ�Сɽ����Ϊ�棬���Ŵ�ɽ�ܵ�Ժ������������ɽ�ӿڴ����ͳ�һ��������������˵��������ڡ�Сɽһ���dz�ʧ����Ťͷ���ߡ���ɽ˵��Сɽ������ߣ���ȷ��ڻ�����������ɽ˵��������������ž�ž�ֱ�졣Сɽ˵�Ҳ��š��Ź�Դ�ͻ��ͱ����ڿ�����������ɶ��Ϸ�������龰������Ť����һ�ߡ�����˵�������ɣ���ʳ�����ˡ�һ����һ�˶���һ���ʳ�������ꡣ ����գ�������л��ˡ�ʩ�ʣ��ҵ�Ϊ��������������˵����Ҷ�����������������ˣ����Ƹɿݺ�����������������֦��������˻ƶ���Ĵ������飬�����ܵ��۾�������ϲ�ظ������ǣ��������ˡ��������ǾͰ�������ָ���ڸո���������������æµ���������ǵ��֣�ͨ����һ�����������ѣ�һ��Ů�������֡�һ˫˫һ�Զ��ڵ���һ�ֶ��ſ������ֳ��������������ϵ�ʿ������Ů���䣬�ɻ�ۡ���Ա�ǻ����ͷ�ģ��������ֵģ���˵��Ц��СɽҲ�����м䣬�������ֵ������ӡ����죬Сɽ�յ���ͷ�����ӾͿ�������������������˹���������غ���һ��Сɽ�硣��֪����������������֣���Ҳϣ�����Ӹ��������֡�Сɽ�����������������Ľ��������ʱ����һ����˿˿�ĸо������ָо�����Ѫ������ѪҺ��������ȫ��������˿˿�������֣��Ǹо��к���һ�����Ա������顣˵ʵ����СɽҲ��С�ˣ�Ҳ����̸����Ȣ�����䡣����Ҿ�ƶ������ͷ��ѹ�Ÿ��������ɽ�����Сɽ��δ��������¡����û���ף��ܾܵͲ���̸���£����û���ޣ����þͲ����ȳ��š��������汲�����������Ϲ�أ���ֻ�Ǽҹ棬��������Υ����������үү��үү���������ֹ���Եĵ䷶�� ��˵��үү��үү�Ǵ����������ֵܣ��ϴ���ž����϶������ϣ��������ţ��Ҿ�ƶ����һ��ݷ����©�����˹�˯һ�Ŵ����ž������ʮ�������˸�������ף�����Ҳ�Ѷ�ʮ���꣬�����˸�����վ������ͱ�죬�ۿ��ٹ�����Ҳ�������������ʱҲ���߳��˹�Ů������������֮�⡣�ž��dz��ż��������ֵܲ��ܾ������������ҵ����Ҫ�����������϶�������֧�˵���𣬽��������������������ܵظ����������������ž�Ȱ�ܵ�����˵��ϱ�������ϲ���Ӧ���ž����Ĵ���ý���˷����ޡ����첻�������ˣ������ҵ���һ��Ը������ϵĹ�Ů���ž�һ˵����������Ӧ�ʣ�˵���ûȢ��������ռ�ȣ��������ּ���������������ǽ�ϡ��ž�����ֻ�����ա������ϵĻ�ʹ��������������һ�죬�ܾܵ�һ�첻Ȣ������������ˣ��ܾܵ������ԡ�������һ������ºڵ�ҹ���ž������˱�������̶�������������¿���Ȣ���ˣ���������λ����Ȱ�������ճɻ�������֮������Բ��ӣ���ҪΪ�����Т���ꡣ����֮�����˸��������ף�����˵���δȢ��������Ȣ����������������˼���������˵��һ�����ף����ϰ�������ķ��װ�Ů�˵�ʬ�������ʬ�Ǻ�����һ����ʱ������Ҳ�����ʮ�ˡ�������Ȼ���ˣ������ϵ���Ʒ����ȴ�����˷�Բ����Ĵ��կկ���ж��˲�������ŮŮ����һ����������ж���������ý���Լ��Ĺ�Ů�������ϡ������ֵܵĹ�����������������Զ�ĵط���Ϊ��̸�������˹�ȥ�ˣ����ž�������Ȼ���żҴ����ֵܹ�ϵ�ĵ䷶��ÿ����������ֵܲ���֮�£������Ƕ������ž������ϣ������ǵ�����ϸϸ��˵һ�飬���������ֵܾͻ��ƿ����ԣ������ѵ���������Ǹ��ÿ��ũ������ʮ�������ʮ�����Ϸؼ�������ӣ��Ҽһ��������Ծ��ظ��ž����ϵķ�Ĺ���������������㣬���������ż���һ��Ƭ�ص��о����ž����ϵķضѴ�Ҳ�����������ض����ۡ� Сɽ�����������֮�⣬������һ�����ǣ��Ǿ�������������һ����ġ�һ����ij��ף�����������Ҳ���������Թ��Ƕ�����IJ�����Сɽ�����Ӷ��dz�������Թ��Ƕ����꣬����������һ����÷�������మ���������ˣ����˾�ȷ����������ϵ����Ϣ�������������һ��ը����СС���Թ���ʱ���۷ף�˵�����˷���ף�������ɥ������˫����Ͷ�����������ˡ���֮˫����ͥ�������ԣ��������������ζ�˫˫������ˮ�⡣��˵��ˮ��ʱ�����DZ�������ȥ�ġ����ǵĵ���ʹ���ܶ��˶������ˣ�����һ����ˮȥ�ȡ���˵��������������һ����һ������������һ˫����Ȼ���ؽ���Ϊ����Ļ��������Dz�����Ϊ������������ϧ��Ϊ���������˱��ˣ�������һ�ֻ��������Ŀ�С���������ʬ���ˮ��Ư����������Ů���Ҹ��̸���ʬ�壬����ʱ���ײ��õĶ�����ľ���ӡ�������ľ����������Զ�����ף���Զ��Ͷ���� ��Сɽ�磬������ɶ�������Ӽ�Сɽ�������ص������ʵ��� ��û��ɶ����Сɽ����������һ����һ���������ѡ� ��û��ɶ������ˡ�����������Сɽ������ �����û��ɶ���� ����˵�����ˡ������Ӳ�Ц�ˣ�Ҳ���ٿ�Сɽ������ͷ���������ѡ� ��Ĭ�����͵ij�Ĭ����ͷ�н������������ţ��������ϴ�����Ů��Ц�������� ���㲻˵�Dz��ǣ��������̲�ס�ˣ�С���ʣ�������ǿӲ�� ���Ҳ�֪����զ����˵����Сɽ�����������ˣ����ò��ش����ӵ��ʻ��� ����զ���զ˵�������ӵ���ͷ�� ����������������ŵ���ꡣ��Сɽû������˵������˵�Ļ��������ڱ߹��˸������ ��������⣿�����Ӳ������ʡ� �������⡣�� ������������ɡ��� �����ٴ������˳�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