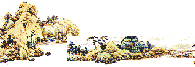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ˣ���������һ����߶�Ĺ����ڵ��ϲ�ͣ���û���С���������߽��˻���������Ҫ���Ź�Դ��ȥ���Ź�Դ�����������������ŵط�������Ǹ�Ϲ�ӣ������ģ�������һ�����紮��������һ��ʮ����Ϥ�����Ƕ�������Ĺ���Ҳ�������Ź�Դ�ļҡ� �Ź�Դ������ľ������ˡ�һ����ʲô���������������ж����Լ����˲��������ر��Ǿ������ˡ��������ж����Լ����˾�����������֮�ˣ���������Ǿ��ӣ����������������Ҳ�ͳ���С�ˡ�С����û����Ը���ġ����Ҳ�����ϴ����Ľ����ˣ������˶��Ǻ��������ģ��Ź�Դ�ȹ������������������Ź�Դ��������ġ� ����ճ�ʦ�����ڼ��ſڰ���̯��������̫���ᣬû������������ܲҵ������Ϊ�˶�������Ǯ�����������ˡ������������Ķ����Ķ����Ķ����Ķ�ס�����궬�죬��ѩ���������������ʱ����·������֪��ãã��ѩ����ת�˶���Ȧ�����ȵĶ���ʹ�������õ�����赹��ѩ����ʧȥ��֪��������ʱ���������Ź�Դ�ļ����������֪�������Ժ��������顣 ���ı��������ƵĴ����������ĵؽ��Ŵ̵��������ۣ�������ѩ��������裬����Ʈ�������֮�ϣ���ѩӯ�ߡ��캮�ض����������š� �������ˣ���ɫ������������������������������������ʱ���ߵ����ſ����������͵Ĵ���Ӵ�ɽ���سǶ��飬ס��ѧУ��������Ż����������棬����ֻ������С����Сɽ�� ������զ����������ʱ��������������������� Сɽ�����ケ�ǵ���ɫ��֪�������ε����������Ѿ������ˣ�������������ͻ����ˣ���γ�ȥһȥ�������죬������ʱ������������Ӱ������������������˵զ�ܽ��˲��Ľ������˲��ż��� ���Ͱ���������������Ϊ�Ź�Դ����ů�����ġ� ���ҵ����뼹�Ͽ�����������˵�ž������ߡ� ����Ҳȥ����Сɽ�����ܳ��ݡ� ����ͷ���䣬����ڼ���� ��������Ҫȥ����Сɽ��֡� ��������Сɽ��������ܲ�һ����С�ֳ��˼��š�����ˡ��ีؽ��Ž��������Ƶ�ѩ��������ת��������˴�����������������ͺ�Сɽһ��һ���ؼ��ѵ����뼹Ų���ų��صĽŲ�������������ƽ����ѩ����������һ����СС�ĺڵ㡣��������ѵ������˱��뼹�� ���뼹�ǻ�����������ߵ�ɽ����һ�ϱ��뼹�����۴�����С·����������Ƕ��ܿ���--��˵���ǰ����ӣ����ˣ�����ʱ��������˶��ܵ����뼹�ϣ����ϱ���ʯͷ������ӾͲ������ϳ�--���ϵķ���Ķ���������վ�����ȡ��Ƿ������Ƥ�Ƶľ͵ش����������ϲ���ѩ��������У�������Ʈ������ѩ���й���һ�������ɳ��ʯ�Ե����������ۡ�����̧���ַ���ü�ϣ��ڵ��������ѩ���۾�ʼ�����ű��뼹ǰ��������С·����Ȼ�����˵�˵����Сɽ���㿴���Dz���������������ˡ��� ����ϲ����ʤ��Сɽ˳������ָ�ķ���һ����Զ��һ��ģģ��������Ӱ�����������ɫ����������Χ��������һ��СС�ĺ��Ӷ������������뼹�����ƶ��� ���ߣ���Сɽ�������Ǹ��˾���Ҳֹ��ס�˷�������ק���������С�ڵ㷽��ȥ�� ���̹��̣�����ӯ�ߵĻ�ѩ�ڷ���Ľ��������ź��������ضԷɱ��������ʵʩ�˱��������ǰ����ˣ��˵���ѩ���ϣ�˫�ְ��ŵ�������������մ����ǰ��ѩ���ּ�����ǰ�ܡ�С�ڵ�Խ��Խ���ˣ�������Խ��Խ���ˡ���Ȼ��ɫ�����ھ���������ѩ��������ڿ������Ǹ�С�ڵ�����������ˣ�СɽҲ�������Ǹ�С�ڵ�������������ͼ����������ϵĵ��ӳ��أ��������ǣ��������ص�˵������ô�ˣ����û�Ѽ���������Сɽ֪��������ȥ���������ǿ�����ȥ�����ӻأ����ʱ�ǿ����ӣ����س�����������ɽ�����ɼ��͵�����������������Ǯ��Ȼ��ؼ�Ъ���죬��ȥ�������˶����������⣬������ʷ�����ڶ��������ص��ӻ����ģ�����Ȼʮ�ֵ��ġ� �Ź�Դ��һ�������ص��ӻ���ʱ��ǰ�����죬СɽҲ������һ�����ʱ�����뼹���ӵġ���ʱ��ֵ�����ˬ�������ֺã�������ɽ����ϼӳ�գ�Сɽ����߸����˵س��ţ����ϱ��뼹����ʱ�������Ѿ����գ�����ϰϰ���¹����ڣ������վ�ڸߴ�������ɫ����ԡ����磬�۾�������Զ�����ڴ��ŵ�����Ӱ��վ�˺ô�һ�������δ�����������Q�ˣ�˵��Сɽ��������ǰ���ߡ�Сɽ˵���С�������������±��뼹��������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