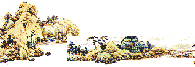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軨�IJ��κ��ˣ����Źⴺ�����ҽ���� �Դ������Źⴺ�ڴ����������軨��������þò���ƽ�����軨�����軨������軨�ľ�ֹ������ʱ�������Ժ��лε��������ı��軨�ķ��Է���˻ҧ�ţ�Ū�������ۡ��軨������ͷ������ͷ�����е����ڱ��˿����Ƿ��˷���Ƿ軰���Ƿ軰��˭Ҳû����������軨�������ģ�������̣�˵ġ�����̣ǰ�IJ軨������Ƕ䣬�������⣬������¶���������ţ���Ө�����������˺ܶࡣ�ر�����Ⱥ�����ˣ����ڲɻ����۷䣬����Χ�Ų軨�������ˡ����ڲ軨���Ǹ����Ƕ䣬û�п��ţ������۷�Ҳֻ��������Χ��һ�ɣ��м����������������Ʒ���������ۡ� �ŹⴺҲ���������Ҳֻ��������ѡ����������������������ϣ������е�����Ů������Զ�Ȳ軨Ư�����ο��軨���ڷ��䣬�ŹⴺҲ��Ī����Ҳ�ͽ����ص����ˡ� �δ��������������Dz��ϵ���Բ軨Ҳ���зǷ�֮�룬�Źⴺ����������ġ������������Ժδ����Dz����ġ�֮�����������̺δ���������Ϊ�δ��������ĵ����ɽ��������ĸ���һ��ʱʱ�������ҡ���Ҫ�����ˣ��δ��������ֵ��ϣ�����ȼ�����Ҫ�����ˣ��δ���������������ޣ��������ˣ��δ����������ް����������Ե��ǿú����ϡ��������سǣ���ʡ�ǣ��������������Ǻδ����ڴ������ϣ��Źⴺ�벻���δ��������Ծ������̺δ������������˲������������̩ͨ���������ر��Ǻδ����Բ軨�Ĵ��ѣ��Źⴺ�ǿ��������������ġ�����軨�����軨�����������������͵��������Ķ�Ů����̣�������������ף������˾ͳ����������Źⴺ�����ս�����IJ軨����Ȼ�������Σ�����������һ���촽���Ѳ���������ȥ�����˹�����Ǻ����Ϸ�����һ���£�������ͷ������Ĺ�������Ҳ�ͺ��ٻش壬������ط��ڶ�����Ҳû������������ ���죬�Źⴺ�ػ������Һδ�����·��С��������ʱ��ͷ������ɹ��������ͷ��������������С������έ�ӣ��������·����̹⣬���紵����ɳ���������ŵ�������ɫ�IJ��ˣ���������έ�е��Ǹ�Сˮ̶�����뵽έ�У���СȪ�ߣ��ȿ�Ȫˮ��ϴһ�������������졣��������Сˮ̶ʱ������̶�ߵ�ʯ���Ϸ��ż�����ˮ���ݹ������ѣ������¿���û���ˣ����룬Ҳ��ϴ���ѵ�Ů�˽�έ�﷽��ȥ�ˣ�Ϊ�˱������Σ�����СȪ������һ��ˮĨ��һ������������һ�����˹��˺��˼��ڣ�˦˦���߳�έ������Ȼ����һ���˻Ż����Ŵ�έ����һ������ܳ��������Ƶ�˳��ɽ�����������Źⴺ̧�����������ڶ�ͷ������������ϸһ���������Ǻδ������Źⴺ����ֱ���ֹ�������ˮ̶��ʯ���ϵ����ѣ�����������š��Źⴺ�������߽�έ�����뿴�����������δ������˺�һ���ˣ��Բ������˵�Сˮ̶����������έ���ȥ���Թ�һ����έ�ж�����������������������ڿ����ˣ�����Ƭ�����������������һ��Ů�ˣ�˯�����Ƶ�һ�������������Ღ��έ�ӣ��������Ǹ�Ů�˿���������Խ��������������Խ�����������Ǹ�Ů�˺�Ȼ���𣬷��������ڿ��������ƿڴ�����һ�٣�������ô�죿Ȼ�������ĵ����Ƕ���ģ����ھ���Ů�˼���֮��ĵط��ݷ��˺ô�һ�������Ů����Ȼû�ж�������έ��̫�ܣ�������һ���赲���������ߣ���ֻ��ͨ��������ķ�϶������Ů�˵����Ӷ�ʼ����������Ů�˵������Źⴺ��������Ů�˿��������Źⴺ������Ů�˵���ʱ���������һ����������Ȼ�������軨�����϶����Լ����жϣ������ʱ�����˶Ժδ����ķߺޡ��δ������δ�����������������Źⴺ�����źδ�����軨�ڵ���§���ţ��軨�����治ס��Ť������һ����������������������һ�����͵ļ��ʣ���л��ӿ��������ڰ����ߴ���Ӱ˴���ķ�ʢ�IJ����ϴ�Դ��һ�������ﲻס�����Ų��ѣ������ֺ��ּ��������Լ�Ҳ����ȥ�������ڡ����ںδ����Ѿ��Ժ����ˣ�����ֻʣ���˲���ʣ�ˡ����������ڵ��ϵIJ軨���Źⴺ�ѶԺδ����ĺ�ת���������軨������ΪʲôҪ˳������˳�����ɥ���������������̶��Źⴺ�ֺ������Ϊʲô�����ںδ���ǰ�档�����ʵ���Źⴺ��������������Լ���һ��ʧ���ߣ����δ�����һ��ʤ���ߡ� �軨��Ȼû�ж�һ�£��ѵ������˯���ˣ��δ����ոմܳ�έ���������������˯�ˣ��ѵ����Ͳ��·����������飿Ů���Ǻܽ����ģ��ر���û�г���Ů�ˡ��軨�����������ֵز���һ���Ǻδ�����ȡ�˷dz��ֶΣ�Ū���˲軨��Ȼ��Ŷ����֡��Źⴺ֪���軨�������Ǹ��ҵģ���������˳�Ӻδ�����ֻҪ�����������������ͻᷴ�����ס������Źⴺ�ó�һ�����ۣ��Ǿ��Ǻδ���ǿ���˲軨���뵽����Źⴺ��Щ���£��������ߣ����軨��ԲԲ��������������߸�������鷿���ε�˩ס������ʹ�����߲��ܡ�����û�������ļ���ʹ������֧���������������͡��δ���ռ���ȣ���Ҳ���Դ��˳ˮ�����Źⴺ�����һ�������˲軨����ž��һ�������Ķ���������������ϡ��軨�����ˣ���һ�������۵ɵ����˿��¡��軨������һͷĸʨ���ִ���ץ������š����Ů�˱Ͼ���Ů�ˣ�Ů�˵������ٴ�Ҳ�������˿��⡣�軨���Źⴺ������ѹ�����¡��軨��һ�λ����ˡ��Źⴺ�ӳ���έ����û�лش壬Ҳû�лع��磬������ͨ���سǵ�·�ϱ�ȥ�� �δ����ӹ���ص������������ع����ֵ����������ɵ���ȥ�� �Źⴺ���سǻص����磬Ҳ�������ɵ�ƭ�������ǵ��۾�����Ȼέ�����������Ľ�ӡ����˭Ҳ�����뵽һ�����õĹ�����ǻ�ɳ�����������������飬���ο����������سǶ�����δ�ع��塣��Ժ���кδ������죬�ŹⴺҲ�ڷ�ͥ���δ��������ұ绤ʱ��ϸ��������������έ��������飬ֱ����ʱ���Źⴺ��֪���δ�������û�����軨�������Լ������������ﷸ��Ȼ������ͥ����֤�ݵģ��δ���ǧ�����˵�Լ�û��ǿ��軨��������ָ���ֳ���һ�����˵Ľ�ӡ��˭���µģ����ο������������˵Ľ�ӡ�������϶���һ��������������ǿ�鷸��Ҳ���Ǻδ�����Ҳ������һ�����ˣ�Ҳ���������ǡ��δ������ұ绤����ٸ����������IJ��⣬�δ��������Զԣ�ֻ�ǿں�ԩ���������������δ������д�����ͽ��ʱ�δ�����ɫ�Ұף������ƵĿ���ԩ��ԩ����ʵ����ԩ�������δ����ڴ��С���б������ߴ�����ķ���Ѻ�����̳����Źⴺ���ڷ�ͥ���������е�ȫ���̣�����ʱ������ͷ�������¿������ټ�����Ϭ�����۾���Ҳ��Ը�����δ����DzҰ���ֽ����ף�����������ͻȻ����һָ���������������ﷸ�����������뿪��ͥ�����������ټ��ٵ�ע�⣬����һֱû�����Źⴺ���ڷ�ͥ������̺�����ڽ������������С����н����ˣ��Źⴺ��Ϊ�Լ����ѷ��������ң���Ϊ�δ�����ԩ���е��������軨���ˣ�һ���������ŵĻ��ٿ�ή�ˣ��Źⴺ����е��Լ��������أ����ǿ�����ʱ�̲��ܵ���ĥ��һʱһ��Ҳ�ò���������һ�������˺��£����˲�֪�����Լ�Ҳ�İ����ã�һ���˸��˻��£����Dz�����¶������Ҳ�ᰵ���ܵ�Ǵ������������������Źⴺ�����ܺ�����ڣ�Ҳ�������ܺ�����ڣ����������ܺ�����ڣ������ܺ��߲���һ���˶��������ˣ������Źⴺ���ij����ܵ��ӱ�����ĥ���Źⴺ�ڹ��統���ʱ��һ��ææµµ�����ٻؼң�û�����軨��Ҳ��û����ô�ࡣ�������ص��˻��������ص��˼����軨�ǵ�ͷ����̧ͷ����ֻҪ�����ţ�һ��Ҳ�����⿴���軨�Ƿ����IJҾ���ÿ�ο����軨�����ӣ������ľ�����������˻ҧ�ţ��������ܣ����Է��ۡ��������������軨��ҹ��ֻҪһ�����۾������Σ��ε������廨�����������̨���δ���վ������ҧ���гݵ�ָ������ݺݵ�˵������ֻ�Ϻ��꣬����������������ε����������λε�������һ������ij��صĽ��ͱ�Ѻ���̳�--��ӱ���Ƭ��ͺͺ�IJ�������ʯ�ĺ�̲������ʱ�Źⴺ�����лᷢ��������״�ĺ������ŵ������ű�����ֱҡ�Σ����ﲻס�غ��������ѣ������ѣ��������۷�����������զ����զ������˵ɶ�ˣ�������˵��û˵ɶ���㱻����ס�ˡ��ŹⴺҲ�ͷ����ˡ�����զ˵��ҹҹ�Ķ���ʹ�Źⴺ������ҹ�����ˡ��Źⴺ˯���þ�Ҳ�Բ��·�����Խ��Խ�ݣ���Խ��Խ�ƣ�������˵����ȥҽԺ�������Źⴺ˵��Ҳû�ã������Ż���Ϊ�����˲���֢֮����������ϴ�档�Źⴺ�IJ���ֻ�����Լ�֪������֪����ҽ����Ҳ�ǰ״�ʱ�����·���ð�Ǯ�����Բ���������զ˵����������զȰ��������һ�����������ڼ�����Ҳ��ȥ�����������Źⴺ��ʹ�����ĥ�пా�ţ��������ꡣ���������˺ܾ�Ҳ�벻������ʹ��ĺð취�����뵽���뿪������ӣ��뿪�ˣ���Ҳ�Ͳ����ˣ��۲�����Ҳ�Ͳ��ķ��ˣ��IJ�����Ҳ�Ͳ����������ˣ�����������Ҳ��˯�ð����ˣ�˯�ð�����Ҳ�ͳԵ��·��ˣ��Ե��·�������Ҳ�ͺ��ˡ�������һ���뿪���ӵĺô������ź�Ȼ�����뿪��������������ȥ�أ� �Źⴺ����Ժ����۴�����������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