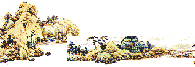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δ����ڲ軨������䵹��������һ�����ʲôҲû�ҵ�����һ��մ���������Ҳû�С���������������Ҳ���뵽�˵ġ���Ҫ�Ѳ軨��������ԭ��ġ��軨�⼸�곤���ˣ���Խ��Խ�ÿ�������Խ��Խ������һ�μ����������飬������Խ��Խϲ�������Ů�ˡ��ɻ�δ���Ҳ�������ɵ����ɵģ��ɲ軨���Dz����飬����û����������ɫ������Ҫ˵Ц���ˡ�����֪�������Ů����һ�쵽������ɶ������ͨ���Ѳ�軨������ֵ�ʲô���ܣ��ɽ�����˹�Ů���õĶ�������һ��д���ֵ�ֽ��Ҳû�������δ���������ȥ����Ȼ������̨�Ϸ���һ��С���ӣ�����������������������Ȼ��Ѿ��ӷ��������۾���ʱ������������ӵı������һ��С��Ƭ����Ƭ�������øֱʹ���������д���ĸ��֣���ҵ����δ���֪�����Dz軨Сѧ��ҵʱ�յġ�Բ����Բ�ۣ���������С���ӡ��δ��������ֿ����������֣��������ߣ����Ҳ������ߵ����ɣ������ò����¡��δ����߳��軨���ݣ���������վ���Լ������ſڣ�����б�����ſ��ϣ���˫����Ϥ��Ҳϲ����������һֱ�������� �δ���������������ݣ�����һ�Ŵ���һ�����ӣ�һ�����ӣ�һ��ľ�ʣ��Ȳ����ӣ�Ҳ�����������룬һĿ��Ȼ����������Ȼ�����ſ��ϣ�����������δ���û�����Զ��֣�������ľ���ϣ�����������ȥ�ѡ�һ����������ľ���������²��������£�û��������������Ҳ�������ˡ���һ��������ȡ����ǽ���Ϲ��ŵ����������ѣ��������ѵIJ���������������ľ���ӣ������ְ����ѹ��������档 �δ���վ������˵����ûɶ���߰ɡ�������������Ӧ���������ţ��δ�����̧�ţ���Ȼ����б�����ſ��ϵ�����������Ŀ�������������������Ȼһ����һ������״����д��ĵ���Ȼ��������������ȥ���ţ������Ͼ��������δ���֧�������������ˣ�һƨ�������������ϡ�������������ڴ����ϣ���δ�������档�����Ѿ��м���û����������������ˣ�����ͻȻ����һ���������е�İ�����㿴�����ҿ����㣬һʱ��֪���ôӺ�˵�� ����������������鵱�˴���ĸ�Ů���Σ���������Ĺ����ӵ�����һ����������Ȼ����һŮһ��������������ʰ��������Ȼ���з��ϣ�����ǰһվ����Ȼʹ��Щ����������Ƿǡ������鱾�����Ի��ã�ϲ��������ϲ˵��Ц��������֯��Ů�ǻ�����������졷��Ť�����裬���������������ߣ�������Ůƽ�ȵ�˼�룬������Ů�Լ�����Լ����ſ��Լ����ŵ�С�ţ���ȡ������������ ��ϲ��ϱ���Դ�ű���������Ϊ��Ů���⽨�ĵ��ͣ��Ĵ��������Դ����������������ϣ����С��Ͻ������ŵĺ������������ŵľ������Դ��û����飬˵����������ֻ˵�����ۣ�����ܲ��졣�Դ�Ż����˸����ӣ�˵���Ų���û��ã������˼Ҵ����ݣ����߽��������һ����ڹ�����֪������ڹ�Ϊɶ��������˳�ۣ�������������ڹ����ˣ��ŵ����������ﶫ������ζ�����������ؽ���һ���ͱ��˹����������Ⱦ��ܣ���Ϊ���˽ţ��ܲ��죬û�ܼ����ͱ���ڹ������ˣ���Ҳһ�����������ڵ��ϣ�ˤ�˸�����ʺ����ڹ�������С�ȶ����Ϻݺݵ�ҧ��һ�ڣ������Ӷ�ҧ���ˣ��������ڶ�����һ���̡��Դ��˵���������ȽŽд�ҿ��������ǿ鹷ҧ�İ̡��Դ��˵�����찳�Ӿ˼һ������Ͱѹ��Ų����ˣ���������š����ﲻ����˵�������У����Ű��Dz����ɣ������������ʹӼ������ˣ��ܵ�һ��ɽ�����������������������������Ҳû�ҵ�������������ʵ��̫���ˣ����������������������һ�������ͣ�����̲�ס�ˣ��ֻص��˼ҡ�����������˵�����Ӳ���������ˡ����������˵�����������˾�û��Ҫ������������˵��û��Ҫ�۾����š����������˵������Ҳ��������һ���ӡ�����������˵����һ���Ӿ���һ���ӡ����������˵���ǽ�����ס�Ķ��顣����������˵�����Ķ��鵽ʱ����˵��������������˲�����һ�ء������������ˣ���ϲ����Ȣ�˰�����Ȼ��ϲ����ö����죬�����Ӱ��Ŵ�Ҳ�Ͳ��������ĩ�ˣ��Դ��˵�����ž��Dz��ã�Ҫ�ǰ�û���ţ�Ҳ����й�ҧ��һ�ڡ����ǿ�������·������һ�����Դ��˵���ڸ�Ů����ǰ���������˼�����˵��������·������ϲ���첻�ϰ������꣬��ϲ����������Ҵ����ݣ���ϲһֱ����ǰͷ�����ں�߸��š��쵽�����ˣ���ϲ˵����ţ�ƽʱ����˵��Ŵ����ߵÿ죬���������������˭���ߵ��ҡ���˵�С����ǰ������������ʹܵ�����ǰͷ������˦���˺�ͷ��������Ϊ������ϰ���Ҳû������ֻ����·��˭֪���������ˣ�������û���ϡ��м�����Ů������͵͵��Ц���Դ�ſ����ˣ�˵�����DZ�Ц��������ġ�������Ժ�ӣ�����ͳ����ˣ����������һ���ˣ��ʣ���զû������˵��˭������˵���������Ů��������������˭��������Ů������Ц�ˣ�˵������ں�ͷ�����첻�ϰ����������ˣ����˿�������������û��Ц�� �Դ��˵�ú��о�����Ҳ˵�úܾ��壬�����Ͼ��Ǹ���ä��˵���������ϣ�Ϊ����̽�¶�⽨����Ը�Ů�IJп��Ⱥ�������������Դ�ŷ������ŵ���ʵ������¶�����������������������Դ�Ÿ����������ָ�㣬�����������ŵ��¶�˵�ø������������з��⽨�������ˡ���������Դ����Ϊ���⽨�ĵ��ͣ������Դ�Ż���ȫ���ĸ�Ů����������ݽ��� ���ڻ�������Ů���⽨�˶���ú�����ң���������ȫ��Ҳ�����������Ĺ����Ӹ���Ů�������Ǹ���Ա�������鼫�кøУ�˵�����鹤��������������ǿ������о�����������������������ܡ��Դˣ��δ������K�������������鲻������δ���Ҳֻ�ܿ���������������������Ĺ������Dz���˵�����ĵģ���Ϊ���ҵض࣬���ջ��ɷֵ����ߣ����ǵ���Ҳ�Ǹ�ũ�����ԣ����������Ĺ����ӵ��˳��������ϴ���Ц��ƨ���۶��ŵ�ֱ���ਡ����δ����ĵ��ܻ����£��Ѻδ��������������˹����Ӷӳ��������Ӷӳ��ںδ�������������ס��һҹ���δ�������ijɷ־ͱ��������ũ���δ������Ǹ���������õĹ����Ӷ�Ա�����������Ӹ������Ӷӳ��չ��˼��䣬û�����죬�Ǹ���Ա�;����̸Ǿ����ˡ�������Է���ش����ˣ�˵�Ǹ������Ӷ�Ա���������е��Ǹ����������ӿ����ˡ�Ϊ�ˣ���������������˺δ���һ���ʡ����Ľ���ʱ��չ��һ����Ա�������Ӷӳ��������δ����������ˣ��δ���Ҳ��˳˳���������˵����ʶ���֮�س��˵�Ա����������Ȼ�������гɼ�����Ϊ���Ǹ�������Ա���л��������뵳������ͱ������Ӷӳ�ѹ���ˡ����Ĺ����ӳ���ʱ�������������˳����磬�δ������˳������糤�����죬�ν������Ź�Դ�ֽ���ɽ������ȥ�ˣ��δ����������龭����һ������Ա�����һ���糤��һ����Ů���Σ���һ���ٶ࣬Ҳ����Ȼ�ģ������ģ���ָ��ģ��������ڿ��ᣬ�����о�������һ�죬�δ����������������Ͽ��ᣬ������Ϸ¥�����һ��Ϸ������ʱ�Ѿ�С��ҹ�ˡ�ҹ���˾��������������ĵġ�ֻ��С����֨��֨����֪ƣ��ؽ��ţ����ž���ɽ�������һ˿������ͬʱҲ�����������⡣ �δ���˵���������䣬�۵�����������ȣ�ůů���ӡ��� ������˵����̫���ˣ����˰ɣ��������ȥů���ѡ��� �δ���˵�������Ҹ���һ��ů���� ������˵�������У������Ƕ��ڼҡ��� �δ���˵������ɶ�����ǿ϶���˯���ˡ��� ������˵����˯������Ҳ������һ��ů���� �δ���˵������ů�Ͳ�ů����ֻ�������ȡ��� ������˵����˵����ֻ�����ȡ��� �δ���˵���� ˵����ֻ�����ȡ��� ���˻ص��ң������ݣ��δ�����Ҳ�����ˣ�����������������ϰ���������������˵����˵����ֻ�����ȡ��� �δ������Ų��ţ�˵�����Ҳ������ˣ���ֻ����ů���ѡ��� ������Ť������Ҳֻ��˳���ˡ� Ū���ˣ�������˵�����������߰ɣ���������ˡ��� �δ���˵�����е����У��ٵ�һ������ⱻ�����Ⱥ����� ˵��˵�ţ�����������һ�ء����ڹ���ƣ������֪���������˶�˯���ˡ� �ϸ����dz��£�Ҳ�Ǿ���ҹ·�ɡ��ν������Ź�Դȥ��ɽ�����ض��������죬ƫƫ���������ɽ���꣬����ȥ���������Ӽķ��ڳ���ŵ�һ�����Ѽң����˿��ַ������ˡ��ص�����������û�нС��ν������˵������������˺δ���������������Ρ� ������ǿװ���ʣ���˭ѽ�����������к����������εľ��š� �� �ҡ����ν����ش� �δ������������ʱ����һ�ţ���æ���ҵ��ڴ��϶�ץ�������ν����Ӵ������������Ϸ���ϤϤ���µ����������һ������֪���������ʲô���顣����˳�ֵ��������ſڵ���ͷ���ݺݵؽ�������һ�¡��������������쿪�ţ�ĥ��ɶ���� �δ����ŵ�������Ҳû����������������˴��¡� ������û�е�ƣ�����Ѻν������ϴ���˵�������ϴ��ɣ��ñ������ȵġ��� �ν���������ͷ�ѣ�˵����������һ�ף��ѵƵ��ţ��� ������˵���������Ϻ���������𡣡� �ν���˵�������������������š���˵�Ŵ��Լ��Ŀڴ����ͳ��˻���������ţ���ȼ���͵ƣ��ڰ���С�����ʱ���������� �δ��������ƹ���������è������ɸ����ֹ�� �ν���һ�۾ͳ���˴��ϵ����ѣ�����û˵�����е���ͷ��ͱ���˴��£���������������������յģ��� �δ����ŵö߶�������һ���������ӴӴ���������˳�ƹ��ںν�����ǰ����ͷ���ġ��ν������ˣ���������ֱð���ǣ�������ͷ��δ���ͷ����ȥ����������Ʋ��������ȥ������קס�ν����ĸ첲������˵�����軨������ɲ���Ū������������ �ν���������ͷ��һ���ƿ������飬ҧ���гݣ�����첲��ʹ��ƽ���������������źδ���������žž�������������⣬Ȼ���ַ���һ�����ںδ������ϣ����������Ҫ���Ķ������������ �δ������˴���һ��Ҳû�ио����ۣ��������ν���������ʱ�����������⣬������ɥ��֮Ȯ���������ӳ嵽���⡣������������������˳�ȥ�� �ν�����һ���� �δ���������ְ�� ��ʱ��ǡǡ�Źⴺ�ӳ���ս�����������γ������糤���������������˸��磬�ŹⴺҲ����˸����糤���ٺ��������������������������������ӣ��Źⴺ�����������Ӷӳ�������������ӽ����˵�֧�����Źⴺ��ѡΪ��֧����ǣ����������˾ͽ�����֧�顭�� �����Ժδ�����Ҳû��ȥ�ҹ������飬��û�л������������������������������һ�𡣸ղ��Ǹ��������ù���������ͱʱ���δ������ڵ����ϼ�������������ﶼ�����˸���������֪Ϊʲô���������Ǹ������˵Ķ����е�����ҹ�ν���ͱ���Ķ������Ǹ��������ջع��ӵ�ʱ�����̧ͷ����������һ�ۡ��¸������ˣ�������ҹ���������飬����������£����ս�ľ��������ˣ���û���ҹ������飬���Dz��룬���Dz��ҡ���û���������������������Ҫ����������ƴ������ȥ������ס�ν����ĸ첲����һ��ͷ����ȥ�����϶��Դ�������һ���ں��ˡ��Ǿ�û�н����ˡ���������ְ��������Ҳ����һ����Ĩȥ�˸�Ů���ε�ñ�ӣ������˶�����ƽͷ���գ�����ͨͨ����Ա��������˭Ҳû������˭Ҳû�л�������˭����˵����ǰ�������������͵�������������˵��¶�ʱ���ڰ�����û��֪�����������Ժ�ͱ������ˣ�����ͺ���Դ��ϵ�ʭ�ӣ������˵��۾����Ƕ��ŵģ���˵����������һ�𣬾������Ķ������ˣ�Ҳֻ�ܻ��һ�ۣ�͵͵���ϸ���ɫ��������˵������Щ����������ǰ����ˡ�������������죬�Źⴺ�������鵽ǰͷȥ������������������·��������ʱ�������һ�ۣ�����സ���õ������ϣ����Ź�Դ�Ͷ�ϲϷ����һ�١��������������ţ�������С���������������ҧ���гݣ����˾�˵�����˾��˵��������ĸ�����Ǻ��꣬���������ǰ��ǡ�����˵���б������۸�������һ����С����˵�������ǹ�壬�ǵط���ͺͺ�IJ���ׯ�ڡ��δ���������֪����������ׯ���ұ��������С����˵���������ĸ��һ��ɧ��һ��Ҳ�벻�����ˣ�û����������������˯���š��δ������룬��֪�����ν���������ȥ�ˣ���ʱ�һ���û��ȥ����˯��������һ����˯����˭˯��С����˵�������Ƕ����������������տ��Կ���ֱ�죬�����ǽ���ͷһ�����������۵��С��δ������룬�㶮���ѣ��������ò����۵á�С����˵��һ�����ڹ����ϸ�ݣ�������������ν����ڹ����³��أ����ų��ţ��ν���վ���ر������հ��Ƕ����ͳ����ɣ���������ܹ�ȥһ�ѰѺν����Ƕ����������һֻ�ֽ�Լ��Ŀ��Ӱ������˵��Ƕ������Լ����ǵط����������������������ҿ��Ŷ����ģ���æ�뿪�˹��ء��δ������ˣ�������Ȼ����ģ����ǰ�����˵���㶮�����ͣ���������������á�С����˵�����������ι�̣�ι��ι�ɣ���Ҫ�������������ߣ������������Ǹ����ŵ���ͷ���Լ�������������˵Ŀ�������ģ���ɧ�������Dz�Ҫ�������������Ҳ�Ҳ��š��δ�����֪��С������������ģ����ﻹ��һ�ɹ�ֱð��ˮ���䲻��ð����һ�仰�������˼������Ӹ���á�С����˵�ú����ߣ����Ҳ���о�������һ��Ҳû��˵�δ���������δ���������ְȫ���Ǹ���ƨ�����������飬�������������Ӳ��������ק�����ﰴ�ڴ��ϵġ� С������������˵�ýŵ�����ͷ��ðŨ�����IJ�ֵ��������塣�δ���ȴ˵����Ϊһ��Ů�ˣ��������ٻ�������ǿ������զ˵���������ܻ�����һ����Ůһ�����ӣ������أ���һ�������µ��ļ����ⳤһ������ɶ�á��δ����Ļ��ҵ���С�����Ķ̴���˵����С������ʹ����С�������������ֱ����ˡ��������δ����Ҹ㣬������ְ��С�������ö��ˣ����Ż�����ң�˵Ҫ���δ�����飬���������Ȱס�ˣ�˵��ֻҪ���δ�������һ�а�Ů���ͰѺδ�������˩ס�ˡ����˾��ǵ��ԣ�Ȣϱ��ʱ�䳤�ˣ�û����Ů���ľ������Ů�������롣С����һ��Ҳ�ǣ����ܹ�ֺδ�������ô�������ˣ���Ҳȷʵ�ø��δ����¸����ˡ�����������δ���˵����һ�������µ��ļ������δ������˻�˭��Ҫ�������ԣ�С����û�Ⱥδ�������������ӣ��ԹԵش���һ����ˡ������㰲�����ĸ��δ��������ӣ����㾫�����¸����������µĵ���Ҫ��һ��ĵ����δ�����������˭����С����С������������Ȼ���ڶ���С�����ĵ��������ˡ�С�������˸���С�ӡ��δ���������̬��Ҳ��ķ����˱仯��С�����о������Ե��Ǻδ���û����ȥ�������顣�ɱ����ǣ�С����û�뵽�δ������Dz������û�л���ȥ�������顣 ���ڣ��Źⴺ���˹��縱��ǣ��δ�����Ҫ��ɽ������������ˡ��δ�����ô�������������������������£��ع��ںá���һ�����ڵ����ˡ��뵽�ˣ��δ�������һ��һ��ϲ�ã����ϸ����˶������ټ����������е�Ц�ݡ���ʱ����ϸ�ش�����һ����ǰ�������飬������ԲԲ�ģ�ֻ�ǹ�������ǰ�ˡ��ۻ��������ۣ�ֻ��û����ǰˮ���ˡ���ë��Ȼ�dz����ģ�ֻ�DZ����ȱ����¶�ĺ����Ե���Щ��ɬ���仯�����ǣ����Ӽ����˶̷�������������ʱ�ͼ����˵ġ��۽�û����ǰ�����ˣ������˼���ϸ����˿����β�ơ��ز���ԭ���������߸������ɽ�徭�������ʴ�����������ƽ̹�ĸ�ԭ���δ��������������ⲿ�ı仯�����������Ѹ����µ�ʵ�����ݣ��������������������������ѩ��˶����鷿�����������װ�ð뱥�IJ���������ǰ���δ���������������������������Ϻ��������ı��飬����Ȼ������һ����ֵ��뷨������һ�����������ͷ���о�һ��ɽ���벼�������𡣵����������һ�뷨�����ʵʱ���������Ȼ���ֳ�������������ڵ��Ϻͺν����Ǹ߸߾������ͷ���δ����ij嶯���Ǹ߸߾������ͷ�����ˣ�����Ũ�����������գ����ĵ���������ʧ�ˡ��δ�����������������������ˣ�������ȥ�������������Լ���˫��ȥ��������ֻ��Ȼ�ǰ뱥����Ȼ���˵IJ����������ڻ�����֧�飬����֧������������ܺ����� ��ɩ�ӣ��Ҹ����ˡ��� �����ɣ���ɶ���� ����������鼫�临�ӣ��������Ҫ���δ���˵�����ֲ�֪�Ӻ�˵�𡣺δ���������ʱ�������۾�˿��û�лرܣ�����δ�������ӵ���������������ԥ��ӭ��ȥ���������źδ����ж������δ���ȴ�����ˣ�������û���뵽�ġ������������ʹ�ո�̧��̧ƨ�ɵĺδ����������ˡ������鿴�źδ��������Ŷ��ӷ��ޡ������Ǻδ����Ķ��ӣ���һ��Ҳû˵�ٻ���������Ѿ�ʮ�����ˣ�һ��Ҳ����ν����Ǹ���ͷ�࣬��Խ��Խ��δ����ˡ������dz��࣬����Ҳ��δ���һ����������������ӷ��������������⡣ ��������ѧ�ˡ���������˵�� ��֪���������ӹԣ����������δ���˵�� ������̰ˣ��ѧϰ�����ù�����������˵�� ���������С�������¶�����һ��ͺ��ˡ����δ���˵�� �������˵˵���������úö��顣��������˵�� ��������δ�����˵�ţ����ſڴ����˷����õ������������������ȥˣ���� ����������ҵ��û���ꡣ�������Ź�Դ�϶�����Сɽ�������� Сɽ�ȷ���Сһ�꣬�����˵ĸ�ͷ��࣬��һ������顣�����Ը�����˵����Сɽ�Ը��������� ���ߣ���ȥ���С�����������Сɽ�ĸ첲�� ����ҵ��������ʦҪ��������Сɽִ���Ų�ȥ�� ��������������ɶ�����軨��֪ɶʱ���ߵ����������ߣ���һ����ǰ��һ������ק��Ц���ʵ��� ���㣬�ҽ������ۼ�ȥˣ����ȥ���� ���軨�㣬����ҵû���꣬�ҵû�ȥ����ҵ���� ���һ�����û���ꡣ�� ��������Ͷ��ˣ���������һ������ҵ�����Сɽ�����軨����Сɽ�ļ�� �軨��ϲ��������С�ܵܣ�����ϲ��Сɽ��������Сɽ������ʵ���������Ƚ��ڿ죬��ɶ�¶�����һ�����ܵ÷ɿ졣�ν������Ź�Դ��ϵ�ã����ҵ������������ã�������һ��ˣ��Сɽ���軨������һ˵��Ҳ����һ�����Ժ�ӡ�Сɽ����ܸ��ˣ���������軨����һ���ˣ������ò軨������ȶԷ����á� ����ѧ�ˣ����δ����������˽���Ժ�ӣ����еش����к�������ϸ�ض�����һ������ǰ��ķ��ޣ��ĵ�ȷȷ���������������۾����DZ��ӣ�����ͣ�������СС�Ķ��䣬��ֱ�������δ����ķ��棬Ҫ�б���˵����������һ��ģ�����������Ļ���ֻ����һ����һ���һ��Сһ������ѡ��δ������ﰵ�����⡣��������Ŀ������軨�������۾���Ȼһ�����ⲻ��������һ�μ�������������ԲԲ�����������ۣ������Ľ�ë������С�衭���δ���������̾������ĸ������Ů���軨������û��һ����ν�����Ӱ�ӣ�û������һ����ν����ĺۼ���������������˵ġ� ���š����軨���δ������������������ܲ�����ζ���ñ��Ӻ���һ�����ǻش𡣷���Сɽû�п�ǻ�� �軨��ӰӰ�´µ���˵���δ�����������¶�����������������ΪɶƢ����ô�֣��������ﳳ�ܣ��������Ͱ����ˤ�롣�軨�䵭�����������ӵ�Ŀ�⣬���ޱ����Բ����ʹ��������δ�������Щ���Ρ� ���ҵ�զ��û���������軨�ʡ� ���������ɳȥ�ˡ���������ش�Ů�����ʻ��߰��۾�б��δ�����ԲԲ����������һб���δ������⣬������ǡ� ����զ��ۼ��������軨�����߳����ŵĺδ������ܲ����˵��ʡ� �������������� ����������һ���ˣ��� ����Щ�������ˡ��� ���ҵ����ڼң������������ɶ�����ᣡ�� ���������Ů�����Ǹɲ����������������ۼ�����һ��������ܲ����������� �����Ҳ�ǣ����±���˵�л����� ������˵ɶ������ ��������С����һ�춼������˵�����ģ������������� ���軨��������Щ��Ϲ����ͷ����˵�˵������˷�û�¸ɣ�һ�쵽�����л����� �������л����л������ǻ�Ҫ���ˡ��� �軨���������һ�����һ����ף�����һ�仰������������ȥ�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