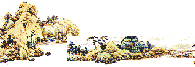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ȵؽ��ţ����Ϸ��ɻ����ˣ��ɵ������Ǿ�Υ�˵ļ��硣�������������Ҳ������һ�ԣ����Ǵ�СϪ�����������ĺ��࣬�������¹��������ǵ��¾ӡ��������»����һ�����������죬Ĭ����С���ݺ��ˣ����Ǵ�ɽ���ϣ�����Ұ�������ɿ�������С���̵������棬����ˣ��ͳ�˫�ɶԵ���������Ϣ�� ����������Ҳ��ʼæµ�����ˡ�����ҵأ��ͷಥ�֣�һ��һ����������һ��ææµµ�ظ������Լ������ء��Ź�Դ�ͺν���û����ȥ�������⣬��Ϊ���ǵ����ز��࣬����������ڶ�������˵����Ϊ��Ҫ�ˡ�����һ���ѣ������������ũ����������������ˡ�����˵������ׯ���˵������ӣ��Ź�Դ˵���⻰��ȷ��ֻ˵����һ�롣ȷ�е�˵��Ӧ����������ׯ�ڵ������ӣ�ׯ����ׯ���˵������ӡ�ԭ���ǣ������ٶ࣬�����ٺã���ȥ���֣���ֻ�ܳ��ݡ����Ź�Դ�Ļ�˵���ǽл��¡��Ź�Դ��ν������˶��ܿ������أ����ܿ���ׯ�ڣ����˶�Ƣ��������˵���Ż������ԣ����˼ȸ��������⣬Ҳ������ׯ�ڡ������ˣ�һ������һͷţ��������ػ���������ţ��Ҫ���ģ����ҵ�ţ���׳���һ�̶ֹ��Ļ�����ʽ�����۴��ֻ������գ�����Ҳ��������������ҵģ������ҵ�����ģ��Ӳ��ƽ�˭��˭���ػ���������˸ɣ������������ͻ������������������Ժ����������ף�����顭������������ȥ��Ҫæ�����¡����ʱ�䣬�ν����������鼸���Ǵ粽���룬����һʱ�ν������ڣ�����Ҳ��������������һ�𡣺δ������ӽ������飬����������ǣ���š�Ƶ����ܡ��δ�������һ�����ڴ��ת�ƣ�Ѱ������������ӽ��Ļ��ᡣ �����Ҫ���ˣ���������ҪέҶ��һ�죬���������������߽���С������έ����Ƭέ��Ȼ�Ȳ��ϱ�����έ������ӽ���Ҳû�б�����έ��ô���ˡ�������έ���и���̶��һ�쵽�����ॵ������ͣ�����Ź����˵ġ������µ����Ǹ���̶�����������ˣ�����˵���Լ�����ȥѰ���ģ�����˵������̶��ϴ�豻�������ģ���˵��һ������զ˵����̶������������ġ����ԣ������Ů������û���˵���������έ��ȥ�ġ���Ȼ������Ҳ���ҵ���������ȥ���ο����ɵ�έҶ�����ӣ���û�б�Ҫȥð�Ǹ��ա� ����������С�������ߵ�έ��һ������έ���ϵ�έ����ȻҲ��һ�ɶ�ߣ����˺�ϸ��Ҷ��Ҳ��խ���Ͳ��������������έ����έ�м��ߡ����������έ�˻���ײ���ţ�������έҶ����ĥ���ţ�ɳɳֱ�졣������·��έ�е�Сˮ̶������ϴ�˸��֣�Ȼ�����έ��������έҶȷʵ��Ҳ�ٱ��˲ɹ������������������˫�֣���ժ�����Ƶ������������ֽ����ժ�š�ৣ�ৣ�ৣ�έҶ��ժ��ʱ�������н���������� �����顣����Ȼһ�����˵�������֪�Ӻδ���������������ʮ����Ϥ�� ������ͣ���������Ĵ���������ï�ܵ�έ�ӿ����δ���������ææ������������ ������Ūɶ����������Ծ����������� ���������㡣�� ���ò��ţ����߰ɣ������˿������� �����û���ˡ��� �δ���˵���Ѿ������������飬ͻȻ�����˵��������ǰ�����������ر�ס�ˡ�έ�ӻ��༷���ţ��������ᣬɳɳ֮�������ڶ����м���έ�ӱ������ˡ��δ����Ȳ����������ֽ��������Ŀ�������ͬʱҲ�������Լ��Ŀ��ӡ�����վ������罺���ᣬ������մ����һ���ˡ� ����ڸչ����δ�����Ȣ��ϱ������Ȣ�����ϱ�������նս����������ʯ�����δ�������ϵľ������������ӣ�ԲԲ�ģ���������Ļ�Ҫ���������˿������֣���ʵ�������ﶼ����С�������δ���Ȣ��С����������������������극���������ر����ˡ��Դˣ����������ʮ�㡣һ�죬��������δ���������ڴ���������δ���ԶԶ�ؿ��������飬���ӿ��˽Ų��������������ڲ�·�ڴ��������������¿������ˣ��������������������վס���Ҳ�����㡣�� �δ������ε�ͣס�˽Ų��� �������ǵ��ԣ�Ȣ��ϱ����������� �δ�������������������ŭ��Թ�ı��飬һʱ��֪˵ʲô�Ǻã�֨���˰����˵������˭Ȣ��ϱ��������ҲŲ��������ˡ��� ���ף��������ˡ���ô�����ӵ��Ķ�ȥ�ˣ�����Ӱ�Ӷ�û�����㣬�벻���������������� ����զ������ ���㻹��֪������ ����֪��ɶ���� �����ÿ龵�����գ��������������ÿ��úܣ���Ŵ��������ﹰ�������Ҳ�����ģ���������ûɶ�����ٿ��������������ѣ�������ɶ���ˣ��ٲ����ŵ㣬����Ҫ��ɹ�ͷ���ӣ������ˡ��� �����������ߴӿڴ����ͳ�һ����ƶ���С�����棬һ����һ���������ﶪ���δ���֪������Ҥ��װ���ˡ� ����˵�ɣ��㻹����˼���� ������ɶ������˼���� �����������Ūɶ���� ��Ūɶ��δ���㲻֪������ ���ҵ�Ȼ֪�����ν����ָ���װ���ˡ�������У����δ�����������ģ����ν����Ƕ���Ҳ�����¶����� ����ƨ�������û���ĵĻ����� �������ܵ���ί�����ƿڴ���δ�������Բ����Ī����� ��δ����û˵�ԣ��� ��˭֪���Ҷ��������ĸ������֣��� ��δ�ػ����ҵģ��� �����������˭�ģ��� �δ�������������С�ģ��ҿɶ�����ûմ���ı��ˣ�զ�����ҵģ���������δ������Ű��ɣ�ֱ�������� ������������έ���Ū�ġ��� ��������ôһ˵���δ����Ծ���С��վ���������װ���ˣ�����ô���ף���ϲȢϱ�����ü����ˣ���ϱ���Դ�ŵĶ��ӻ����Ϻ��е�ñ��ƽ̹̹�ģ���˵��ϲÿ��Ū���¶���ʱ����һ����ͷ�����Դ�ŵ�ƨ�ɵ��£�Ū���ˣ���Ҫվ�ڴ���˫�ֵ����Դ�ŵ������ȣ�ʹ�����¶��������Դ�ŵ��Ķ���������³����ˣ���û���Դ��װ�ϣ�����Ȼվ�ž�������װ���ˣ����е�����Ҳ�е��Ժ��� ���ң����� ���������ǹ����� ��������䷢�ģ��δ������ﰵ�����ˣ�ͬʱҲ������һ��˵�����Ŀ��⡣ ��ɩ�ӣ��ν�������Ū��һ������Ҳ����Ū��һ������������Ȼ���ҵ��֣����Ժ���ɶ�¶������˵���� ���������δ���������ɩ�ӣ���������һֻ�̶��Ӳ�Ӭ������ܲ�����ζ����θ����һ�£�����һ����Ż�����Ͻ��������ﶪ��һ�������档 �ڶ��꣬�����������˶�����֣��Ǹ����ӣ�ȡ�����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