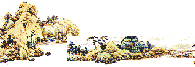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Źⴺ���˹��縱��ǣ��ᵽ����ȥ�ˡ� �δ������˴�ӳ����������Źⴺ�ڻ���������ҵ�� һ�ұ�������žž���������һ���������ﵮ���ˣ������������˹���ʳ�á�ʳ�õ�ǽ�����ð�ɫ��ʯ��ˢ��һ��������� ������Ƥ�Է�������ɾ��������� ��д�ò���ô��������������������Ա�ǵ�ӵ���ͳ��ޡ�ʳ�ÿ������죬�δ�������һͨ������˵�ÿ��������������˻������˰��ơ��δ���˵������ʳ���ǹ�������IJ���Է���ҪǮ�����Գ������ӣ���Զ��ٳԶ��٣��ܳԶ��ٳԶ��٣�Ը�Զ��ٳԶ��٣�һ��Է���һ��ɻһ��˯�������������Ĺ���������ͥ���ʳ�õĵ�ȷȷ��ò����������ɣ��������������������ԡ���Ů�Dz��������������Dz���Ϊȱú���η��������Ǹ��Ǹ��ˡ���ЩС������һ������ϲȸԾ���ı���������Ϊ���Ǵ���û�����ܹ����ִ�����������Գ�����Ƥ�Է������ұ�һ��һ���Եúã�һ�컹Ҫ�������Ǹ������췶��Сɽ�����Ǹ�����˵�һ�����������ߣ���Ȼ����һ�����ڽк��������ޣ�Сɽ�ȵ��ң��� ����Сɽ��ͷһ�������������ܱߺ��Ӻ����������� �������Źⴺ�Ķ��ӣ��뷶��ͬ�꣬������ͬ��һ������顣���������е㱿��һ�������ĿΣ���ʦ�ںڰ���д��һ�����ء��֣������ش���ʦ�ʣ�������������ɶ�������������Դ�������������ͬ����Сɽ����һ�����Ŀ��ӣ�����ָ��ָ���£����������ش���ʦ��������ǡ������Ϸ��ѡ��ء�����Ϊ���ǡ�������ʱ��������ô�Ц�����������Դ����ҿ�������������ͨ�졣����֮����û��ȥ��ѧ������¶��ڴ��ﴫ���ˣ������˾���ȡ�˸���ţ����Ƶ��ǣ���ơ����ơ������������˶��������ƣ���˳���ˣ����������־͵����ˡ�����Ҳ��������˭��������������Ӧ�� ���������Ǹ������Ʊߺ������ش������ߴӿڴ����ͳ���һ��Ѻ�����̵��Ǹ��� ����զ��Щ���������ʡ� �������������ġ�������˵�� ����ֻ��������������������Щ����������Щ�ۺ졣 ���㲻��������������������˵�� ������������������ʡ� ���ᡣ��������ȥ�����������ŷ��ޡ� ���ߣ��۶�ȥ������������Сɽ�� ����С�������ܵ���ʳ�á���ʱ���ѳԹ��˷���ʳ����ֻ�кδ����ͻ�� ��������Ūɶ�����δ��������̱��ʡ������Ļƽ�ҶҲ��ʳ�ù����ġ� ��������Ҳ������ǵ��Ǹ�������ɵ������˵�� �δ������˿����ޣ��������ڴ����ֿ���Сɽһ�ۣ��ӿڴ�������һ�ѽ������ޣ��������ڴ�������һ��˵������ѽ��û�ˣ�Сɽ���������ٸ��㡣�� ����û�ˣ��Ҹ�����������˵����Сɽ�����������ư�һ���Ǹ���ݸ���Сɽ�� ��������Ҳ���㡣������Ҳ��һ���Ǹ���ݵ�Сɽ��ǰ�� Сɽ˭���Ǹ���Ҳû�ӡ� ����С�����߳���ʳ�á� �δ���Ҳ��ʳ�����˳����� ��Զ��Χ��һ���ˡ��δ������˶���ȥ���˶���վ��һ����������ÿ��������룬վ������˵˳��� ʳ�úã�ʳ�úã� �����ɸ������� ���ܶ����ж�� Ը�Զ��ٳԶ��١� ���������Σ� ��Ϊ���淳�գ� �����ʳ�ã� ��������Ҩ�� ������ճ��꣬�������ֵĶ�ϲ�Ե�����һ���룬�����ʵ���������˵ʳ�õ��ò��ã��� ���������𣺡��ã��� �δ���������Ҷ��ڿ乫��ʳ�õĺô������ϸ����˲��õ�Ц�ݡ��������������˴�����Ҹ��������Ѵ����˴����˹������塣 ���������δ����Ժ��������˵����������ϵĸְ壬��һ��ߺ�ȣ�����ŮŮ���¿��ӣ��߳�ʳ�ã����������վ���������£����Ǻδ������վ��»���Ҫ����Ź��Ķ��У���һ�����Źⴺ�ڹ���ר�Ž̵ġ��δ���վ�ڶ���ǰ�棬�ӵ��׳�����������һ�º�������ʼ�������δ���˵��������ͷ��ָʾ�������ڿ�ʼ����һ����չ����ء��ڶ�����չ�����˶�����������չ�����ĺ��������ģ���չɨ����ä�����������ֹ������������أ�Ů�������ʣ�С�����dz����ĺ���������˵�������Ҫ����ߣ��Źⴺ���𡣷�Ҫÿ���˻�һ���������鸺�𡣳����ĺ�����һ��һ��Ҫ����ֻ������ֻ��ȸ����ʮֻ��Ӭ��һ��ֻ���棬�ζ�ϲ����ɨ����ä���¶��������죬�ɴ�ɽÿ������·�ڣ�·�ڷſ�С�ڰ壬�չ�ʱ����Ҷ����������ÿ�˱����ںڰ���дһ���ֶ���д���˾��ߣ�д�������ͽд�ɽ�̣�ɶʱѧ��ɶʱ�ߡ���ɽ������û�У� �� �����ˡ�����ɽ�ڶ�����ش𡣴�ɽ���Źⴺ�Ĵ���ӣ������ڶ���С����Ծ����ʼ��ѧУ��ʵ�а����ơ� �δ���������ϣ���Ҹ���λ���δ������ص���ڻ����ϡ�ׯ��һ֦����ȫ���൱�ҡ��˲��Է�û�о�����ׯ�ڲ��Ϸʾͳ���׳����ǰ���ÿ�չ�Ļ����˶��У������Ժ���·�ϵĵ�Ƥ�������ˣ�˵����ǧ���࣬�ʡ�·�ߵIJ�Ƥ�������ˣ��ӹ������ĺ����౻�;��ˣ������Ҹ���ǽ�ϵ���Ƥ���ҹ��ˣ������µĻ�������Ҳû��ɡ�����ֽд�һ��ʣ����������ڣ�����������������ͣ�������ң����ںδ��������ѧ�˾��飬����Ѭ����ʡ��δ���Ҫ�ƹ���Ѭ�ʾ��飬��Ȼ�͵ø���Ů����һ����������֮���õġ��δ����и�Ů��������������ϰ�����������һ���ݳ�һ����С���ѣ�ԶԶ��ȥ��һƬ�صء��δ����и�Ů�DZ�����գ����ˣ�Χ������������Χ���û����ţ�������̶���һ�Ѷѣ�һ���У�׳���ޱȣ������ʱ���ȼ�ķ��̨����Ϩ֮����������Ѭ�ý��ڣ�����������˵Ļҽ����ڵ���������Ѭ�ʡ� ���������ʩ����Ѭ�ʣ����Ϻ������������ס������쵽�ˣ�������������ͷ�ˣ��ƻƵģ����ݵģ��г߰��������������������ϸ����ָ�����ɣ�խ��������Ҷ�ӣ�һ�߶�߾�ð���ˣ������ˡ�������������үҲ�����ۣ������²�����һ���꣬������ظɵ�ֱð���̡��������ˣ��ճ����� ����ʳ�ã�����ȱ�棬����Ҳ���ٸ�������ʳ�ˣ���Ϊ�ڹ������յ��ʲ��ϸ���Ӳֿ����ʳ���ٶ����Գ������ꡣ��Щ���ֶ��Ǹ�����Ա��ġ�ʳ��������ɸ���������˺����������ɡ������غ�����Ҳû���ˡ��ֹ��˼��죬��������ʼ����������һư��С���Ӱ�ư��������ˮ����ӳ���¡�һ��������������Ա��һ������ɫ���ң��������С�����Ƕ�����˴���ֻʣ���Դ�������һ��Բһ������Ķ��ӡ� �����ˡ���������ش��ţ������˳�˯��С����������ϸС���������۵ĸ첲ʹ��ȫ�������³��˴�����ѿ������Ҳ������С�ݣ�С�������۾��ӱ��������������ſ�������Ƕ�ڸɿݵĻ�ɫ�������ϡ��������ڹ�ȥ�ˣ��������ڰ������ˣ����dz�������ɫ����������¶���˼��������ټ���ϲɫ��һ�������������߳����Ÿϳ��Ƶ�ӵ��ɽ�£��ɲ��ƵIJ�ժ������֦���ϸո��³�����ѿ��С���ֻص��˶��죬֦�����ֱ�ù������ˡ�ҹ�䣬���dz�������˯���Ը�����ٶ�������ɫ���Ŵ��졣���ǣ��컹û�з�������Ա���Ѿ����ĵ������������ߣ������������������ǵ����Ӷ�ȥ������ҹ����Ͷ��ɹ�����������С�����ϵ����̣���Ա�Dz��ϵز�ժ��һ���һ�磬һ����һ�磬����ժ��ժ���¡�������С�����Ŭ���������������ٶ�ҲԶԶ�ϲ�����Ա�Ǽ����������ٶȡ�����ɽ���ϵ�Ұ�˳������ˣ�ΪС���ֵ����dz����Ҷ���������ǵ�����ʱ����Ա�ǵ�Ŀ�����˸ո����������ۻƵ�Ұ��ѿ��������������������ɽ�ˣ�Ѱ���Ƶ���ɽ������Ѱ�š�Ұ�������ˣ��Դ���¶����Ƥ����δ������һ�����ʵĿ�������һ�����죬��һ��̫�����ͱ����÷��ŵĶ����Dz��̵ظ�ȥ���Դ����еļ����ĸ����ָ�������ȥ�Դ���˵������˳�������ڵ��������������ѽ����죬���˵��ϵ�ׯ����ͺ���Դ�ͷ�ϵ�ͷ��ϡϡ������ɽ��Ȼ�ǹ�ͺͺ�ģ�С����Ȼ�ǹ�����ġ�������ʵ���Ҳ����Ե��ˣ�����������������������Ƥ��һ�ÿ�С�������һ�������ڵ��ϵ�ľ�����״�����������ɭɭ�ǡ�С�����������ᣬ������ѪҺ���ɿ��ˣ���ȥ�ˡ�����Ϊ�������ַ��������˹ǣ�С��Ϊ���ȼ�����������������Լ��������ǰѰ�������Ƥ������������̽�����ɺ�����������ţ�����������θ���һʱ֮���� �ν������ϳ���һ����Ƥ�ɣ�������ͷ�µ�ȥ�ˡ����Ƕ����ţ��ʽ�����ۼ��������µأ����ܽ�ţ���š��ν�����������������ţ���ַ���ѣ�����һ�ţβ��һ�������ͷ���ߡ����������������˻ҧ�Ű������ء��������⣬ţʵ���������ˣ�վ��ԭ�غ����ش��Ŵ������ν����ٴ�������ӣ�ţ˦����һ��β�ͣ������������ν������ţ˦��һ���ӣ����ڱ��Ҽ�������ţ����ʱ����������ţ�Ǽ����ӵ�ƨ�ɣ��������������˲��Ա�û��������ţ��Ҳ��һ�����Ŷ�Ƥ������һ������һֱ���dzԵĸ�ɳɳ����ն��ް������ϡ��ν�������ţ��Ъһ�£��շ�����ͷ����Ȼ�����˺δ���˵���Ǿ仰�����������һĶ���ν����ַ�������ͷ����Ϊ����ţ��ʡ���������ν���ʹ�����������ᣬ��ʹ�������̫�ţ�ǵ���ʡ���������ν���ȴ�������� ��ͷ�������죬�ν�������ͷ��Ŀѣ������Щվ�������ˡ������ڵ��ϣ�ֻ�������춼����ͷ���緱�ǰ��������顣�������۾����־��������������ĥ���ϣ���ͣ����ת����ʵ��̫���ˣ���������û���˳�θ��ǰ�غͺ�����������һ�𡣹���һ������ز�ת�ˣ��ν���������̧����ص���Ƥ��ֻ����ͷţ���ڵ�����Ȼ�ص���ĭ�����ν����룬ţ���˿��Է�ۻ������Ϊʲô������ѧţ�����ͻȻ�ķ���ʹ���е��˷ܡ������Ҳ����ţһ����ۻ������ļ������ⲻ�͵õ��˽�����ν�����ʼѧţ����һ��һ�ϲ�ס�ؾ��š����ǣ��ν������˺ܾã�������Ȼû��ð��һ����ĭ����������ţ�����������������ĭ�����ν����룬Ҳ�����Լ��ķ������ԣ�����������Ѱ���µķ�������ͼ�����ϳԽ�θ����Ǹ���Ƥ�ɵ���������¾���������һ����ʵ���˵ķ�ۻ�����������ܰѳԽ�θ����Ǹ���Ƥ�ɵ�������ν������˶�ʱ�����һ���취��������һ��������ʮ�ȵĶ��£�ͷ���½ų���ſ�������ͼʹ�Ѿ������˵���Ƥ�ɴ�С���ص�θ��Ȼ���ٴ�θ�ﵹ�ؿ��С��������ڶ����������������̹���θ��û��˿����Ӧ������֮�������������ڵ�����Ѱ�ţ���������һ��Ұ�ˣ�������������ֻ���ƣ���������������һ���������͡� �����ں��ˡ��ν�������ʵػص��ң��軨���˵�������������Ͷ���ʵ�ݵ��������ϡ��ν����ӹ�����һ�������������������һ�飬ҧ��һ�ڣ����Կ��ԣ����糴���������еĺν�������һ����û�Գ�ζ���� ������ɶ�������ʲ軨�� ������ɶ����ɡ�������ʮ�����۵��IJ軨Ȱ���� ������զ���ԣ��� �����dzԱ��ˡ��� �ν�����ڴ�ڵؽ��ţ�̰���������ţ�ͻȻ����һ�죬���۷�ֱ��������Ӳ��ʯͷ��ҭס�ˡ��軨��æҨ��һ����ˮι����������ν�����������������������ҹ��ν����ڸ����̣������˼�����ˮ�� �ڶ������磬�ν����Ѿ����ˣ����ӱ����� �ν��������ﲻ�����ˡ���ȥ���ˣ��еĻ�������ҽ��˵�ǵ���ˮ�ײ���Ҳ�е���ν������ݵ������ã�ҽ��˵�dz���ʯͷ�����˳��ӡ��軨һ�ҿ���ȥ�������軨�߿ޱ߶϶�������˵�������ø���Щ��ȥ��ʯͷ�棬�����ӱ��ԣ����������˵����軨Խ˵��Խʹ�� ��ʵ���軨����Ҳ���ˣ�ֻ������ö�Զ������˵��� ������������������Ա���ǹ��������ġ�����վ�ڴ�ڵ��������£��ִ���壬����Ա������������ ���� ȱ��ʳ��Ұ�˲����ж�Ұ�˲��ܳԡ� �Զ��ӣ��Ƕ�ҩ��˭��˭�Ͳ��ܻ ���� ʯͷ�棬���ɳԣ������Ժ����ӡ� ���Ӷ������ѱ����װ����������š� ���� �ν������ˣ��������������˴����Ź�Դ��ϱ��������������������������飬Ȱ�˼��죬�����������������һЩ�����ͻص�����Ҳ�����ˡ�Сɽ�����ݵ�ֻʣһ��Ƥ�ˣ�֪�����Ƕ����ģ�������Ѱ��������ҵ������ӵĶ���������ɶҲû�У�������ˣ�˺�����dz�����������ӳԡ���������ݵ���צ�Ƶ��֣�һ��һ��ӱ����ﳶ����÷��ڵ�������һ��һ��������������Сɽ�Ӵ���������俴���ˣ����������ܳ���Ժ�ӡ�Сɽû�����ǣ�������������ʳ�ö˻ؿɼ���Ӱ�ĺ�����������Ҩ��һ�룬���������ڣ����������Ѿ����꣬˵����ɽ��Сɽ����Ȳ���ȥ��˵�Ÿ�����������һ�˵���һ�롣��������զ�Ȳ���ȥ����˵������ڲ軨����軨���������һ�������ԣ�������Ҷ���û������������ˣ���������������һ�����ھͰѰ�������������ˡ������Сɽ֪���ˣ���˵��ȫ�Ǽٻ��� Сɽ�ߵ�ʳ�ã��������͵�㶫���ԡ���������һ����ʳ�������ˣ����ӻ��������һ��С�����δ������ڵ���������ֽ�̡�Сɽ�����ˣ�ת�������ߡ� ��Сɽ������������δ�����Сɽ���ſڰ͵���һ��ת�����ˣ���Ҫ��Сɽ�������ʸ������� Сɽ�ԹԵ�ת��������ʳ�ã������ºδ��������Ǵ�ӳ��� �������ſڿ�ɶ�����δ�������һ���������۾�����Сɽ������ ������ɶ����Сɽ˵�� ������ɶ�����δ���������һ���̣�������ɡ��� ������ɶ���Dz���ɶ���� ���㲻˵��Ҳ֪������ �δ�����һ˵��Сɽ������ͨ��ֱͨ���� ����֪��ɶ����Сɽ���ӵ��ʡ� ���㼢�ˡ���û�´��ɣ����δ����ܵ��⡣ ���������Ҳ�������Сɽ���ϡ� ���������ҿ�����˵Ϲ����������ӡ������δ�������ָͷ��Сɽ���Ķ�Ƥ�ϵ���һ�£�Сɽ�Ķ��ӷ�����һ�����죬�δ�������һ�����á� Сɽ�ŵ���һ�ɴл�����ζ����Сɽ��ס�˱��ӡ� ���������������ˣ��Ŵ����һ���������� Сɽ�ӹ��δ����ݸ�����һ��С�����������ꡱ����һ�ڣ�ת�����ߣ���������������� ����������������ԡ����δ���˵�� Сɽͣס�˽Ų��� �����ûؼҳԡ��� �����С���������ԡ��� ��������Բ���һ������ ���ҽ���������ԣ���͵�������ԣ���Ҫ�ߣ��ͰѺ������¡��� Сɽ���Σ�ֻ�ô�ڴ�ڵؿ��š� �δ�������Сɽ���̻��ʵ����ӹ�����Ц������ ���������Ӷ���˵Ϲ������˵�������� Сɽ�����ˣ���Ȼվ�������ֻС�۾�������װ�ź��������� ������ԣ����δ����ʡ� Сɽ���ͷ�� �������һ���ˣ���Ҳ���ܰ׳ԡ�ȥ���º�������ʰ�������� Сɽһ���������������ˣ����룬�����ɵ�ϣ��Ѷ�¿�ƽ��˲��ݡ������е��Ǻ�������������������Ҳ���ԡ� �������Сɽ��Ӧ�ˡ� �����������Ӻ�����Сɽ����ʳ�ú���ĺ����ѣ���������һ��һ�ɶ���ľ�Ͳ�ӣ��ո���������������װ���Ǹ����������Ϊ�˷�ֹ��͵���ھ�Ͳ�ӿڵĶ����ϱ�����һ��ȭͷ���С����������ľ��ʮ�ֽ�����ͷ�ֱ�Ž��ĸ������ʮ���Ĵ�����һ���۶������ﴮ��һ�����ǣ������������ϡ�����ȡ��Կ�״��ţ�Сɽ˳�ž�Ͳ���������һ�������������ȥ�ˡ�����ϵ�����Сɽ�����ڵ�ס����װ����װ�߳ԣ�װ�����Ŀ𣬶���Ҳ��Բ�ˡ��Ͻ�ʱ��Сɽ������ѡ�õ�����ϸ���ĺ���������һ���������Ѹ�ס����������̫С������Ĺ����ҵ��������������Сɽ������ʱ��С�Դ���¶����Ͳ�ӣ���ʱ��ɵ���ˡ��δ����Ͱ���վ�ڽ��ſڣ��۾������Ž��š�Сɽ��ʵ�����ˣ������������һ¶ͷ��������è�������˻�ȥ�������ֲ�������Ҫ������ͺ��ˣ������˻ض��ɶ��Ҳû���ˡ�Сɽ�Ȳ����˻�ȥ�ֲ����������������ڽ��ſ�ĥ���ţ����ºδ�������������Сɽ��Щ���棬����Ⱥδ����������������ɺδ���ƫƫ���ߣ��������������� ��Сɽ������������ Сɽ���㲻��ȥ����Ȼ����һ�ƣ���СĿ�ꡣСɽ�Ķ�������һ����һ������˳�ſ�������ѵס� Сɽ�����ˣ����������è�Ƶ�������� ��վס�����δ���ͻȻ������ Сɽ�����←��һ�£��ԹԵ�վ��ԭ�أ��۾����ŵ��ϣ�����ת���� ����������ɶ�����δ����ʡ� ��û��ûɶ����Сɽ˵�� �������ҿ������δ������š� Сɽ�˻�����������Ȼ�����źδ����� ��ת�����������δ�����ݺݵ���� Сɽֻ��ת����������źδ�����������ͷ���ҿ��δ��������� ���ͳ�����û��ɶ������ Сɽ��Ȼ����ͷ�����ͣ�Ҳ���ش� ���Ͳ��ͣ������δ����ʡ� Сɽ�Բ�˵������ֻ������һ�𣬲�ͣ������š� �����ͣ����δ������ʡ� �δ���ת��Сɽ�ı�����һ������Сɽ��ƨ���ϡ�Сɽ��һ�������˸��������ſ�ڵ��ϡ�Сɽ��Сҹ�����ˡ�һ���Ⱥ����Ķ���˳�����������˵��ϡ�����Ҳ������˳�ſ������˳����� �������첻Ӳ�˰ɣ�����ɶ�����δ����ýŵ��ű����ʪ�ĺ����ʡ� Сɽ�����С�죬���ﺬ���Ứ�� �����ţ��Ժ���͵���������ġ����δ�����һ�ŷ���ֻ����ಡ���һ���죬�Ǹ������ʪ�ĺ����ɳ���һ�ɶ�Զ������ǽ���ֵ��ص��ϡ�Ȼ�δ�������˫�ֽ�ʳ��ȥ�ˡ����ӻ����ںδ��������� Сɽ����ȥ���Ǹ�������������ͷ�ؼ��ˡ� ����ˡ��ڹ�¡�ˣ�û��������Ҳû�����ǡ�Сɽ����ʳ�ú�ߵĺ����ѣ������������ϵ����ǣ������Ĵ��������ϱߡ��������˺����������Ƕ�ǽ�ڡ�����Ϲ��һ����ǽ��������ǽ������������һ�ַ�ǽ��һ�����أ��������ߣ����߱��������ڵ�����ϸ����Ѱ�ű������ʪ�ı��δ����ߵ�ǽ�ߵ��Ǹ�������������һ��ë���Ķ����������˵��Ƶ���Ȼ���أ�վ�����ý�һ�ߣ���-- һ����У�����������Ϸ���һȺ�������ܵ�������Сɽ�����ˣ����ղ���������Ѱʳ������Сɽ������������������������Ǹ������������Ѿ��������ˣ�����Ⱥ����е���������ӿӰ������ˣ�����һ�����Ÿ߳����յĵ��ܼҵ�̵���Ʒ��Сɽ��������������������Ȼ����Լ�û�����������磬������ռ���ȣ�������������һ������У��Ͼ���������õ��Ķࡣ�������˵��һ�����İ�ο���δ�����������һ��Ҳ��û�װ��������Ǹ��������ĺ����ûؼң��ݵ������� ��˵����Сɽ����ɡ��� Сɽ˵������Ҳ������� ��˵����Сɽ����˵Ϲ������ Сɽ˵�������û˵Ϲ���������������ҵĶ��ӡ��� Сɽ�����ع���һ������ �ڰ��У�����������һ��Сɽ�Ķ��ӡ� ��Сɽ�����ɶ����������Ծ����ʡ� ���������� ���ʣ���������Եģ��� Сɽ˵����������� �����ŵ�������˶��������Сɽ����ͷ��ʯͷ�档 ��˵������ס���ٶ������ҳԶ������� Сɽ˵����֪���ˣ�����ɡ��� �������Ǹ��ӿӰ����ĺ������������ĵ����������� ���͵IJ��Բ����ᣬ������������һ�����š�������ʮ���꣬�ں�����һ���ø�ʢ�������ž�����������Ƴ����������ܴģ����ų������ڹع�����ǰ�����̾�����ͷ��Ҿ��ع�������һ�����ա����ڸ��ײ����У����˲��ϣ�������ҩ����Ҳ��Խ��Խ�ࡣ���ŵļ���������������ϳ�һ�����ﲻ�������Ű�����ҩ���˶��ˣ�����Ҳ���ò��ų����ˡ������������룬����Ҳ���������ֽ�����ϡ�����������������һ����ģ������ݣ������������С�á������鷭ɽԽ�����˼�ʮ��·�������żң����ſ���ԭ��һ����ķ��ϣ�����������������������������߽����͵���������ţ����ϴ�������ع������ǽ�ϡ������㰸����һ����ˮ��Ȼ����㣬ͬʱ���������дʣ����������ʱ�����������۵Ľ�����������һ�����ֽУ�����һ������������������ಷ������棬������Ʈ�����С����Ͳ��������ش��˸����������϶�ʱ����һ�㼦Ƥ��������ͻȻ�����ȵ��������ӣ��ŵ������ڿ�������һ�£�Ȼ��������ǰһץ�����ȭͷ������Ҫ��ץ���������ħ��������һ����֮����������һ��������������һ�������ŵĹ��������ˣ�����ԭ״�����Ÿ�������˵�����ˡ��ѹص�ү�͵�ҩ����ι�¡������������ţ�С�ã�������զ�ˣ�����˵�����ڶ�����̫�࣬����Ͷ��������Ѱ��������������������������Ҫ���������ÿ죬���������¡������ں��ˣ������Ķ������ѱ��ص�үնɱ����������������δɢ������ѹص�ү�͵�����ҩ���£�������Ȼ����������˵�꣬������ǡ������鼱æ����������һ��Ǯ���������������û���ƴǡ��������ţ���������ݣ�����ص�ү�͵�ҩ�ݵ�������ǰ������һ����������ˮ�������ң�������ˮ�е���һ�κ�ɫ��īˮ�� ������˵�����Ȱɣ�С��˵���˾ͺ��ˡ��� ���ͱ�����ȣ������ǹص�ү�͵�ҩ���Ҳ��ܣ�������ҧ�����������ǿ�ɬ����ˮ������������������������ȻҲ�����ף���ν�ص�ү�͵�ҩ������ˮ��Ʈ���˼�����ҡ����ǣ�����˭Ҳ����˵���⻰�����ǽ������ص�ү������ȿ���ѵ������������������е����顣 �����Dz��ҵ���ģ�Ҳ�ǵ��ﲻ��ġ� ���ͺ���������ˮ�������ϲ�����ء����³������ߣ����Ե����²��ѡ�����������ˮ�������ֽ���һ��ûһ�εط��ڻ��͵Ķ�ͷ�ϣ�����ʱ�ػ�����ȥ����δ��Ч�� �������������ҵ��δ���˵�����������һ�뽪���档�δ���������������������������δ���˵��˵���һ�뽪������Ǻ�ʮ�������Ҳ��ʳ�ø�����������ʳ�õ����ӻ���������������һ��Ʈ�Ŵл��Ľ����档��������������ڵĽ�����˸����ͣ����ͺ��˽����没�ͺ��˴�롣���Ͷ�һֱ�������ߵ�Сɽ˵��Сɽ�����ȥˣ����ɣ�����ˡ� Сɽ����IJ����ˣ�������ˣ�����һ˵���ͳ�ȥ�ˣ�����ȥѰ��������ˣ��Сɽ·�����Ӽ��ſ�ʱͻȻ����������һ�����Ǯ�������ﰵ����ϲ������ǰ���������ˣ�����ʰ��������Ǯ��СɽŤͷ�����ߣ�������ȥ�ҷ��������ˣ���Ҫ��Ǯ���������˸��ˡ���Ǯ���Ը������ԵIJ������ӡ�Сɽ��������ģ��߸����˵��ܽ��ݣ���б���ڴ��ϣ�һ�۾Ϳ���Сɽ���ϵ�Ц�ݡ� ���ʣ���Сɽ����Цɶ���� Сɽ˵�������¡��� ��˵������ʰ�������ˡ��� Сɽ˵���������ʰ��ɶ�ˣ��� ��˵������²��š����ó������������ Сɽ˵��������һ�ء��� ��˵������ʰ����һ��ͭԲ���� Сɽ˵�������û�¶ԣ��ٲ¡��� ��˵�����Ǿ���ʰ����һ��ˮ�ʡ��� Сɽ˵���������û�¶ԡ��������һ�ء��� ��˵�����ﲻ���ˡ��� Сɽ˵����������Ҳ�²��š��� ��˵�����²��žͲ²��ţ���Ҳû˵����š��� Сɽ˵�����������ۣ��Ҹ����������� ���ͱ��������硣 СɽͻȻ��һֱ���ڱ�������͵������ǰ��Ȼ������ý�����Сȭͷһ��˵������㿴���� ���͵��۾������ˣ��ղŻ�Ц��������ͻȻ������������Сɽһ���ס�ˡ� ��˵���������Ķ����ģ��� Сɽ����Ϊ�����ˣ�û�뵽�����ɫͻȻһ�䣬�����������ˣ�������Ǯ����������͵���ġ�Сɽ���ϵ�Ц��Ҳ�������ˡ� ��ʰ�ġ��� ������ʰ�ģ��� ������ʰ�ġ��� ��û˵Ϲ������ ��û˵Ϲ������ �����Ķ�ʰ�ģ��� �����Ӽ��ſڡ��� ������ģ��� ������ġ��� ���͵�Ŀ��һֱ������Сɽ������ֱ����ʱĿ�ⷽ�ű���º���Щ�� ������ȥ�������Ӽң����Dz������Ǽҵ��ġ��ǣ��ͻ����˼ҡ����ǣ��������ʱ�ļҡ��� ����˵��ʱ��Сɽһֱ�����С�죬��������˴��������Ǯʮ�ֲ����� ��˵����ȥ�ɣ�����������˭�ҵ���Ǯ�������ż��ġ���ȥ�ɡ��� Сɽ����С���ȥ�ˡ�������˵�ģ��ȵ������Ӽҡ�������Сɽͬ�꣬��ǰ��Ҳ�������Ӽ�ˣ�������������Ժ��һ��Ҳ��İ����Сɽһ��Ժ�ӣ����������������ڸ���ŭ���������ɶ�¶�������ȥ������ʰ��ҩ�����žͰ�Ǯ���ˣ�Ҫ֪����������ľ���Ǯ����Ѱ�����Ͱ����Ƥ���������������ӵĿ��������ǿ����������У�����������ʹ��������ί����Сɽ����Ҳ�̲�ס���������ᡣ�������ߵ�����������ǰ�������ذ�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