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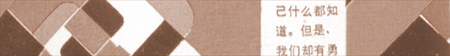 |
|
|
��Ԫ������һ��������
|
|
|
|
|
|
|
||
|
�����¡����������죬�����ͬ�ɡ��� �������ݺ�ʫ�ʼ����顱����������ʫ������龳��������˼�� �ҹ��Ŵ��й����ɵ�˼����Դ���硣��������˼�������ʫ����Դ���⣬�ܵ��������ڡ���豺�����ʫ�������й���ѧʷ���ļ�����ҳ199~203��һ������ʮ�־��ٵ��������˲������������ػʺ�������ɷ�ҩ�ͶԳ������ϵ�ϣ����̽��������Ϊ��ĵ�ʫ��Ҳ�����ˣ��硶ˮ�ɲ١�����ȸ�ǡ�����ȫ��ʫ����һһ����ʫ�����ȵȽ��ǡ��ں�������һ�ס�������ʫ���������о䣺�����������壬������嬽�������ͬ�ϣ�������ʫ��Դ��ս��ʱ��������ԭ�״������ƺ��ѳɹ��ۡ����DZ������������������ʫ��һ�ĶԴ�����̵IJ�������ԭ����Ʒ���硶��ɧ���Լ��ഫΪ��ԭ�ġ�Զ�Ρ���ʫƪ������Ũ���������������Զ�Ρ��ƣ�����ʱ��֮���i�⣬Ը��ٶ�Զ�Ρ��ʷƱ��������⣬���г˶��ϸ������塤����ν��ԭ��������֮����˼���ɾ���������������ԭ���Ա������ģ��ʷ�����Զ�����Թ㣬Ȼ����٣�����Զ�Σ����ʷ���ʥ��������٣��ʿ�Ȼ��־���������֮�£��ǽ��м�֮�Զ��DZ���Ҳ��������ɽ����ע���ǡ���ҳ145��������ԭ������ʫ����Ϊ��ɧ֮�ʣ���Ȼ��ʧƫ�ģ�������֮����Ҳ��ȷ�����������ϵ�ʧ���йء������������ʫҲ����ˡ����DZ��������ӵ���������һǻ�dz������ע�ڱʶˣ������ɵ�ʫ�����۵����к�����˺ڰ�����ʵ��ᡣ��������ʫ��������ͳ������ĩ����ٳ�ͳ��180~220���Dz��ɺ��Ե�һ������������顷���ľš��ٳ�ͳ������ ͳ���m�Σ���ֱ�ԣ�����С�ڣ�Ĭ������ʱ�˻�ν֮������ÿ�ݿ����٣����Ƽ����͡�����Ϊ���ε����ߣ��������������������������棬�������������������������飬�����������������־����֮Ի����ʹ���������լ����ɽ���������ػ��ѣ���ľ�ܲ���������ǰ���������۳����Դ�����֮�裬ʹ������Ϣ����֮�ۡ������м���֮�ţ���������֮�͡�������ֹ����¾�������֮����ʱ���գ��������Է�֮�������Է����Ϸƽ�֣����ˮ�����磬������߮�ߺ衣��������֮�£�ӽ�����֮�ϡ�����뷿��˼����֮���飻�������ͣ�������֮�·���������ӣ��۵����飬�������ǣ�������������Ϸ硷֮�Ų٣�������֮��������ҡһ��֮�ϣ�������֮�䡣���ܵ�ʱ֮����������֮�ڡ����ǣ��������������������֮���ӡ����۷������֮���գ�������ʫ��ƪ���Լ���־����Ի���������ż����������ǡ��������ۣ�����ɥ�ǡ������ܱ䣬��ʿ���ס��������Σ��ҷ����㡣��¶������������ᢡ���嬵��ͣ��������������飬��ϼ��������֮�ڣ��������������¿��ţ���Ϊ�ִ٣�����������ģ������߹ѡ������ǣ������ɡ��������ƣ�ί�����������Ǻ�Ϊ����Ҫ���ҡ��ij����ϣ����ǵ��¡���ɢ���徭�����������硷���š����ټ����飬���ôӻ𡣿�־ɽ�ܣ����ĺ���Ԫ��Ϊ�ۣ���Ϊ��������̫�壬������ұ���� �ٳ�ͳ��������ʫ��������ʫ���������ڵľ����뾭�ѵ������ʣ���Ԣ������������֮�С�������ǶԱ�һ�������������ʫ�����ѷ�������֮�����������Ƶĵط���ֻ�������������б����Ϊ����һЩ���ˡ���Ȼ���������ܵ��ٳ�ͳ��Ӱ���Ϊֱ�ӡ� ���������ʫ���У��������ֶ��������ǡ������ӡ����������ӵ������������д�Լ����������������档��ǰ������ʫ�˸�ӽ���ɣ������̺���������ǻ�֮�У�����ì��ʹ�ࡢ��������������Ϊ�����ġ���Ȼ����ʵ�в���ʵ���Լ������룬��ô��ֻ���˻ص��������ڴ���Ļ����й���һ��������翵��������硣��ˣ����������㻳��������������ʫ���һ��������ɫ�������ĵ�������ʫ���ƣ�������ʼ������ʫ�����ģ�����֮ͽ���ʶมdz��Ψ��־�������ּң����ܱ��ɡ�������ʼʱ�ڵ������У�������������ʫ�Ĵ���������ȡ�õijɾ���Ϊͻ���� ��һ������ּң����������ʫ ����ġ�ӽ��ʫ���У��в�������֮��������ʫ��δ��������ƪ�������еĵڰ�ʮ�ף� ���������ˣ����������ȣ���ɽ�����ǣ�����˭���ڣ������г��̣���������֪�����������P�����н���֮����������ݣ������ڽ�ʱ�� ʫ�˽������롶ӽ��ʫ��֮�ڣ���˵�������С�ӽ���������ʡ���ƪ��ƷŨ����ʫ�˶�������ӽ̾��ʫ�еġ����ˡ���ʫ�˵�������С���ӽ��ʫ����ʮ���Ǹ�ӽ�����ˡ���רƪ�� �����м��ˣ�������չ⡣���������£�������˫諡�����ҫ������˳���������Ǹ�����˼�����ǵ����������������䣬���������衣Ʈ�u����У��������Ұ�������δ���ӣ������ø��ˡ� Ȼ�����˲������ɡ������У��������������·��ţ����������������ҡҷ��С��һ����������������ʱ�����ܱ����ۡ��ڡ�ӽ��ʫ��������ƪ����������ɵ���д��ӽҲռ�кܴ�ı��ء��ƴ�ѧ������˵����ӽ����ν���黳������κĩ����֮�������ǻ������������д�ʫ�����ʱ���ʾ�֮�飬���������ѡ�������Ȥ��ʵν����Ƿ����߲���̽��֮����������ѡ�������������Ͽ����ˡ�ӽ��ʫ�����������ʣ�����ָ�����еġ��顱ͬκ��֮�ʵ���ᱳ�������й�ϵ�������ڷ�����ӽ��ʫ���е�ʮƪ��ƷʱҲָ�������˽�ӽ����֮��Ҳ��ʮ�·�һʱ��������һ�����ɡ�������ʼ��˪֮�꣬���Ԫ����֮�꣬������ɧ���������ܣ�η����֮�ֻ�����ӽ����ͳƪ���������ף������ٸС�Ω�伥��֮ʲ������ʱ�¿�Ѱ������ͻ����ܣ��������飬���ӵ������������ء����ޱ������������֮˼����ν��������ܹ���֮־�������������ƺ��������£�����ͬ־�����ģ�Ŀ�����ᡣ���ܱ������ʣ��������һ�¡���»�����ӽ���ƣ�������ټ���ʶ�ܼ��ප������Ի����躹��ճ�������֪�ǻ��硣������˹�⣬�鲻���ԣ���Ŀ���ģ������͡����Ŀ����һϵ���ش�������±䣬�������ĺڰ��������ļ������������ǽ����ڵ�ʱ�������̬����������������������ط�����ӽ������ʫ�˵�������ȡ���������ӽ��֮����ͳ��ƪ������Щ����ʫ��δ�ӱ��⡣ʫ�˽����ɵ�ʫ����д����֮�飬ʹ����ı��KΪ�������������ν���鲻���ԣ���Ŀ���ģ������͡�����˼��˵�������ʫ��ֻ����ᣬ�����Դ����ɼ�������Щ��Ʒ�ı�������ȷ�Ľ�ʾ�� ʫ����Ľ���ɵ���ٸߵ���ƮȻ���ۣ�˵��ֻ���������ɲ��ܰ�����ʵ��������ɵĿ��ա���ӽ��ʫ������ʮ���� ��������ʢ�����պ����ġ�ȥ��������������ƾ����������¶����������ơ��뾰����ɽ��������������ʥ�ٳ�����ϧ�ź�������ȥ����������������Ը��̫��ɽ�����������Ρ��游֪���������������ۡ� ʫ�������游�������ۣ�����ǣ�ң�ϣ������̫��ɽ���������һͬ���Ρ���������ֺ���Զ��������ȴ������ģ�����Ҳ��ͬ��¶һ�㣬ת�ۼ��š���Ʒ������Ķ����ɵ�Ľ֮����ʮ��ǿ�ҵģ���������λ���ɳ�Ϊʫ�����������������塣��ʱ��ʫ�˻������ɵ�ʫ�����Բ�κ���������ͬ�飬��Ԣ�Բ�κ�Ļ���ͱ�ϧ����������ˡ���ӽ��ʫ������ʮ�壺 ����ʮ���꣬���������������ï��������ۻ����档�ɼ���������лʱ�ˡ��ᵴ��㱣�Ʈ�u���������ɷ������裬������������ ���ڴ�ʫ����ּ��ǰ�˽��Ͳ�һ�����ƽڵĿ��۱ȽϿ��š�����˵�����Ǵ�ʫ�˸߹��繫����Ҳ����κ־�����߹��繫�����ʮ����λ�����꣬��λ֮ʱ�굱ʮ�塣ʫ�г����ۣ��硶־���ص���̫ѧ�������¿�֤��������Ի�����߹Ż����ɣ������дǣ�Ȼ����������Ե����������ʫ���ᵴ�������˸߹����ָ?���������ӽ��ʫע����ҳ78~79������Ϊ��ʫ��Ϊ�˵��߹��繫���ֶ����ģ���˵�ɴӡ�ʫ�����������ĵش��࣬��ӱ�Ʊ磬���������ᵴ³ç���װ��������������������е�ͬ�顣�֡�ӽ��ʫ������ʮ�壺 ������ͷ�?�˵���ء�׳����ʱ�ţ���¶��̫����Ը���˺��Σ����ղ��ƹ⡣���·������ƺ���������媷����ȱ���Զ�����������DZ����������ɴ���������ʱ·��������̫���ɰ��衣 �����Ͽ�������һƪ����֮��������Ʒ�ĸ�������ǶԲ�κ�Ļ����ͶԺڰ��������С���ʦ�~˵������Ը���˺��Σ����ղ��ƹ⡯������κ��Ҳ�����·�����������ܣ���֮���ɶ��ѡ�����ת���ԡ����ӽ��ʫע����ҳ45��ʫ���ػ�����֮־������������֮�롣���������У�κ���Ĺ��������峿��¶��һ����ֻҪ���ҵ�����һ�գ�����ɢ�����ˡ�Ϊ�ˣ�ʫ������Ƿߡ�ʫ��ִ��������Թ���������������ʫ������ס������̫����ϣ������Զ��ҫ��أ�����˼䣬��Ը���Ƕ�ô����!Ȼ�������·�����ƺ���Զ�������象�����ʫ����ʮ�����ԣ���������̫�壬����������������˼�黯������δ���ϡ�������ȫ��ʫ����һһ�������κε��龳֮�£�ʫ��ֻ�ܼ������ɾ����ڻ���������������ʰ��������Զ�����յ�ʱ·��������̫��֮�С� ����������ʫ���Կ�������ӽ��ʫ���ڸ�����﷽����ʮ�����ġ������ڶ��������ָ�����������������ض�����ỷ����ɵġ��塤���DZ˵�������ӽ�������������ң��˼��ˣ����䰧Թ���m������Ī���Ȥ�����֮ʱ����Ӧ���֮ʫҲ�������߱���ʱ����ʵ֮�������ӡ�����ͳƣ�����ּ�忢����ּң����ʵ���Ȼ�ֵ���������˵ʫ�����������������ʫ�������²ᣬҳ531�������ϵ���һ�۵�����Ϊ��̵ģ��ر���������������Ͱ����ʫ�����ѧ������������Ʒ������ʷ�����ӣ��Ͷ�Ȼ˵��ӽ��ʫ��������ʱ���أ�Ҳ������ʵ�ʡ���ǰһ��ʫ���ۣ�ʫ��ʵ��������������λ����Ӱ����֣�����ʹ������Ϊ��������ʫ��Ҳ�Ͳ��ỳ��ʫ�������η����Ԣ�⣬�����ʱ�۲�֮��������ʩ��Թ�ɡ�������֮����ʫ��ѡ�����ģ��ˣ��Ӷ�Ҳ�ͱ����˸��˵���ν����������ν��ӽ��ʫ�����ؼ�������������壬���˶��ڸ��̣���ڵ������˼��������������������֮�����ף���ڵ������������֮���������֮�����㣬�п�֮�����⡱����һ�����Ϊ��̡����١�������������飬��ʹ����ı�����Ϊ����ڵ�������������ˡ���ּң�����ɫ���Դˣ��Ŵ������ۼҶ��в���������ν�����������ҳ�����������������ȷ�ӽ����ÿ������֮ൡ���־�ڴ̼������Ķ����Σ��ٴ�֮�£�������⡱������ѡ����������ӽ��ʫ����������˵�����ڶ�Ŀ֮�ڣ���İ˻�֮����������ּԨ�ţ���Ȥ�������ӽܡ�ʫƷע����ҳ23������������Ϊ�����ڼ��С���������ߢ�ࡷ��������ʫ������ҳ774������Ӧ��� ���˼ij�Զ������ʫ���ڱ�����������С����ԡ���������˵����ӽ������ƪ������ָԶ������֮����ʣ���ָ��Ҳ���ij��Ҷ�̸���⣬��˻¶�Ľ���ɣ���������һ���������顷���ǹ�Ү�����������������ǣ�����κ���������Ҽ����ע����ҳ89����������˵�������ڡ�ӽ��������ּ��ΪԨԶ��������֮�ȥ���ˣ������ټ��������ոš�������ʫ�š�������Щ�������ȽϷ�����ʫ��ʵ�ʡ� ����������־�����������������ʫ ��������������������ʫ��������д�����������黳���������������ġ�����ʫ���������ġ�����ʫ���������ף�����һƪ������ʫ�����ڽ���о䣺 �����Ͻ��������ޡ�����������Уע����ҳ327�� ��һƪ��Ʒ�DZȽ�����������ʫ�� ң��ɽ���ɣ�¡������У�����һ�θߣ���������˫��Ը�������£���·����ͨ����������ȥ�����Ƽ�������Ʈ�uϷ���ԣ�����·��꣬������Ȼ����������ͯ�ɡ���ҩ��ɽ�磬��ʳ�����ݣ����������ۣ����ѼҰ�ͩ����������أ��Ÿ�����ߣ��������˱�˭�ܶ����١� �����ɴ���ν������ҹ������֮־����ת���ԡ�������Уע����ҳ371������������ʫ�����⡣������������ʮ��ǿ�ң�������һ���ɾ��������ˡ�ʫ��ͨ���Ի����е��ɾ�����棬Ҳί��ر����˶���������IJ�����������������������������֮�еģ��������ڡ���������ʫ���ס���һ��������С���������д���� ˼�����ǣ������ΰ˼���˼�����ǣ������ΰ˼��������������������ڣ�������ҩ����������������̫�ͣ�������ɫ��������֮��˼���ΰ˼��� ����ӽ̾�ľ�ʽ����ʾ��ʫ�����ɵ��Ϻ����顣ʫ����ͼ���ɾ�����þ���Ľ��ѡ�������˵��������ҹ��������������֮ʿ���䡶����С�����Ĭ֮�£�������ʫ�����ܶ�֮�ԣ������ұ��ߣ��������⣬��֪ʶ����������Ҳ���������ոš�������ʫ�š�������������Ϊ�пϡ���Ȼ������Ҳ�ǽ�����������ġ� ����������ϣ�����������ʫ�����ͬ����Ʒ����ͬ������˵����־���������������ν����Ϊ���С�����������Զ�������ӽܡ�ʫƷע����ҳ32��һ��������ָ��ҹ��Ʒ��������Ȼ��������������������Զ�γ���֮־�Ǻ������εģ���Ҳû�м���ʲô���⡣����������ʫ���ס����ߣ� �ǻ���ɽ��Ϣ���ڲ�ǣ��ǻ���ɽ��Ϣ���ڲ�ǣ����ǣ��²���Ӣ���ܵ���ĸ��������ͥ����ң���飬ǧ�س�����������֮���ǻ��ڲ�ǡ� ������˵����������С���Ϊһ�壬��ȡ���⣬������κ���ŷ硣����ת���ԡ�������Уע����ҳ52������ʫȷʵ��һƪ���˿������Ʒ��ʫ�˻����ǻ�����ɽ֮�ϣ�Ϣ���ڲ��֮�У���ҩ�ܵ���������ͥ�������������ң������������������Ʒ�����ʳ������¸ս�����κ��۵ġ�����С�������������������Ź��������ʫʮ���ס��� �˷���Σ�Զ�������к����ǣ�Я�־��Σ�����̫����Ϧ�����ݣ�����ӽʫ���������ǡ� ��ʫ���֣�Զ�ο��䣬���������������������ź����ۣ��������ˣ�������������־���� ������ʫ��ӽ�������������ʫ�˳���������Ը����������ֱ֮������͢��˵��������ҹʫ������ȥ����һ����������ʸ���ʳ������ѣ���κ�����䣬����һ���ֱʡ�����ת���ԡ�������Уע����ҳ19����Ȼ������Ҳ���ѿ�����������ʫ�����ۻ�������Ƚ����ء�����һЩ��Ʒ������ּ��¶��ȱ����Ⱦ�������������Dz������������ʫ���Ტ�۵ġ�������Ϊ��ʫ��ڦֱ¶�ţ���Ԩ��֮�¡������ӽܡ�ʫƷע����ҳ32��������½ʱӺν�������ģ�Ȼ��ʫһ�ٴ���������ʫ�����ۡ���������ʫ�����ࡷ��ҳ1405�������������ʫȱ������֮�����Եġ�������˵������ҹ֮ʫ���ң�����֮ʫ���ݡ��������ոš�������ʫ�š��������ֲ�ͬ�����������ʫ�˵����˼���ر����Ը��ϵIJ���Ҳ�����й�ϵ�������ڡ����ĵ���������ƪ����ָ���� ���������Ǩ������ѧ�ɣ��������У�����Ѫ��������ʵ־��־�Զ��ԣ�����Ӣ����Ī�����ԡ����ԡ��������m�Σ������ݶ���Զ����ҹ���������˸߶����ң����� ������Ϊ����������ͬ����ԭ���������ǵġ����ԡ���ͬ����ҹ��ֱ�����С������±㷢��������ǡ������������ڡ���̹�����ڴ������������顷������������ǡ��m�Ρ��� ��Ӧ��˵�������ɡ���ʫ��������ǣ������ȡ�������ʫ������������������ͨ��������������֪������֮����ʫ������ˡ���ӽ��ʫ������ʮ�����б������飬�ޱ�����˼���������������ǻ�֮�У����ڰ���֮�飬�������ǵ�����ʫҲ��������ġ����顱�롰��˼�����ر��������Ʒ���䡰��ȡ�������������и��ߵ�������ֵ��Ԫ���ʡ���ʫ������ʮ�ס����壺���ݺ�ʫ�ʼ����飬�����ܽ��j��ƽ?�����˭��ã�����һЦ�ᡣ��������������ʫ�����ʮ�ּ�ע����ҳ54�������������ݺ��ʫ��������������˵��������磬Ҳ���쾡�µ��㷢�����õ��黳������ν��象�����ʫ�������ǿ���ӽ����������֮ȤҲ������ʫƷע����ҳ39�����Դ�������������Ҳ����ȫǡ���ġ��������������ʫ���������ң������ǽ����������飬�ȼ̳��˳���������������ͳ��ͬʱ��Ϊ��象�����ʫ���Ĵ����������������顣�塤������˵������象�����ʫ���������ӡ�Զ�Ρ�ּ֮������ǣ���ɼ��ơ�����������ղ�ԡ����������š����Ķ���������ܵ�����ԭ��Ӱ�죬�������������ʫ���ڹ��Ͻ�����ԭ��Ӱ��Ҳ����һ������ʾ���á�����������Ʒ�������ֵ�������ᣬ������������ʵ��ڤ˼���룬��������ʵ���������������ij�ֿ������ĸ�����У���������α�����̺ͺڰ�������Э����־�����۷�ӳ��ʫ�˽��������滳���ȱ����˿��������ĺ��飬�ֳ������Ž����������Զ�r�����ˣ���ʾ��ʫ�˲������ľ��磬ʹ��������ʹ�˸зܡ���ʫ�˱��µ���˼׳���У����ǻ�����������С�����˵��������ʦ����Dz�ۣ��ʹ������ʫ�����������죬�����ͬ�ɡ����������ĵ��������ԡ�����Dz�ۡ��롰��ʫ����Ȼ��ͬ��������Ͷ��������ǹ�ͬ����������������ʫ�Ĵ�������Ҳ����ˡ��������ʦ��ʹ������ͬ�������������Ľ���ʫ��������֮������������������֮��������ǧ� �� |
��ѧ��վ����Ȩר�У�����ת�أ�ע��������������ã���Ϊ��Ȩ��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2917824
010-62917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