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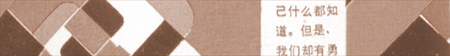 |
|
|
��Ԫ������һ��������
|
|
|
|
|
|
|
||
|
�й�ʿ��֮��̸������̸�������ʮ��ͻ�������۵IJ�������̸�ұ���߱��ģ���Ϊ��ŵĸ���ֱ�Ӿ�������̸��ʤ����Ҳ��ӵ�Ӱ������̸�ҵ�������ǰ;����ˣ�������һ�������ʷ��չ���������������Ǽ������̸�Ļ�����ʶ�� ����̸�磬�Թ���Ȼ��˼���Ծ��ʱ���;������ɵ�ʱ����������һ���������Ʊ������紺��ս��ʱ�ڵ����Һ��ݺ�Ҷ����Ƴ����۶�����ʿ�֡�����ѧ����ʮ�����ӱ�ŵģ�����Ҫ���������л�ʩ����������ѧ˵�ɡ�ׯ�ӡ�����ƪ���ɼ�һ�ߡ�������ƪ�����й��ִ������һƪѧ��ʷ��ר�����۴���ʱ������ѧ�ɵ�ѧ˵�����Ӻ������ӱ����ڴ�ƪ֮ĩ����Ȼ����Ϊĩ������ʩ��Ϊ�κ����ﶼ�������㲻��ģ�����˵������ر���ɽ����ƽ���շ��з������﷽�������������Ϸ���������������Խ�������������ɽ�Ҳ����֪����֮���룬��֮��Խ֮����Ҳ������������һ��Ҳ����Ҳ����˵������֮��û�о��ԵĽ������𡣻�ʩ�Դ����˼��˵Ŀ��ţ����ҡ��Դ�Ϊ�������¶������ߣ�����֮����������֮������ʩ�����ܳ�������ë�������㡱���������ѡ��������ȡ��ȹ۵㣬�������ڹ�硣��ʩ�빫���������Ƴ��ڱ�ġ�����ʩ֮��̸������Ϊ���ͣ�Ի�����׳��!�������Կڱ�Ϊҵ����������������ʵ�ʵĹ�ϵ�����硶����ƪ����˵�������Ź���������֮ͽ������֮�ģ�����֮�⣬��ʤ��֮�ڣ����ܷ���֮�ģ�����֮��Ҳ��������������ڡ��Է���Ϊʵ��������ʤ��Ϊ�����������ڲ���Ҳ��������Υ�����������ۺ���ֵ��Ĵ�˵����սʤ���ˣ�����ʾ�����ڲ�ͬ�������ӡ���ʮ����ƪ���ƣ��������������������壬�����ι�˵�������ǣ���������ݣ�������ã����¶��ѹ���������Ϊ�θټ͡�Ȼ�����֮�йʣ�����֮�����������ۻ����ڣ��ǻ�ʩ����Ҳ����������Ϊ���ҵ�ѧ˵�����ڹ������Σ�û���κ��ô���Ȼ������֮�йʡ�������֮�����������кܴ����ƭ�ԡ����Ӻ�������������������˼��������������壬����֮�����в�𣬴˲����ۡ����Ƕ����б��ۣ������乲ͬ�ĵ�������ս��ʱ�����ݺ��˼������һʱ����ʱȺ����¹��Ӣ�ܻ������⽻����Ƶ�����ݺ�֮˵��硣�̸��֮ʿ�������γ�һ��̸��֮ѧ�����ǡ����غ����ܵ������еĴ������������ͨ�����������ܼ��������������ꡱ��310
B.C.���� �������ؽ����ݺ�֮��������λ����������ĽЧ֮������κ�˹������ߣ���ԻϬ�ף�����̸˵�����������մ������������¥��֮ͽ����硱������£����Ա�թ��ߣ�����ʤ�ͣ����ǡ��ء��������� �ݺ����ƾ���������ݺ����ϱ�ڸ���ʱ�������¼�˵���Ի�ȡ�߹ٺ�»�������������ԣ�����ս�����ۣ���ʿ��ӿ���Ӻ��ı�����̽��ƣ�ת������ɴǣ���ǯ���侫����һ��֮�棬���ھŶ�֮��������֮�࣬ǿ�ڰ���֮ʦ����ӡ�������壬�嶼������⡣���������ĵ�������˵�����й�ʱ���ı���֮����������ѧ���Լ��ݺ�ҵı���ңң���졣�Ӷ���������������֮�縴������������ʢ���ϳ����������������������ǧ�Ҿ��㣬��������������Ŀ��Ͼ�ӡ� һ����κ֮�ʣ��йű��Ŀ��� ��һ������ʱ�ڵı�� �Ժ�����Ժ�����˼��ר�ƣ��й�֪ʶ�������ټ�����������������Ҷ����ѧ����һ��ľ��濪ʼ�����ƣ����DZ���֮�罥�������飨ҳ7������Ԯ�������顤����������ν��������̫ѧ�ۻᳩ̸������Ŀ֮Ϊ����̸�����鸡��̸֮������˵����ʱ��̫ѧ֮�б��۵ķ����Ѿ�ʢ�У��������б�Ŷ���ʵѧ���ʳ����ɱ�֮�������顷�����ˡ����ڴ����� ����̫ѧ��ʦ���ٸ����ߡ�����߷��Ը�ÿ���ڣ����������ͣ��������ۡ��ڷ�����ф��̸�����ƣ���ÿ����̾Ϣ��������ʼ�뾩ʦ��ʱ��Īʶ����һ��൷������Խ������ߣ�����֪���� ����֮���Լ��������ߣ�����Ϊ��̸��������������֮൷������ڣ�Ҳ����ڲŲ���ϵ�������顤�����ڴ��������ڡ���̸�ۣ������ơ�������ƽ�չ��ӵ�����Ҳ��Ϊ��ʿ����л������á�����̸�ۣ�����ʢ����ÿ�������ڣ�δ�������մ�ҹ����ͬ�ϣ��������ڴ�������л�紫�����������顷����0�ϡ���Է�д������ء��� ������Т�ȣ�����������Ҳ��������֪�������������ˡ��ؿڱ磬�����ռ��ԣ�����˽��֮Ի������Т�ȣ�����㡣�����飬�����ߡ�����DZ��֮��Ӧʱ��Ի������Ϊ�գ�ТΪ�֡�����㣬���徭���ӡ������ߣ�˼���¡������ܹ�ͨ�Σ��������ͬ�⡣ʦ���ɳ������ε��?�����ߴ��L����֮�ŽݽԴ���Ҳ�� ���ز�˼���ݣ��������ݣ����ڳ��ϣ�����̾��������Ҳ�ǡ��Ƕԡ���ר�ҡ������顷����0�¡���Է�д������á��� �ٱ粩�������ġ���������ռ[��]���ܴǶԣ�ʱ�������ã�Ī������硣������ڡ����ʲ��̺��ɡ� ���ܴǶԡ������ó����Ӧ�����ݡ��ڵ�ʱ���������Դʣ���������ۣ����ر����������ġ�����ĩ�꣬ʢ�����飬̸��֮��IJ��������������й�ϵ���μ�����ҳ2~4�����������漰�Ķ����������������������鷽���ר�ң�������ڡ����ں����ߵȵȡ��������Ρ������������𣬱�ʿ�Ǿ�ǯ�ڲ����ˡ�ֱ����ĩ������ʱ��������֮��Ÿ��������� ������ ��ĩ������ʱ���ı�� ����ĩ�꣬�ܲ�Ю���������������������ķ����ܲٳ�����ѧ�������γ����������˼��š����еĽܳ�֮ʿ�����ӣ�177~217�������գ�156~217�������壨��~217��������ʫ�Ĵ�������������Ҳ�Ա���֮�ų���һʱ��������־�����Ӵ�������֮ע�������ԡ������Ӳżȸߣ�����Ӧ��������һ��������Ȱ˵������˳�ܲ�һ���������������֣���˵�� �������ţ��ܹ����˽�Ҳ�����Թ�ʱ����ı��������Ԭ���ڹٶɣ�����Ȩ�ڽ��⣬��������¤�ң��������ڰǣ��������ĵ����ߣ�����������ʤ�ơ�����֮�£�ȥ�Ϳ�֪Ҳ����ͬ�ϣ�����֮ע������ʿ������ ���������ܲٵĹ�ҵ��Ȱ˵�����������꣬Ӧ��˳�����Թ�ܹ�����ͬ�ϣ���ٲȻս���ݺ��֮���ڡ���������д��һƪ������ϭ�ġ�ΪԬ��ϭԥ�ݡ�������ѡ�������ģ�������ʹ��ܲٵ�����������丸��֮���С��������չ�˳�ܲ٣��ܲ�˵��������Ϊ�������飬������״�¶��ѣ����ֹ�����������ϼ�����а?�� ���ջش�˵����ʸ�����ϣ����ɲ���������ͬ�ϣ�����ע����κ־��������֮ϭ�����ڽ������꣨200��������ʱ���ڹٶɴ�ս֮ǰ���ã���ֵ˫����������֮ʱ�����մ����Լ��ʮ���꣨�����ܳ������������������ס������������Ӽ�����ҳ395������ν��ʸ�����ϣ����ɲ���������ν�������ȣ�����������ʵ�DZ�Ը�����Լ�����Ҫ�����Խ��Լ�������������ι�ȥ���ܲ�һ���Ͳţ�����Ҳ����Ȼ�ڻ��ˡ�����Ŀڲ��ڡ��������ӡ�����Ϊͻ��������˵������һ0��Т��ע������ʿ������ ���Ա�ݣ�����Ӧ��������ƽ������ˣ���������ʹĥʯ��������з������ߣ����������ɫĥʯ�������Ի����ʯ����?
����������������������Ի����ʯ����ɽ����֮�ۣ�������ɫ֮�£��ں�����֮�䡣ĥ֮����Ө����֮�����ġ��������꣬��֮��Ȼ���������������ƶ������ꡣ���۹����Ҵ�Ц��������֮�� �֡�����־�����Ӵ�������֮ע�������ԡ��� �ĵ۳���������������ʦ��������ȡ��Ϊ�����鳰���ƣ�����������Ϊ���ڼ���֮�֣���������֮�ࡣ����ȡ֮�������䲻��Ҳ�������Ի�������ž�ɽ֮豣���Ԫ��֮�������֮�飬����ʿ֮�ã�����֮�𣬵���֮�ף��@��֮β���̳�֮�������ı��ߣ�����ʯ֮�£�DZ����֮�У������ǧ��֮�ϣ����ʳ���֮�⣬���δ�ܳ��Խ�������Ҳ����������������������Ҳ��������������������Ҳ�������ݳ��ɶ����������£��κ�ʼ���ũ���ȳ������������������������Σ���ʵ���죬�п���Ҳ�������ּ��������ǣ�������Ϊ������װ������� ��Ȼ�����պ�����ı������Լ������ڲ����ֵܣ����������йء�������κ������¡�������ű�֮ʿ���кܶࡣ���ϴ�ű���ˣ���Ī����Ŀ����������־�����������ۼ͡�����֮ע����κ�ԡ���������趡��Ա�ۣ�ÿ���²������룬����˵�����£���������̫������š���������־�����ˡ�����趴�������֮ע�������ԡ������ĺ�͡�����в��ۡ���
�����ĵ�Ϊ����֮����ÿ��ᣬ����һ������ʿ����������֮�����߶��֮�Ρ���������־�����š��ĺ�Ԩ��������֮ע��������������ա����IJŻ��磬�ٵ������ꡢ��������־�����Ӵ�������֮ע�������ԡ�����Ӧ�ꡰ���Բ��ţ���̸�ۡ���ͬ�ϣ�����������¼�������ȵȡ������ͺ�����ڱ��ۣ� �ϸ��ֹ��٣������ɴ�����֮���۽�ѧ�ʣ����ơ����﹫��˾���������á������á����ϡ���ν�����ϡ�Ϊ̫�٣���ν������Ϊ�����ң�������ɹ��������̡���Ϊ�˻��ݣ��Ƴ��ۣ�����ګ�ڣ���ʱ������Ӧ����ν��Ի��������߾�Ϊ���������ӡ�����Ի����ֱ����Ϊ��ʹ������������δ��Ҳ���� �����־�Ȼ��������Ҳ���������������빬���ڶ�Ҵ��������Ǐ��ֲ������ʱ�����꣬�������ʡ�������֮�����ʲ���ȥ�����������ϣ�ס�ڵ��ߡ�ֲ�����Ȳ�ȥ���ֲ�Ϊ����פ����ʹ�䳣�������ι٣����ƣ���ة���ı��Ҳ����ֲ����Ի����Ӧ����ͻ�к��?
����Ի���������֮�壬���������������֮�ϣ�δ����ʿ��Ϊ��ʿ�����Ҳ����ֲ��Ի�����������ԣ�Ϊ�˸�����������Ӧ�����?
������Ի������������һ��Ҳ���������ֳ�����ֲ֪��֦���������ȥ����Ϊ̫���ԣ���Ϊ�硣��������־������������DZ��������֮ע����κ�ԡ��д����� ˾��������151~230�����������鷨�Һͽܳ���ѧ�ߣ����ڱ��۷���ʤ���ϸɣ�����ȡ���������ֵĵ�����Σ�����Ҫ���ڿڲ�ʤ��һ���ĩʿ�ֵ����ֳ��дDZ��Į��������������й���̸���кܴ�Ӱ��ģ��μ�����ҳ114~115�������е�̫����ָ��ا�������ֵܶ��ں��������ı�ʿ�ر����ͣ��������������߾ۼ��˺ܶ��������˲š�������־��������������֮ע��˾���롶���ݴ���ƿ��ڣ�153~208���� ��̸���ӯ��ٲܣ��������ţ�������У����¿�ʵ���ѿ�Ϥ�С� ���dz��ڱ��۶�����ʵ���ˣ���������Ȼ���ˣ�ȴ��������ʵ�ʣ��ɼ�����ĩ����̸���鸡��ʵ������ȷʵ��ԨԴ���Եģ���������ѧ˼��ĽǶȽ������ڵı���Ҳ�п�ȡ֮������Ϊֻ��Զ����ʵ�ĸ�̸���ۣ����п����ݱ�Ϊ��������ۡ����ں��Ծ������ʵ�������͡�����������ۣ���������һ����˼������ κ����ѧ�ĵ�������������۵ķ�չͬ���ġ����̡��������˽Գ��ڿڱ磬����ѧ�ķ�չ���˺ܴ���ƶ����á���Ϊ��ѧ�Ҽ�Ҫ����������Ҫ������˵�����Ρ�������������泤�����������־�������ˡ��ӻᴫ��˵����������������ɽ��������֪����������������Dz��ݱ磬ע���ס��������ӡ���������֮ע�������ָ��á���ۿΪ�䴫Ի����������ۣ���ʮ�࣬�á����ϡ���ͨ�����ԡ�����ѧ����������ۺ���˵����������ƽ�干˵���ϡ���ׯ�������ס������������������������֮������������־��������������֮ע�������������ǡ��롰������ϣ������ڡ��ǡ��ķ����ͻ��һЩ�����ǡ������Դǣ�Ҳ���ǿڲš������ĵ�˾����˵���̡�����������������˵���Ʒ�塷��һ������˼��˵���ı��������ɵù��֣�����Υ�����������俴������ղ�ı���ϡ���ʵ���̵Ŀڲ�Ҳ������������һ��������ǰ�������Ĺ��������εIJ����Ѿ����ֵú������������ҳ83���� �⡢��������ʿ�ˣ��������⽻�Ĺ�������ʾ�Լ��IJŻ������ϱ�ڣ��������ǣ���������עĿ��������ʹ��֮���サ����ΪƵ�������ݻ����������ܹ�������ʤ��������־�������ˡ���嵴����� ���˶��꣬ة��������������ѡ�ӭΪ��ݣ�Ѱ�������ɽ�����ˮУξ����Dzʹ������Ƹ���ٹٽ������ɡ����˽Լ����δ��������Dzʹ��֮����Ի�����˺���Ҳ?
����Ի��������ѧʿҲ��������������Ի������ѧ��?
���Ի�������ͯ�ӽ�ѧ���α�С�ˣ����¸���Ի��������ͷ��?
���Ի������֮������Ի�����ںη�Ҳ? ���Ի��������������ʫ��Ի�����˾����ˡ����Դ���֮��ͷ������������Ի�������ж���?
���Ի�����촦�߶���������ʫ���ƣ��������ھŸޣ��������졣����������������֮?
����Ի����������������Ի�����С���ʫ���ƣ����첽���ѣ�֮�Ӳ��̡����������㣬���Բ�֮������Ի���������պ�?
���Ի�����С�����Ի��������? ���Ի��������������Ի��������֪֮?
����Ի�����������������Դ�֪֮������Ի���������ڶ���?���Ի���������ڶ���û���������������죬Ӧ�������������´����֮�ı磬�Դ���Ҳ�� �����ԡ��족Ϊ�⣬��������������������⣬�������ͱ��ˣ��䲻�ݷ��������������ʫ������Ӧ�������������࣬�侫�ʵı�ǣ������İ��о���С˵�����н��������д�롶�������塷�ڰ�ʮ���ء���������嵳���硱���ɼ�������嵵ı��Ҳ��ʮ�����͵ġ�������־�������ˡ����������� ����Dz��ʹ���⣬��Ȩ����ű磬�������Դǡ�������ݣ�ȨԻ����������֮����?
��������Ի����һ��һ��δ��Ϊ�͡�����֮���ݣ������ˣ�Ȩ����֮�� ����ƽ�ճ��ݵĶ���������������ʱ����֮����Ϊ��Ȩ������һ��˫�أ��ɽ����������Ȩ������ί����ķ��̣�����ν������֮����������֮������Ȩ����û����ŭ����������ڲ���о��죬�ɼ���Ҳ�Ƿdz����زű�֮ʿ�ġ�����ʱ�����⽻���Ǹ�����磬��Ϊ����Ч�ҵĹ��Һ;�����������ر��������Ե����κ��۱�ļ��ɡ����ǵ�������Ȼ����ȫ������̸�ķ�Χ����������������������ķ����Լ���������������������Ȥ������̸�Ļ��ķ�չ�϶�����Ӱ��ġ� ���������p�ı�ѧ���ۣ�������־�������� �ں�κ����ʿ�˳���̸��ķ�����Ӱ���£�κ�������˲�ѧ�����p�ڡ�����־��һ���ж��ⷽ�����������������ϵ��ܽᡣ���p�����֣�ͨ������ۿ��ʵ��Ӧ�������p�������Ŀ�ȫ����Ŀ����һ�ߣ���������־��������κ���p���p�ֿײţ������ˡ��Ƴ��й�ɢ�ﳣ�̣���ʼ�д;����ں�¼��ߡ�����κ־�����𱾻�����ۿ���������ۣ�����ĩ�������ƣ����ݽ���顶κ־������ۿ֮ۿ������������������ߣ��x��֮����������˶�ѵ��������ͣ�Ȼ�㲻Э���ײš�֮�塣��˵�ġ���Ϊ�p����ͬ�ϣ������Դ������ѵ��Ҳ�����ۡ����ϡ�ѵ��Ҳ����������ײ���������ӡ����ԡ�Ի���ܹ�֮��֮�p����Ҳ�������澫�ˣ����֮������˵���ǡ� ���p��Ϊ����ʱ�ڵ�����ѧ�ߣ�ƽ�����ӷ��ɵĽ������˲ŵ���Ρ�����������������־��һ�飬����ʱ�˲�ѧ֮��ɣ�����������Ҳ�ǽ��������й��Ļ��ıض��顣����Ŀ�ݳ����ۡ�����־��˵�������������۱��˲ţ������֮�������ڲ�֮�����ֱ���Ʒ���������ơ��ʡ���־�����½���¼�����ҡ�Ȼ���Ծ�Ϥ���飬�����˽�����������֮˵��»����꺫��������֮˵Ω�����ͬ���ߣ��ĺ���ͬ������ѧ��������ң�������������Ҳ������ͬ��������ͮ����ν������־���������д����ע�����аˡ�һԻƷ�������������Թ������̡�������Ի�ֱ���Զ��������ˡ�������Ի��֮��Ϊ��������Ŀ��������Ի����������̸�ۡ�������Ի�����ﳣʧ�����ȡ�������Ի��̫ƽ����ʥ�ˡ�������Ի����ҵ����Ӣ�ۡ�������Ի������������ӹ��Ϊ����������������־ñ����������ͮѧ�����ļ�����ҳ196��201����������֮ѧ����߶����ۡ�Ǯ����������Ϊ������־���ǡ��ҹ��йء��Ը����͡���personality types��������ר���������й�ʫ���й�����������������ҳ9�����������֮˵�����Ա�����������Ļ���ֵ��������־����Լ��������ʼʱ�ڣ�240~248�����൱�������Ȩ������������ʮһ��������������������ʮһ�ꡣ���p��ȡ�˶�����������Ʒ��ķḻ�ɹ������Ը����Ժ����������˲ż���ϸ�µ��������о�������֮������Ҫ��Ϊ��κͳ�μ���ѡ�ι����ṩ�������ݡ����p˵������ʥ��֮������Ī��������������֮����Ī���֪�ˡ�֪�˳��ǣ����ڲĵ���������֮ҵ���ӡ�����������־�����������������Թ�ʥ�ͽ�����֪��Ϊ����Ϊ֪���߿���ʹ�����˲Ŵ��ں��ʵ�λ�ã����õط������ǵIJ��ܣ��Ӷ�ʹ�������ҵĴ�ҵ���������������pд��������־����Ŀ�ġ� �Զ�����������ʵ֮��һֱ��ѧ��������ţ����䡢�ٳ�ͳ���ތ�����ɵ�����ѧ�߶Դ����ⶼ��ר�ŵ��о�������ѧ�ʽ����̣��Σ���ѧ���ֳ�����֮ѧ�����p����һλ�ܳ�������ѧ�ҡ��������ţ���������������ܵ����p�Ĺ�ע��������ѡ���˲š��������µ�ʵ����Ҫ���ڰ��Ѻ�����һͳ������֮����֮������Ծ����̫ƽ�������������������p���Զ������� ����֮ʿ��������ѱ����Ĺ������ժ���壬��ߨ���������ۼ�ף���������� ����ס���ָ�������ӵļ��ͬ��֮�ۣ������ۼ�ס���ν�Զ�������֮ʿ�����ڱ�ţ����Դ��ۡ���ס�֮˵���ɴ˿�֪����ʱ����֮����ʢ�����Ⲣ������˵���������������о����ҵ�ѧ˵��������ܡ�κ��˼���ۡ���ҳ172�������p���ڲ�ͬ���������������о�տ���о������ܵ��ܴ�Ӱ�죬�����ġ�����־�����Ǹ��ݹ���������ʵ�ۺ�������֤�����������������������ܸ�������Է������ʵĺ���Ʒ����ͬ�ϣ���ʵ���ϣ����p����֤���������ҵ�������Ҳ�кܴ�ͬ����û�����ˣ�Ҳû��ȡ���ķ�ʽ����������������ϸ�����ܵع�����һ���˲�ѧ������ϵ�����ڡ�����־�����˲�ѧ˼�룬��������־��⡷������ȫ������֣��Ȳ����ۣ����䡶����־��ʮ��ƪ��������ҫ���۱������Ĺ�ԡ����p��Ϊ���۱������һ�ֶ������Ը����������ͽᡱ����ʧ����崡������ܹ�����������⣬�����Դǹ���֦����Ҳ���ܲ��к���������������崡���ʧ�����p��������Ϊ���沩֮�ˡ������ص��ǡ������ĸ����������֮���ģ����Կ�Ϊϵ�����������������ǡ����뷺���̴��ǡ�������Լ�����������ľ���������־�������������Ϊ����������һ�֡�ƫ�š������p���������̸���۱硣�ĺ�ݡ������p���ƣ�������������̸���������ۣ��������꣬�����־ã�ʵΪ��ͥ������������(��ȫ�����ġ�����һ)�����p�ر����ر�ţ��˳��ڿ��������ʵ����Ҫ����˵���������֮�ˣ��������ģ���̸�����գ������Ծ�֮��һ���۵��£������۷��ƣ������۲�����Ȼ�����ܽ�������������֮���ɡ���������ʶ����������֪�ˣ�������¡��������������Դ�������֮��ϵ������ʶ�������������ˣ����pȫ�桢ϵͳ���ܽ��˹����۱�����ۣ�����ƪԻ������������֮�����ǿ��Խ�����Ϊһƪ���м�ֵ�ı�ѧר�ۡ����p����ָ���������ѵĹ����У��������֡���ʧ����Υ�����������ʧȥ��ȷ������Υ������ʵ����˵�� �������壬Ī�������������������ѣ����ܶ�֮����ι���?������Ʒ������Ҳ��������Ʒ����ͨ���˲������������ͨ������ʧ����ΥҲ�� ����Ϊ���������塱����Ҫ������ȷ�ĵ����������۱�ڵ�ѣ������ò���ʲô�������ԭ����������в�ͬ��Ʒ����˵IJ���Ҳ���в�𡣵������ֶ��������Թ�ͨ���˵IJ��ʸ��������鸴�ӣ��ɴ˶����µ��������������������������������������IJ��������ļң����о�ƫ���������ƣ�˵����ʧ������������ͨ�а��ܡ������߸��������������ѧ���۵�ȫ���� 1���IJ�֮�������p˵�� �������������ӯ�����棬��֮��Ҳ���������£���֮��Ҳ��������ʣ���֮��Ҳ�������������֮��Ҳ��������ͬ�����ڲ�Ҳ���������¡������ʶ��У��ǹ��������ϣ��϶��������������������ɼҡ� �������֡������������������ǵ��������������ԣ����ǵ��������������˵IJ��ʵ��Ծ����չʾ����ˣ��˵IJ�������һ�£���������ö��ܲ�����ʶ�������Ϳ��Է����������������������ˡ���ˣ���������������ļҡ��� 2����֮�ļҡ����p˵�� �ǹ�����ƽ����˼��������ͨ��Ȼ������֮��Ҳ�����Ծ�����Ȩ�Ի��ݣ��������٣�����֮��Ҳ�����Ժ�ƽ��������̣������ʧ������֮��Ҳ�����Ի��⣬����ԭ�⣬������䣬����֮��Ҳ�� Ҳ����˵������ƽ����˼ά��������ܹ�����Ȼ��ͨ��Ϊ����֮�ң����������࣬Ȩı��Թ��ˣ��ܹ��������ҵ����Ϊ����֮�ң������º�ƽ�ף��ܹ��������������ǽ̻����������������������ֱ��ʧ��Ϊ����֮�ң������������ܹ����������̽���⣬��Ӧ���ֱ仯��Ϊ����֮�ҡ����p˵�����ļ�֮�����죬���о�ƫ֮�飬���Է��������е�ʧ�������ļ�֮�������롰��ƫ֮�顱������ġ� 3����ƫ֮�顣���p˵�� ����֮�ˣ��������������۴��壬��벩����Զ�������������������Խ������֮�ˣ����ܻ��ӡ��۷�ֱ����������������˵��ͨ�����������롣�ᾢ֮�ˣ��ù�����ʵ��ָ��������ӱ�ƶ���������������¶�����֡����֮�ˣ��Ƿ������������£���ʶ�������������壬���㵶����ܡ�����֮�ˣ����ܳ�˼�������������G�������������Ҫ�����f��������dz��֮�ˣ��������ѡ�����˵�������ɶ����ã����������ת��������ˡ֮�ˣ������ٽݡ������壬���������ţ���ʱ����ٻ�������������֮�ˣ�������ǿ��ζ��������˳�ʶ������������ѣ�������������� ����֮�ˣ����ݶ����졣��Ȩ�ܣ������ζ���׳����������������ء� ��������p�ص��������˵�������ڱ��۵�Ӱ�졣Ӧ��˵����һ�ӽ��Ǽ�Ϊ��ӱ�ġ�����Ϊ���Ե��ˣ�����������������һ���棬�����۴��£����ֵú������㲩���Ҽ�ʶ��Զ����һ���棬����С�����Ե÷ŵ�����������ˣ�����������������һ���棬˵���������£������ط����������˽����һ���棬˵����ͨ������岻ͨ����ʩ�С��ᾢ���ˣ�ϲ�ý���ʵ�ʣ�һ���棬������������ڻ�������ӱ���ǻ۶��������꾡����һ���棬�漰��ĵ��������dz��Ƭ�档������ˣ��Դ����϶����������һ���棬�ƶ����£���������������ܣ���һ���棬�ۼ����壬���������Զ�����ȫ���������ˣ���������˼����һ���棬������̸������㲩�����ĸ���������һ���棬̸������ʱ�������ϲ������Բ����塣dz����ˣ����ܶ�����������˼���ǣ�һ���棬�������ʵ����ۣ����ġ����������ã���һ���棬̽�����ĵ������������Ѷ���ת�����鸡������ˡ���ˣ�����Ѹ�ٿ�ݣ�һ���棬��˵�������ǣ�����꾡���ֺ��ڹ淶����һ���棬���¾���������ٻ����������ܼü���������ˣ���������ǿ��һ���棬��ζ��������֮��Ч���Һ�ƽ��ͨ����һ���棬�����������⣬���������ܶ��ӱܿ��ѡ�������ˣ��������Ķ������죬һ���棬�漰Ȩ����թ��������������ֹ��׳����һ���棬�鿼�����ĵ����������ڹ����δ�⸡��ֵ������p����Щ�۵��ڽ�����Ȼ��ֵ�û�ζ�����кܸߵ�ѧ����ֵ�� 4������ ���p˵���������Բ����������������ơ������Բ�����������ָ�˵��������Ͱ��������ơ��ǡ��Բ���������ɵģ���������� ����̸��˵�����������ߣ�������ˣ����������ߣ��л�˵���⣬�������ߣ��д���ֳ����������������������ߣ��б��Ѳ�Ӧ���������࣬��ʵ��֪�ߣ���Ľͨ�ڽ⣬���ö������ߣ�����ʤ�飬ʧ����������������ʵ�����⣬�����������ߡ��������ƣ�����֮����Ҳ�� �����ơ��DZ��ѹ����о������ֵ������������Щ������Ǽ��������Ի��ˡ� 5��˵֮����ʧ�� ���p˵�����������ʤ���д�ʤ����ʤ�ߣ������Թ��ۣ������֮ͨ����ʤ�ߣ������������죬��������ʧ�ӡ�����Ϊ��һʧ�������ƫ֮�ģ���ͬ�з����ӡ�ͬ����⣬������ǣ�������֡����ƽ����ߣ�����������֮����֮��������˵Ҳ�������������Ҳ�����ƽ����ߣ�˵֮���ӷ���˵֮���ӷ��������ӡ�����Ϊ�ڶ�ʧ���������ߣ���һ�������£��������ߣ����Բ���һ�⡣���Բ���һ�⣬����Ҳ����˵֮��ʧҲ�����ˡ���ʧ��������˵�����о������ֵ����ֲ����������ν����ʤ���͡���ʤ�������й���̸���зdz�ͻ���ı��֣��μ�����ҳ126~128���� 6����֮�������� ���p��Ϊ���۱���̵��У��������ߵ�ʧ���������(������)��������������� �����ߣ������±����������ߣ��᱾����ĩ���᱾����ĩ����ǹ��ӡ��ƹ�ǿ�ߣ�����ʢ���䱾ָ���Խ���֮�����ƹ�ǿ�ߣ�������ǣ��Դ������⡣�������⣬�������ӡ�����ʧ�ߣ�ָ������
��������ʧ�ߣ������������ԡ������������ԣ���Թ���ӡ�����˼���˵�֮���������ˣ��˲���֪������Ϊ���͡���Ϊ���ͣ�����ӡ���ʢ��֮ʱ���������ȡ��������ߣ���֮ʹ�����������ߣ������֮�������˽壬�������ɡ��������ɣ��������ӡ�����������˼������Ҳ��������ǹʲ�˼��˵��������ֹ������֮�������������䷽˼֮�ʣ����˼��⣬����Ϊ���⡣����Ī���䲻�⣬�䲻����ŭ���ӡ� ���ǹ�����������������Թ�����������������������͡�ŭ��������Ϊ�������������Ƕ����ѵ����������кܴ���谭��һ�����е�һ���������������֮ʿ�ͻ�Զ�������ijdzأ�Ҳ�ʹﲻ������������Ŀ�ġ����p˵����������������֮������Ҳ��Ȼ���б乹���������á���˵�����ѣ�������������Ī֪�����ӡ��ɴ���֮��̸�����������ӡ������ϡ��������������䡱֮��Դ�������С��乹�����������ջ�ģ���������ٳ�����һ���Ƿǣ����ֻ�Ǹ��Գ�˵���������������ѣ��ͻ�Ī��һ�ǣ��Ƿ��ѱ档��ˣ������DZز����ٵġ������Ѽ�Ȼ����������������(���ڡ�������)����ôͨ��̸�������������Ŀ�����Ҳ�ͺ�С�ˡ��ɴ˿ɼ������p�Ե�ʱ��ʿ��̸�����Ҳ�Ƿdz��˽�ġ� 7�����������롰�˲ġ� ���p�������������֮˵��������Ӧ���ǡ��˲ġ��� �ǹʴ�������ν֮����֮�ġ�˼����ˣ�ν֮����֮�ġ����ܼ�������ʶ֮�ġ����ܱ��⣬ν֮�ĸ�֮�ġ�������ʧ��ν֮Ȩ��֮�ġ����ܴ�����ν֮����֮�ġ����ܶ��أ�ν֮�Ƴ�֮�ġ��������裬ν֮ó˵֮�ġ� ��������������������˵�Ƿdz���Ҫ�ġ�����˰��ߣ�Ȼ������ͨ������֮����ͨ������֮��������ͨ���ӡ����ܼ��а���������һ�ܣ���������ƫ����������Ŀ�ӡ���Ҳ����˵�����ϡ���������ϵƫ�������ߣ���������֮����Ϊ���֮�ˣ����ܡ�ͨ������֮���������ҡ���ͨ�ˡ�����ˣ����p˵�� �ȼ�˰˲ģ���֮�Ե�����ͨ���ԣ���ͬ����������������ԣ����ɫ��˳�ԡ��������������������ˣ�����ʸ����������ˡ����Գ�����������ֹ���������ˣ��������ȡ�д��֮����������֮���ܡ��������࣬����֮��������������������֮������˵ֱ˵�䣬����η�ɳ���֮������������֮ż�á��������ˣ�ȥ�Ͳ���������ʢ������л���t������ʤ�ѣ�ʤ�����档��ƽ־����������Ī�����ڵõ������ӡ��ǿ����۾���������Ҳ�� ���p����˼��˵������ͨ����ˣ���Ȼ��������ֲ��ܣ��ͻὫ����������ʵ�ʵı�����ȥ�������ͨ����˽������ͻ�����⣬����Ĭ�����������ͨ�˽������ͻ�۲�Է�����ɫ��˳Ӧ�����顣��Ȼ�������ֵ�����ȴ���Դ��������ҫ���������ԣ�磬ȴ����˶��Ծ�����ǰ�����õ��ԴǴ��Լ��Ŀ���˵���������������˾��ʿɶ�ֹ����ª�ʹ������ڱ������ϣ�ָ�����Ĺ�ʧ����ѹ�ȶԷ����ñ��˾���س������ԣ��������˷��ӱ����IJ��ܡ�̸�����ۣ������ʺȲ����⳰���Է��Ķ̴���Ҳ�������ҫ�Լ��ij���������˵��ֱ��Ȩ��֮�ʣ�û��ʲôη��ģ�Ҳû��ʲô���ġ��ܹ����ɳ��ӽ����е������������ܹ����Ͳ���ƽӹ���˵�żȻ���֡���ȡ���趼�dz����ˣ��뿪��ӽ�Ҳûʲô���������Է�ʢ�����ص�ʱ���ܹ�����ǫ��ѷл֮�����Լ��ڱ������Ѿ�ȡʤ��ʱ��ȴ���Դ˽������ˡ����˴����ľ�ƽ�͡�������û��ʲô���ԣ�Ҳû��ʲô�����ԣ�Ŀ��������ø����ĵ������������˾Ϳ��Ժ�����ͬ���������������ڵĵ����ˡ��ɼ��߱����������ġ��˲ġ����������p��Ŀ������ı�ʿ�� �������Ǽ����������p�ı�ѧ���ۡ����p����������������ʵ���ݵģ������а����ŷḻ���Ļ���Ϣ�����ԣ����Ǵ��Ե�������ԶԶ�����ġ�
�� |
��ѧ��վ����Ȩר�У�����ת�أ�ע��������������ã���Ϊ��Ȩ��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2917824
010-62917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