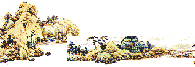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ƽҪ�뿪�����ߡ���У�ص�ί�����ˣ���������ˡ�������õ������Ϣ��Լ�Źⴺһͬȥ����ƽ�� ���ߣ����ţ�����ȥ������ǡ��� �����ˣ��Ҳ�ȥ�ˡ����Źⴺ��¶��ɫ�� ������ͷ����ȥ��϶����ǹܸɲ���������ɲ���С�����������ǵ����˶��������������ϡ��������������Źⴺ�� ������֪����������������ͷ�ۣ�����һҹû˯�ţ���ȥҽԺ���������Źⴺ���ѡ� ���������ȥ�ˡ���ץ��ȥҽԺ����������Ҫ������������˵�������С������ �Źⴺû��ȥҽԺ����ѹ����û�в���ҹ��û˯�����滰������Ϊ�Լ������˵��ġ��ϸɲ�һ��һ���ؽ�ţ�����ƽҲ�ٸ�ԭְ����������췴����˵�����ܲ�����в���������ߺ����ص�����������������ȹ��ϵ����ϣ���Ԥ�е������Ҫ���䵽����ͷ���ˡ� ������Ȼ��û����ã��������顱�˶���ʼ�ˡ���Ҫ�ǽҷ���������췴���еġ������������ӡ��Źⴺ��Ȼ�ܲ��ѣ���������������̨������̨���Ǵ�������㳡�������ظ���ίԱ����������̨�ӵĵط������д�����죬������Ҳ���˲����ˡ���ϲ�����ޣ�Сɽ�����ƣ��������ӡ������д�������������ֵģ��������Źⴺ����������֯�䶷���������������ᵽ���ǻ�����������е���ͽ�����ڳ���ս������̰���������͵ش������� �Źⴺ���������̡� ������̨�¿����������廨������������ϵ�һ����̨�Ϲ��ţ������ϻ�������ô��һ�����ӣ������صؿ��������� ��ϲ���������Ƶļ�������˵�������ƣ��¿ޣ����˿����˻�˵��û�л�����ޡ��� �����̲�ס�����������Ⱥ�����˳�ȥ����ϲ��������Ҳ���������˳�ȥ�������������벻ͨ��ȥѰ�̼������سDz�Զ�������������ƣ����Ʊ߿ޱ��ߣ�����һ·Ȱ�⡣ ����ϲ�壬�����զ���¶����ⴺ����ﶼ���п�����ҡ��������ʡ� �������ң�����˭����ʱ���㻹С�������¶�����ⴺ�����ʱ�����ǻ�ר��������ȥ��ӭ�������ظ��ϱ�����ô��һ���컨������ϲ���ֱȻ���˵�� ��˭֪��զ�����֣�˵�ⴺ���ڳ���ս���ϱ��͵ش�����������զ�ֻ�����������һ����Ϳ�ˣ�˭ҲŪ���塣�� ��Ҫ˵���ⶼ�������� ����ϲ�壬��˵�۴�զ�ͳ����˴�ɲ����ⴺ�嵱�˹�����ǣ������������з������ˣ����ڸոյ�������Ĵ�ɲ����ֱ�ץ�����ˡ��ٵ���Խ��Խ��ù����˵����զ���¶����� �����ޣ�������ү����һ���˵����ɲ��Ҹ�����˵������֪������˵�����š���˵�żҷصر��ۺμҷصغã�����ˮ���ż�Ҫ����١��ɺ�����ˮ���ƻ��ˣ������ٻ���Щ�����˹ٷ���Ҫ���¶�������ϲ˵�ú����ء� �������¶������������Ŷ�ϲ����զ���ƻ������� ���ǿ���������أ��żҷظպ����������ϣ����������ţ��ۺμҷ�������β�ϣ������ܸ����ż�ƨ�ɺ�ͷ�ܣ�û���żҺ�𡣵���������˵�ǿ�����ص���Ȼ�ã���������̫�أ������跨�����������������������������ض���������������ˣ������Ѱ����� ������취û�У��� �����ˡ����������������������⡣��ɽ�±���һ��ˮ�����������ﳣ����ˮ��������ˮ���Ƿصؾ��о��ˡ���������˵��ˮ������й����������ƽ�⣬ƽƽ�������� ����զû��ˮ������ ��û�ط���ˮ���� ��û�������취������ ���С���������˵��û�ط���ˮ���Ǿ�������������������Ȼ�������������ǵ����ȵ����������ر��Ƿ��ϣ�����ɽ�������ˣ���һɫ�İ������������ˣ��������ģ���ɽ����ס�ˡ���������ӣ����ӣ�Ұ����ⵡ���ɶ���С���Ŷࡣ���ǵ����Ȳ��ˣ��߽����֣��������Դ��ã����ֿ��������û�����һ�����Ż���һ����Ȼ�����������࣬���ë����մ���ˣ��������ģ��������㣬���������úܡ��� �������ó��� ��ϲ����˵�������˴��ģ���������ˣ���ɫ�������������ų���������ﵽ���ҷɣ�ߴߴ���������������䵽��֦�ϣ�һ�����ģ������Ͻ�Ĺ��ӡ����ɺ�������Ծ����̿���֣���Щ�����п��ˡ���ˮҲ�ͱ��ƻ��ˡ���ˮ���ˣ���ⴺ��Ҳ�ͽз�����練�����ˡ��� ��Ŷ����������������������������˵�����ϵ���ʱ�ⴺ����������������ˡ��� ��զ���ǡ��� ����˵����ʱ���������ij��˹ⴺ�廹����ȳ�ӡ��� ����ʱ�������Ǹɲ����� ���Ǻ���զ���ٰ������������� ��˭���֣�û�˹ܡ������Ÿ��˶�ȥ�ˡ��������ˣ�ǰ����һ�����꣬һ�����ˮ�����ӳ嵹�ˣ�����Ҳ�����˼�������ӣ����˹�ͷ������¶�����ˣ��������ˣ���ˮ���ˣ���˵�ܲ����¶����ⲻ����Ӧ������ⴺ�����ϡ��� �������գ�ֻ����ͷ�����Ͽ�զ��զֱ�죬���ﹾ�˹���ֱ���� ��ϲ������ֻ��˵����������ǰͷ�ߵú�Զ�ˡ� ����ϲ�壬���߿������� �����˼ӿ��˽Ų��� ����ϲ�壬���Ʋ��ǽ��������˵˵������˵��ϱ�������¿�զ�죿�� �������Ǹ���˵��������ⴺ��һ�춼�����ϣ���զ���õ���������û���ˡ��� �������Դ��˵˵��������ڸ�����˵һ������ �������ɣ�˭�����֡���ⴺ�嵱�ظɲ���ʱ�����˸�����ʱ��ⴺ��ֻ��æ������æ�췴���������ܡ��㲻֪�������Դ�������˵��һ�����ǹ�Ů��ҲԸ�⣬���Ƕ��ٵû���Ǯ�����Դ�����ⴺ��һ˵�������ⴺ��զ˵���� ���Ҳ²��š��� ����ⴺ��˵���Ǹɲ���ͥ����Ҫ���ۣ��ۿɲ���һ��Ǯ����Ҫ��Ǯ���ۿɲ�Ҫ�����ޣ������룬����һ��Ǯ���ĸ���Ů������˵���ƻ��е㺩����ڣ��������ܣ�����һ��Ǯ�����С����Դ������һ���ӻң���Ҳû�����¶��ˡ������������������Ƶ��Ѱ���ң�˵������ڸ������������ޡ����������ˣ�ûϱ�������ϲ��ÿ�������һֱ��û��������ڣ���ɶ�Ŷ����������ⴺ��ȥ�����ˣ�˭���������� ���ҿ����ƹֿ������� ��ֻ�������������������˵���� �����ƣ����ơ��������ں����������������û����һ�����������ø��졣����������Ūɶ���� ���ؼҿ���������ƴ��ſ�ǻ�� ���Ƶ�������֯������֯���������ƺ������۽�����ͣ�����е����ӣ��ʣ����������û�У��� �������ˡ������Ƶ�����������˳�������������� ��զ����������������������Ƶ�������Ӳ�ס�����ᣬ��Ϊ�����ܵ���ί���� ��û�С������Ƴ�����˵�� �������ɶ���� �����������Ʋ�ͣ�س����� �����ɶʱ��������� �����۵�һ���������������������Ժ����ʳ�ļ���̧��ͷ��פ���������С�ݡ����ƿ�֮�϶�������˵�����ҵ�--��--��--��--��--�ˡ��� �������Ķ�ȥ�ˣ��������������һ������æ�ʡ� �����࣡������ҧ����ʹ������ǽ��������һȭ�����ǽ���ϵ����������������䡣 �������������������˵�����������������������ը�ף�����һ�ᵹ����֯�����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