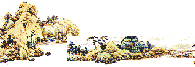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ɽ��������ѧ��Сɽ�����˸�С���Ź�Դ���������յ���������ѧ֪ͨ�飬����СС�Ļ����������˲�С�ĺ䶯����ɽ�ǻ�������ʷ������һ����ѧ����Ҫ�ھ�����������ˡ���ɽСɽ���ܸ��ˡ��������������ˣ���Ҳ�ӵ��˸�С��ѧ֪ͨ�顣����Ц������˵����ɽ�磬�ߣ��۸�Сɽ������ׯ��˵�飨����ɽ���˸����ֵ�һ����Ҫ��ʽ������˵��ڶ�Ҫ˵��Ѧ�ʹ�����������ɽ˵���С��ߣ�Сɽ�����������˸߸����˵���˵��ȥ�ˡ� �Ź�Դ�����ӻ�������Ժ���ǿ������Сʯ�����£���ҡ���������ų��Ƶ������Ͳ�֪ƣ����������˷�����ȥ�����ӡ��Ź�Դȡ�����̴�����ર�વ����ţ��ڳ��ƵĿ�����ע����һ�ɴ̱ǵ�������Ҷȼ�պ�ɢ������Ǻ�˵�ζ���� �����������в��У��������ˡ�������˵�� ����֪���ɷ���������Ҫ�϶��ˣ�Ϊ���ܹ��������죬�ڽ��е�һ��������Ҷ�в���һ������ĺ���Ҷ��ζ��ȷʵ���ţ�Ѭ�û���ֱ���ԡ����͵Ļ����Ź�Դ�����û����������Ь���ϰ���ȥ�̻ң������ְ�����һ��������֪���ɷ������£�û���������Ź�ԴֻҪ�����¾������̡���һ�궬�죬����������ͷ���ţ����͵���ˣ��Ź�Դ�������˺ó�ʱ������̡�������Ҷ�����ˣ���������Ҷ������Ҷû���ˣ������������������������������Dz�ͣ�������������Ĵ�Ѱţ�����ϲ�ס��������������ȰҲȰ��ס���Ƕ�ʱ�䣬��Ƣ��Ҳ�����ϴ���û������������ͷ���ȫ���˶���Щ���¡�һ�����ϣ���ɽ���������ſں�����һֻ��칫��վ������ǰ�����ų����IJ��ӣ��ڶ��Ƶ��۾������ض��Ŵ�ɽ��ͣ������ͣ��ȴ��Ŵ�ɽ�����³��ĺ���Ƥ��һ�������������ˣ���ɽʲô����Ҳû�³�����칫��վ���ˣ�ʱ���������ȣ�ʱ���������ȣ������Ȳ�ͣ�ؽ����ţ����ĵصȴ����ܹ��Ե���ɽ�����³����Ķ�������ɽ����û���¡��������ͷ��ˣ������ˣ�����Ѱ������ʳ��ʱ����ǡ����ʱ����ɽ�Ŀ��Ӵ��������һ���������������ʮ�������˫��һ�������һը������һ�죬С�����Ѿ��ĵ��˴�ɽ�������ɽ�費������δ��վ������������أ�����һ�����������ˣ���ɽ���·���������ϡ������ɽ�㶵����Ź��������ڵ���Ѱ��ʯͷ���Ź�Դ�Ѿ����˹�����ɶ��Ҳû˵�����Ŵ�ɽ����ž�ؾ���һ���ƣ���������DZ�����Ͷ���ģ��Է����붼�����ȣ��������ɶ��Ϣ�����ͼ�æ����������Ѵ�ɽ�����ˡ�Ҫ���������Ź�Դ�Ǿ��Բ�����ɽ�ģ���ɽ�����ij��ӣ����Ƿdz����ߵġ�����ʰ��һ��ʯͷȥ����ֻ�����Ĺ����������Ź�Դ����˵����ͷ���ţ�Ǻδ����������ϻƼ�͵ȥɱ�ˣ��������������ϻƼ�ɱ����ͷţ���������ϻƼ����ѷų��磬��ɱ��ţ�Ǵ���ɽ�����ġ��Ź�Դץ����֤�ݣ�Խ��������ת�������˺δ������Ź�Դ�϶����Ĵ��ţ��͵��δ����йأ���Ϊ������ţ��֮ǰ�δ�������������ţ����������δ����������Ժ��IJ��ͣ��������˸����û�а�ţ����δ������δ����Ļ�������͵�����Ĵ��ţ���������ϻƼҡ� ��ȥ���������ֵļ��ڵ��ˡ��Ҽһ�����æ�������ף���֥�飬�Ժ��������������δ����������������������ϻư�����Ķ�õ���ȫ���ֳ������ϡ��δ����ܻ���Ū�������������һ�Ѻ��֣��������������ս�ů�ͣ�������������������Ͳ���Ƶij��÷�졣һ����������һ�������������Ƶİ���ͷ���Ҹ����ȿֺ��ʹ����������ǰ�ܡ�û��ã�������ð����һ���������С����ɫ��С�Ƕ䣬С�Ƕ����������ˣ�����ʱ�䣬�����↑���˽��ɫ�Ļ��䡣����л���ڹ�����������һ����ԲԲ�������Ƶ�С�����ë���ޣ������ˣ����ۣ���Բ������Ӥ��ʱ�����ϡ�С���Ͻ��������ˣ���ë������ȥ��գ�ۼ�����ȭͷ��ô���ˡ��δ���վ�ڹ���ߣ�һֻ�ֶ���ˮ�̴���һֻ�����Ż�������Ȼ�Եõ����š���������һƬ������Ȼ�Ĺ�������¶���˵����Ц�ݡ����룬�ٹ�����ô����ӿ����ˡ� �Ź�Դ���������ӳ����ˣ�·���δ����Ĺ������δ����ǵ������ɫ�����K����ζ��������ҧ�������ݣ�������һ����ĭ������������δ������к�������ߵúܿ졣�Ź�Դû�뵽���Ǻδ��������ߵ�·�ߣ�Ц���еظ������к��� ����Դ�磬�����컹Ҫ����ɽ���� ���õ���û��������ˡ��� ������������������̡��� �����ˣ��ֵܡ������죬�ø�·�����Ź�Դ������Ƭ���������ʵ�˵��������ϳ��ò��������ʻ�� ����Դ�磬��˵����Ͻ����ܽ���٣����δ������ӵ��⡣ �����ҿ���ֻҪ�첻������˵ҲҪ�Ἰǧ��� ���ϸ������������� ���ֵܣ������ˣ�����ʱ������ĺ��̡��� �Ź�Դ�ӿ��˽Ų�������ͨ����ɽ��С·��ȥ���δ��������Ź�Դ����Զȥ�ı�Ӱ�����룬�������������б��³Ա��£�û���³�����������������ֻ�ܵ������ӡ��δ�������һ���°ͣ����ˣ�����ţ���ˣ���ûȥ���ϻƼң�Ҳû�е������ˣ�ȴ��û��Ϣ�ص���ɽȥ�ˣ��ҿ���һ��������ʮ����һ�첻Ъ��Ҳ������һ��ţǮ�����δ���Ū�����Ź�Դ�ĺ�«�ﵽ������ʲôҩ����һֱ�����Ź�Դ��ֱ���Ź�Դ����Ӱ���ױ�Ⱥɽ��û���Żع�ͷ���� �Ź�Դ���˴���죬�������ׯ�������Ź�Դ�����������ѣ������������˼������⣬�������������ֵܡ��Ź�Դ��С����Сɽ���������ɵ���˵�������һ������ݡ��������緹���Ź�Դ�����������˵��ɩ�ӣ�������ʰһ�´�������Ъ���죬�����ȣ������������ٸ�·������������ʮ�壬��������������Ź�Դ��������ƣ�֪���Ź�Դ����ҹ·��ϰ�ߣ��ر������죬ֻҪ�����������������ǰ���˯��������ϸ�ҹ·����������Ÿ��Ź�Դ��ʰ�˴��̣��Ź�Դ��ͷ��˯��������������˯����ô�㣬˯����ô�����������������ò��öԺδ����Ĺ����֡��Ź�Դ�ո��Ժ��ţ�������һ���Σ����μ��δ����������ϻ���ҹ���˾�ʱ�������������ţ��δ����ţ�������Ѵ��ţǣ����Ժ�ӣ������ϻƸ��ڴ��ţ��ߣ�����ʹ������ţƨ�ɡ����ţ��ǣ���ϻƼҵ��������ò���סţ�ۣ�����˿��סţ�죬Ȼ��Ѵ��ţ���ڵ��ϣ���ס���㡣�ϻ��ó�һ�߶���λ����ź����ɱţ������ţ�IJ��Ӻݺݵش�ȥ�����ţ��ͷ��������һ����ڴ�ϸ����Ѫ�Ӳ��������˳��������Ź�Դ��Ȼ���ѣ������۾�������ɫ�Ѻڣ������´����������Ѱ���Ҷ�����ױ��ɶ˵����ϡ� �����������ˣ���һ���������տ����Ļ���ϡ��Ź�Դ������ɫ�����ĴҴң���ҹè��һ��������С·����ɽԽ�룬�ܿ��վ���˺δ����Ĺ���ߡ� ҹ��һƬ�ž������һƬ�ž���Ⱥɽ�����ش����ţ����ħ����Ӱ���﹡��ϡ�����ľ������վ���ţ���һ�����ڱ������������ط����������ϣ���һ�������ߵ����ߣ���ׯ��ķ��ݾ����ذ����������һ���ճǡ����Ź�Դ������վ�ڹ���ߣ����������ž����Ĺ�����������Ŵ�ׯ��ģ���ķ��ݣ��Ӷ��������ɱ����ϣ��������˺δ����ҵķ��ӡ��Ǹ�����û���ˡ��Ź�Դ�������������ץ׳�����¡�����˵������һ�������������Ǯ�������Ź�Դ�����ֵܣ�������ò���Ǯ��������Ϊ�����δ��������ֵܣ������Ĺ涨���ó����������δ���������Ǯ������һ��������һ���δ������������϶������죬ͻȻ�Ѻδ��������ֻ������Ź�Դ���Ź�Դ���ֵܶ���ץ���ˣ�����������ץ����׳��˩��һ����һ���Ǻ�«����ǰ�߿������죬�����˵��������ʹ��ˣ�Ҫ�������������ڻң�����զ�죿���Ǹ��ڻ��Ž������ܡ������ˣ��类���������ˡ��Ź�Դ���������˵���δ���δ���Ķ������Ź���ץ׳�����ݺ���˯��һҹ���ݺ��ӾͰѺδ��������ָij����Ź�Դ���Ӵˣ��Ź�Դ��δ����ҽ�����ԩ��ֱ�����ڣ��Ź�Դ���������һֱû��������ʱ���Ź�Դ����������û�뵽�δ�����ʮ��������������Ĺ�����˵�����Ͱ͵Ķӳ�˯��һҹ���δ����ҵijɷ��ɸ�ũ�ij�������ũ���Ź�Դû����ץ׳������������������һ������������������������ͷ���ˣ�������Ĺ�����˵�����Ͱ͵Ķӳ������ˣ��δ��������ñ�������һ����˵����ʴ��£�ɲ�������һ������Ҳ�����ˡ���һ������������δ����������������ˣ�û��Ҫ��ֱ����ʮ����ż�����һ������ϱ���Ķ����ӡ��Ź�Դ��δ������ҵ�ԩԽ��Խ��Ź�Դ��δ���Ҳ�ͳ�����ԩ�һ��ͷ�� �Ź�Դ���������߽�������������һ˫�����Ĵ��������������͵Ĺ������Ź�Դ��������˲�䣬��Ȼ�����������һ��ϸ����������--��--���������Ƶġ�����֪���������Ժδ����Ժη���������ſ�ڵ��ϣ��������ŵ��档�����������ˣ����ǹ�������ʱ���������˵����졣�������������ĺ���������������ȴ�������İ������ѵ������������������ģ���Խ��Խ��Ӥ���Ŀ�����������������ҵģ�����ʹ�˲���һ��˺���Ѹε������ܵı�ʹ���Ź�Դ�������ˣ���Ҳ���ˣ������������ڵ������ڲ�ɱ��С���������Ź�Դ�ջ����Ѿ��������������֣�վֱ�����ӡ�����ԥ�Ų�֪��������ô�졣�Ź�Դ̧��ͷ��ң�����졣��ɫտ��տ���ģ�������Բ������ϡ�衣�����������ӣ������˸�������ңң��˼��ţ����֯Ů��ţ��ţ�ɣ��ҵ�ţ�ɣ��������ﰡ����������Ź�Դ���뵽�����DZ����׳�Ĵ��ţ���������ݲ�������һ���죬��������������ֻ���ַ��س����˵��ϻ���ʹ�����ŵĹ�����һ���������á���һ���������С����Ź�Դ�����е�Թ���еĺ�ȫ�����������ϣ���һͷ��ŭ��ʨ�ӷ���˻ҧ�����������ɱ����Щ���۵Ĺ��������������صĹ����Ե������Ĵ��ţ���������ع������Ǻδ�����ħ�ơ�һ�ÿù���������ʪ��������аγ�������˶���������ڵ��Ϸ����ţ������ţ�����ɫ�Ķ�Ƥ������������������ �Ź�Դ����������ڹ���ߣ���һ�����ҵ���ɱ��ƣ���غ������Ŵ�������������Ƭ�����ε��Ĺ������ƺ����ˣ���Ҳ���ˣ�����һ�ֱ���ѩ��˵�����Ŀ�У�����֪Ϊʲô�־����Լ�����Ϊ��Щ���ơ��Ź�Դ�������ٿ���Ƭ������������Ĺ�����������������ͨ����ɽ��С·�� ����֮���Ź�Դ�ص��˴����˵�δ������ˣ����������ڴ�������һȦ�����ﲻ�������غ����ˡ����������á��� �Ź�Դ�������������̣������̴���������̾��һ������������˵�����㿴��ѧ�����Ķ�Ū���� ��������ֻ����ȥ���ˡ��� ������Ҳ�������� ����������ȥ��㡣�� �����Ķ��裿���Ź�Դ��̾�˿��������ҿ����ѡ��� ������Ҳ�ý�������ѧ���� ������֪�������۹�����ѽ���� ��������������Ҳ̾�˿����� ���ҿ��������д�ɽ�����ţ�Сɽͣѧ����һ�����ϡ��㿴�в��С��� ��������һ��˵���������У�����Сɽ�����������ͺ�Ϊ�ѡ��������꼶�����Ӷ�ͣ��һ��ѧ��Ҳ�������ù��������ֿ����ˣ��ٽ���ͣ�����¡���������û������˵�� ��������ͣһ�أ���Ǯ����ȥ�����Ź�Դ�����˾����� Ҫ��ѧ�ˣ�Сɽ�ر��˷ܡ��������������������룬��Ȼ�������ĺ�������Сɽ����������� Сɽ�߳�����������������£��������ź��̴�����ס�������������ʣ����������� ������������˵���������� Сɽ�ܸ��˵��ߵ�����ǰ��������غ������������� ��Сɽ�������ն������������ Сɽ����һ��С�ն����ڵ��Ķ��棬����ֱ��С�ģ������ٿ�������ô��������ô�Ͱ�������֪��Ҫ����˵ɶ���Ź�Դ��ͣ�������̣��̻�һ��һ�����������ⲻʱ�������������֡������̻������˲�䣬Сɽ�����˵����۽���������������顣 ��������Сɽ����ؽе����������ж���Щ�����������ö��ӵ������ȥ�����ϵij��ƺ���ۡ� ��Сɽ����������ѧ���£������˺ܾã��⼸���һֱ˯���ţ������ŶԲ������ǡ��� Сɽ����һ����š� �Ź�Դ��Ĭ��һ����������̾��һ���������������ֵ�û���£����������ǡ��� Сɽ������������������������仰����ʱ����������������һ�������� ���Ҹ�����������һ�£���������ȥһ�������Ź�Դ˵�ú������϶������ġ� Сɽ����ʮ�����ܣ�����Խ��Խ���ţ�Խ��Խ���£��������������٣����Ľ�ָͷʹ���ؿ���Ь���ϡ� ���Ƚ����ȥ�������ϴ�����ѧ�����ס��� Сɽ�����̲�ס�ˣ�������Ȫˮһ��ӿ�����ۿ��� ����ȥ��κ��ʦ˵һ�£�����ͣһ�꣬������ȥ���� �Ź�Դ�Ļ���û˵�꣬Сɽ������ֹ��ס��˳���������̵�����������Сɽ��������������������ҹ����ȥ�� ��Сɽ��Сɽ�����Ź�Դ�����غ��ţ��漴�ܳ����ţ���Сɽ����ʧ��ãã��ҹɫ֮�С� Сɽ�ܵ���������أ������﹡�����ĵ��������ᣬ����Ľ������ϵشӴ��ﴫ�����ڿտ��ž���ҹ���л��졣Сɽ����е����ҵ������������ܵ�ɹ���϶���˻�δ��������ն��С� ��Сɽ--��Сɽ--�����ĺ����ִ����ˣ���������Խ��Խ����������ɹ�����ϡ����Ŵ����˽Ų����� ���Ҹ���˵�ˣ������Ѷ�Ҫ��������ѧ�����㡭�����º��ˣ�����Ҫ��ɶ�£���Ҳ�����ˡ���Сɽ��������ij��������������ᣬ������������������� ����˵�����ɣ�ѧ�����Ķ�Ū�������������� ��Ҫ���������ϣ�Ҫ�������������ϡ�����˵�� ����ɽ���ϴ��Ժ�����ÿ����š��� �������Сɽ�����һ������� �Ź�Դ�������һ����һ������������� ����������ˡ�����ɽ˵����Сɽ���ȥ�������� ��ɽ�ᵽ�����������֣����͵���һ�½������������쵽�Ƕ�ȥѰ����ڶ�Ҫ��Ѱ���ţ��Ҳ�����㵽�ף������ʹߴ��Ź�Դ�� ��Сɽ��Сɽ--�� �ž���ҹ�����������˽����ĺ������������ɴ��С����СɽԽ��ԽԶ�ˡ� �Ź�Դ�����ͺʹ�ɽ��Զ�ˡ�Сɽ��Ȼ����������������̶�Ĵ�˵ӿ���������Լʣ��������Դ�ų���ӳ�έ���£�����ë���Ȼ�����������˼�Ƥ����Сɽ����ն����������պö��Ų�Զ����Ƭģ���ķصأ���һ�����ضѾ���һ����ħӰ���ŵ�Сɽ��æŤ��������Сɽ�����ˣ������Ҽ������������ȥ�ˣ����������ܻؼ����û���ҵ����ʵIJ���֮�أ�����Ժ��վ�˺ܾã�����ʱ�������������������������϶������Ŀ�������Сɽ���뺰һ�������������ᣬ������δ�������������Ȼ�ڸ���ʩ��ѹ������һ����ı�����ġ���������һ�䣬���Ϳ���Ը�Գ�����ѧ�ˡ����������Dz������������������ʩ��ѹ����Сɽ�����˴��ſڵĺ����ѡ�������˽��������ڣ��տյ����������Žѱ�����Ѷ������ڳ�ʪ�ĵ��ϣ�����ʪ����������������ʮ�����ܡ���֪���˶�ã�Сɽ˯���ˡ�̫�������������ˬ�����ͷ��ޱ����������ϲϲ������ѧУ��ȥ��κ��ʦ�������������ң�ָ�ŵ�һ���м���������˵��������������λ�����������������Ӳ��øɸɾ��������ʡ����Ͽ������ˣ�һȺİ����ͬѧӿ���˽��ҡ���Сɽ���ڸ��ˣ���Ȼ��������֪�ղ�����һ�Ρ�����Ϊ�����ˣ����������۾�����ǰ�������һƬ��Сɽ̧ͷ˳�Ž�Ͳ���Ͽ���ֻ����ɸ�Ӵ����գ��������˲�ס��˸�����ǡ������ڹ�ģ�����������ж�ã�һ���߿������ļ��仮����������ҹ�գ����Ź��Ϲ����Ĺ�����չ����һ�����ҵĸ�ӽ���������--���--��������˷������������������֮�����������������Ƶģ�ͻȻһ��ֹͣ����������ׯ������������һ��ļž���Сɽ֪������ͷ�鼦�У�����������ŵ�����Сɽ���·���������ʪ�ˣ�����������һ�����������������Ҳ˯�����ˡ��Ͱ��ĽѶ�����С�ĵ��̣����ƵĿ��������һ�ţ�����Ȼ�����Լ�������������С���������滹����һ����ĺڲ�����������ˣ�����Ҳ���ڽѶ������ȥ�ˣ���������Ҥ��������������Ժ�ᄇ���ĵģ�û���κ����������ವ����ɨ������ʪ���·���ʹ���е�����������ǰ�ĺ��⡣Сɽ���˸������������ˣ��ֵ�����ȥ�أ�����Ը�����繲ס�Ǽ䷿�ݣ����߽��������С�����������ġ�ú����ú�֣�ú�أ�ˮͰ��ˮ�ף�����ư�衭���������������Ψһ��һ��յ�ֻ��ƨ����ô������̨ǰ�ջ�ĵط���Сɽ�����������С�Ŀյ��ϣ���С�����������ž���һֻ��Ϻ�ס���Ⱥ���������Щ��Сɽû�п������Ķ��������Σ���˫�ֽ�������ͷ����˫�������ú�궴�ú���Ⱥ����ģ�����֪������˯���ˡ��컹û�д�����һҹû��˯�õĻ��;���������˴������������Ϲ����ٵ�����ȥѰ�����Ķ��ӡ������ƿ���ţ���Ȼ�������ڵ��ϵĶ��ӣ���������������һ��������ʹ���������������ָ����Ŷ��ӵĶ�ͷ������������ߵ���������������Сɽ�����ϡ�Сɽ����ɭɭ�Ķ��������ˣ�����˫�ۣ���������Լ����߰�Ȼ���ᣬһ�����ӿ����ͷ��ֹ��ֹ��Ȼ���¡� ��Сɽ���㿴�㺩�������������͵ĺ���������ס��˵����ȥ������һ�����������Сɽ�ĸ첲˵��������������ȥ˯���������ˡ��� Сɽ�ӵ������������˽��˻��͵Ļ�� Сɽ�Ŀ�����ʹ�Ź�Դ������СС���ò����Ź�Դ˵��Сɽ����ȥ��ѧУ˵˵�����ܲ������ѧ�ѣ�Ҫ����һ�룬�۾�ȥ�������⣬����ͣһѧ�ڣ�����Ǯ��ȥ��Сɽ���ˣ�������Ȼ������Щ������֪����ֻ��������Ը�����ѡ��ܲ�����ѧ����������Ȼû�ס������õ���Щ����ƽ����������������ӣ�Ϊʲô�Ͳ���һ��ͬ�ʣ���СɽҲ�ܶ��£���֪�������Ѵ����Դ�������յ�ѧУ��¼ȡ֪ͨ���������������꼴�����ٵ������ܲ������ơ�Ҳ���Ǵ������𣬵�����Ϊ������ѧ�ѱ�æ����һ�죬Сɽ����������˵��Ҳ�ǽ������߱��ˣ�СƬ�ĵر�û���ˣ���չ�ˡ�С���塱�˶����������⣬����������Ҳ����͵�����ѣ�Ҫ�����꣬����������ɽ������������ѧ�ѣ����������棬����֮�г����˱�Թ������˵��զ�ţ�����͵͵����һ����ɽ����Ȱ�����ۿɲ���ȥ������Ҳ����˵�ˣ�����Ϊ����ǰ���������ӣ�������˸�͵�����ѵ�ñ�ӣ���Ķӳ�Ҳ���˼�Ĩ�ˣ�������˵�⻰�������˼Ҷ��㡣��˵����˵����ʵ�������ͽ����Ƕ��ɡ���˵���۶��������ˣ���Ը���Ӳ���ѧ��Ҳ��ȥð���գ�ȥ�������������İ취�����ǵ����˸����͵͵�ذѼ������ֻ����������������ʳ�ã��ֵ��������Ѽҽ��˼������Ŵչ��˸���ѧ�ѡ� Сɽû�ϳ�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