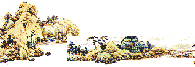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ͷ�������ϵ��ŵ��ǿ�ְ巢���˼��ٵ�����������֮�����Źⴺ������ߺ�ȡ���������Ҫ����Ա����ˡ��Źⴺ��ɤ����Щɳ�ƣ��������⼸��æ���۵ļ������ģ����ٲ�����Ա��ᣬ���Ĺ�����������������ȥ�����ԣ����¾���Ҫ����һ�����Ծ�����Ե���Ա��ɱֻ��������������˭���ҵ��ҡ��ŹⴺҪɱ����ֻ�������Ź�Դ���Ź�Դ�������ø磬�������ã����⼸���Ź�Դ�ϸ����ֱ�Ť����������ȥ������Ӱ���˴�������������Ҳ��������ǰ����������֧���أ������ѵ��ø綼�������ģ�������զ������˵��ѡ���Ź�Դ��Ҳ���Ա�һ�ܰ����ֵ�֮�ӡ� ��Ա���������Źⴺ�����Ƶ�������һ������Ȼ��ƵĴӼ��ﱼ�˳�������Ծ�������ǵ������ˣ����������ҡ���Ϊ��ģ���Ϊ���������ɣ�������ñ�ӡ����ڸ�Ӣ������������ͷ�����飬��������ЩСС�ϰ���û�ж���ϵ�����ǣ��ɻ���ᣬ��������ˣ����˸�ñ�ӣ��Ǿ�ʧȥ�����棬���Ƕ��˵����飬����˭Ҳ��Ը��ɡ��˻�һ����������һ��Ƥ��ׯ���˰����濴�ñ�ɶ����Ҫ����ɶ����� ɲ�Ǽ䣬ȫ�����Ա��Χ�����������£�ϯ�ض������ں���һƬ�� ��������Ť��㣬����ȥ�����Źⴺ��վ�����ߵĺδ���˵�� �δ���������Ť���ޣ�Ȼ��ҵ�����������֦��ϡ� �����ҹ���£����������Ʒ��Żƹ⣬��ãã�����к���Φ���ϵ��źŵơ��������ŵ������ϵĸְ壬�����ޱ�����������ҹ�գ�Ҳ������Ա��ãȻ�����ӡ���Ա����Ȼ�����úܽ�������˭Ҳ������˭���ϵı��顣��Ҷ���˵���������Ƕ��ͳ��˸�������Я���ĺ��̴�����ͣ���������ʵ���Ҷ���̴���������������������������һȺ��ż��ө��治ס�������Է������ʵ��źš�������Ҷɢ�������ʵ��������������գ��������ۣ��þò�ɢ�� �Źⴺ������ܷ��������Dz�ɢ������������һ��������ץ��ס�����ִ�ɢ������������������籨�ĸֲ������緢�͵����ţ��ռ�������أ�ͬ���������ţ���֪�Ƿ������Ի��Ƿ��ͷ۷ŵ�̫�٣��������¶Ȳ�������������û�б��˵����͵���ô�졣������������֣����˱��ղ���ʮ�֣������ղ���ʮ�֣���Ĵ�����ղ���ʮ���ˣ������ƨ��һ�����Ǹ��ڱ���ƨ�ɺ��棬��ƴ��Ҳ�첻���˼ҡ�����ֻ����һ¯����Ȼ�ϱ�����ʮ��֣����ڷ繵��������ʮ���ˡ���������ȥ����˵�ú��죬�����������Ҳ��Զ�ˣ�һ�����ϴ����ɣ������֧��Ҳ�ͳ������ӵ�β�͡����������ˣ�Ҫ̿��̿��Ҫ��������һ¯Ҳû���������������ϱ����ֶ�ʮ�֣���Ϊ�ϱ�������ֻ��һ���һ��࣬������һ���һ���٣����ˣ����Ǻ��ˣ�������ˡ�������Ӵ���뵽���쿳���ϵ��������������ߡ����������赲����ûɶ˵�ġ�����һ��֮�����������������ܶ��ӣ��쾭���壬���۹ܵö��벻�ԣ������йܵ�Ȩ���������ǵ������ܶ��ӣ�˵����ߣ��������������Ź�Դ�dzԱ��˳ŵģ����űⵣ�赲�δ������ǿ��������ǹ������Ӷ�������ˡ���Ҫ֪�����㵲�IJ��Ǻδ����������Źⴺ����֧�顣��Ѻδ�����ס�ˣ���֧��������Ķ��飿֧��Ļ������������Ź�Դ�Ļ������������ⲻ����Ц�����ŹⴺԽ��Խ���������ϵ���ͷʹ��һ�������Կԡ�������������ʼ���������Ľ����� ����Ա�ǣ������ұ���һ����Ϣ���ڷ繵�����ַ���һ�����ǣ�һ��������ʮ�֣�����˸���Ԫ˧�ĺ��졣�۹����������ȫ�ص�һ��Ҳ�����ȫ�صĺ��졣�����˵���������ĸ��峬���ڷ繵���������Ѻ�������ĸ��塣����Ϳ�һ��һ�����������ƶ��������ƶ����֣��ƶ���Ծ����˭Ҫ����ú��죬�͵ô�ɿ�ɼ��ɸɣ������ҹ����ת��������ǻ�˵�ˣ���������ϱ�����Ҳ��Ҫ��ô���壬�����ȱ�Ŀ�꣬�ȱ��ƻ���Ȼ��Ŀ�갴�ƻ�ȥ������Ծ����͵�������Ҫ���Ƴ��棬Ҫ�е���Ҫ���룬Ҫ�Ҹɡ�����˵���ж���ж������ҿ��⻰ǧ����ȷ��һ�㲻�١��õ������ϣ��������ж�����ж���������Ҫ�ú��������������������ǽ���������������������Ǿ�Ҫ���룬�����˲��ܸҸɣ��Ҹɲ��ܶ�ú��졣���죬���Ǿ�Ҫǧ���ټưѺڷ繵�ĺ����������������ǵĴ�ͷ���ú��������Ǵ���Ͽո߸�Ʈ���ԶƮ�һֱƮ���������塣���ԣ��ӽ�����ʼ�����ǾͰ����ҹ����ת���� �Źⴺ���鼤����Խ˵Խ�о��������ǣ��᳡��ȴ������һ�������������С�����ۡ� �����ǣ����ǽ����������û�и��ϣ��ر��ǿ����ӣ����Źⴺ��������������û�а��ƻ���������ⲻ����ȫ�����ǣ�����Ϊ�ҵ���Դ���Źⴺ����ʡ���ˡ��硯�֣������Ͻ��������������������֡��ر��ǹ�Դ�����ձⵣ���ٺδ������Ż������Ӷ�Ա����ɿ����ӹ���̱��������һ�����ص��ƻ���Ծ�����ƻ������������¼���������ϴ��������ԣ����Ǿ���������Ϊ�����ɣ����ϸ�ñ�ӡ���Դ����վ�������� �Ź�Դ�����Źⴺ����������������������һ��һ�����ϴܣ������ش���Ⱥ��վ�����ߵ������£��ݺݵض����Źⴺһ�ۡ� ����Ҫ��ͷ���Ҫ��ʵ������Ϊɶ�ƻ���Ծ����Ϊɶ�ƻ��������������Źⴺ����Ź�Դ�� �Ź�Դû�е�ͷ�����ǰ����Ĺ�ͷ�߸߰��ţ���б�һ��ֱ�� ��˭˵���ƻ���Ծ���ˣ��ƻ����������������� ���㻹���������� ���ҷ�ɶ����Ϊɶ�赲�������㲻�����ң���ȥ����������� ����Ա�ǣ��Ź�Դ����ʵ���������Ѹ�ñ���ȸ������ϣ� �δ������ᡱ�شܵ��Ź�Դ��ǰ��˫�ֶ���ԲԲ�ļ���ѩ���������ߵ�ֽñ����������ظ��Ź�Դ������ͷ�ϡ� ������С�������� �δ���˵��һ��¶�ܻ���ƨ����ȴ�����Ź�Դһ�š��δ���û�з����Ź�Դ������һ�ţ�����һ������ʺ���ǵ���Ա�Ǻ��ô�Ц�� ����ȥ�����Źⴺ�����ȵ��� �Ź�Դ����ؿ����Źⴺһ�ۣ���������ԭ�ء����������ԵĶ�ϲ����һ�����ļ�ͷ������ָͷ���ᵯ��һ����ͷ�ϵĸ�ñ�ӣ���ñ�ӷ�����һ�����ԡ��ش��죬��ϲ����һ�������������Ź�Դ�Ķ������ĵ�˵���������죬���Ż��������� �Ź�Դ�Զ�ϲЦЦ˵�������Dz������������Ҿ��㡣�� ��ϲ��æ���֡����Ҳ����Ҳ��롣�� ����ɶ���ֲ������������ԡ����Ź�Դ����ϲ������Ц�� �Źⴺ��˵���ˡ����ҵ���ʹ��ˣ���ڶ�û�����Ұ��ⶥ��ñ�Ӹ������ȥ�������������ڣ����ֵģ���̿�ģ����ϵĸ���λ�����������������ֳ���˭���������Ͱ����������͵����磡�� �δ�������վ����һ�ӣ��������ӵģ��ߣ��� �ž���ҹ���У������˳��صĸ�ͷ������ͷ��������������ҹ����������Σ����Ǿ�����������������������ȥ����ͷ���������������������������ҹ���õ÷��顣 �Ź�Դ�Ѹ�ñ�ӷ��ڼ�����������ӱ�����ɳȥ�ˡ�������ѿ�������Ϣ�����Ŵ�ү���ֺ����Ŵ�үһʱ�����dz��������Ŵ�ү��ô��һ�������ˣ�����������һһ�����ϲ���ҭ���ˣ����Ź�Դ�ͳ��˺����Ŵ�ү�����ˡ��������Ŵ�ү˯�ɣ���������ľ�ѳ��ۣ�����������췹���Ŵ�үҲֻ�����ˡ��Ź�Դ���Ŵ�ү�Ĵ�ǰվ��һ�������������������ˡ����Ź�Դʼ��û����ͨ���Źⴺ�ſڿ��ӣ����˵��˵�ٻ���һ�쵽������ţƤ��������Խ��Խ����Щ��Ӱ�Ӷ�û�е����飬�����һ��˵���컨��������ȷ�����¡���Ϊ��ֵ��ǣ������Ǽٻ�����ͷ��ƫƫ�š��Ź�Դ�����Źⴺ������Ϲ����ȥ�ˣ��ٴ���ȥ��Ҫ���µģ����������Źⴺһ�£�����Ϲ���ˣ�ţƤ����̫���ˣ���Ҫ��ը�ģ������ܺ��Ļ��Ǵ�ţƤ�߱��ˡ����ǣ��Ź�Դ���Źⴺ���ǻ���Ͷ����˵����һ����ˣ��Ź�ԴΪ����������Ҳ��û�����Źⴺ��ǰ�ἰ���¶�����ʱ�Ź�ԴҲ�����룬�Źⴺ�ǵ�Ա��֪���ö࣬�����ö࣬˵������ͷ�����������ߡ���������ɶ���ߣ���ͷ�ܲ����ۺ���ͷ�����ܸ���ͷ˵�ٻ������Ź�Դ���˰���Ҳû���������������������������ȷʵŪ������ �Ź�Դ̾��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