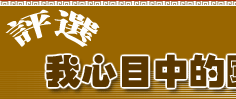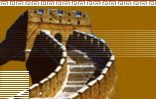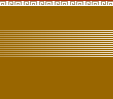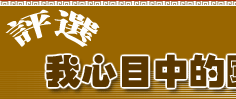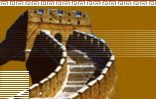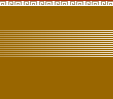����ѧ�о�������������һ��
�������ڹ�ѧ��20����20��30�����90����ͱ����ͳ����ֱ���ֹ��о��ȳ�����ֵ����������ͶԴ����������ͷ˵�������������ڹ�ѧ�Ĵ�Դ����ѧ�ں�����˵��
��������ѧ��ԭ���Ǻ�����ģ����ǹ���������ѧУ���ƶȡ���������Ϊ���֡��䡢�����顢�����ϳơ����ա������������ڲ�����ʦ��������ʦ�ƹ�ѧ֮�����Խ̹���С�衣������ǡ�ѧ�ǡ�������֮���ߣ������ӣ������ԣ���������ѧ����������̫ѧ�������ƹ���ѧ������ƹ����£�����ƹ��Ӽ࣬����ʱ���Թ��Ӽ��ܹܹ��ӡ�̫ѧ�����ŵ�ѧ��Ԫ�������ѧ��Ҳ�й��Ӽ࣬����������������Ӽ࣬���������ʮһ�꣨��Ԫ1905�꣩��ʼ��ѧ�������Ӽ����ֹ��
�����������峯ĩ�꣬����ѧ���������ת��Ϊ�����壺��ѧ��ָ�������е�ѧ���Ļ��������ڲ�ͬ�˵�ʹ���У���ȴ�����Ź���ѧ������ѧ�����ҹ����Ļ�ѧ���������塣�α��ɣ�������ν����ѧ��������С˵�±�����20����1�ţ�1929��1�£��������������ϱࡶ��ѧ��١�����ƽ������꣬1933�꣩���ǽ����������ѧ��һ��Դ������ġ�
�������ҹ�ѧ����Ŀ�֤����ѧ��һ��������������ʹ������ǣ�
����1902�����죬���������ձ�ı�����졶��ѧ��������д���������������ϣ�������������������˺������¡�������д���������걯������������ѧС��֮������ѧ�����ѧ֮�Ӵ˶��������֮��Ҳ����ʹ��ѧ֮�����߹�����������֮Ӱ�죬��ʹ���ѧ������������Ҷ���Ҳ����������ʹ��ѧ֮�澫���ռ����������ת��֮���ߣ������ڹ�ѧ��Ȼ��������Ч����������������ѧŷ��֮ѧͯ��Ƚϣ�����Ч�����ӡ��������Լ������Թ�ѧΪ������ȰҲ�������������������й�ѧ��˼���Ǩ֮���ơ���������Ա�����22�ţ�1902��12��14�գ������������ġ���ѧ��������Ŀ���������е��о��й���ͳ�Ļ���������Ҫ���ˡ���ѧ�������������������õĹ�ѧһ�ʣ�����Ҫָ��Ӧ���ǡ����ҹ��е�ѧ���Ļ������������ʡ��������ܲ��ɵ�ʱ�Ͱ졶��ѧ�����������Գ�������˵����Ϊ�й�ѧ�����ȴ��Ż���������ѧ����ٹ��ѧʢ�У����й�����֮ѧ������Ƚϣ����ྺ��������ѧ֮�澫�������������������������ʱ������֮������ѧ������ȡ�����л�ܣ�����ͻ��У������Ҳ�����Ҳ������ת���ԡ����������׳��ࡷ���������Ŀǰ��֪��������ʹ�á���ѧ��һ����֮һ��
����1902�꣬���������ձ�д�ġ���ɣ���¼ǡ��У�ʹ�� ����ѧ�����Ҳ���ڡ��������е�ѧ���Ļ�����������ʹ�õġ�
������ʱ��һЩ�ԡ���ѧ��������ѧ������֯��Ҳ���ڡ��������е�ѧ���Ļ�����������ʹ�õĹ�ѧ�������ġ�����������ʮ�����仨�Ρ��ġ���ѧ�硱����1903��ͳ����ˡ������䡢��֪������ʦ�ࡢ��ѩ�ٵ������Ϻ���������ѧ�����硱������������1905���Ժ�
������������������ֵ���ʷ����������������ˣ�ѻƬս���Ժ���ѧ������ʹ�й���֪ʶ���Ӵӡ�ʦ�ij�����������ˡ���ѧΪ�壬��ѧΪ�á���������ѧ���Ƚ�����������ѧ������ҡ����Ϊ����ѧ�ʵĴ����ʡ���һ�仯��֪ʶ�缤�����Ļ�Σ���У����Ϊ������ѧ�Ķ���Ϊ������ѧ�ij����������͢ȡ��ŷ������ǿ����������ƶȡ������е�����������ѧ�������������������ת�������Ϊ�����������е�ѧ���Ļ����������Ź��ʡ����⡢��ѧ���������ݡ��峯ͳ�����У�����֮����Ҳ���ű�����⣬�����ڸ�ʡ����ѧ�ü���ѧԺ����������������ѧר��ѧ�õġ����Ա��룺����Ժ����¼��������ѧר���衷�������Ҽ�����һ����30-31ҳ��������Ҳ���Թ�ѧ��ֵĴ�������������������ѧ��ֱ�ĩ����������ʡ��ͼ��ݵ����꿯�����Ͼ���ѧͼ���1930�꣩
������ĩ���������ѧ�ߵ����ۣ��dz����ӹ�����ġ��������롰�����¡��ı�𣬲�����Ϊ������ѧ�������ѧ������ѧ��������̿����죻����ѧ�������ѧ����ѧ�����֮�����չ��ӡ��������������۹���������ŷ������������ѧ�����ڣ���ڣ��ڣ�
����Ϊ������ѧ�����������������ѧ���Ļ���˼������ʹ��һʱ�ڵ�����ѧ��ϰ��֯�����DZ����������̫���ڶ������ѧ��ϰ�ᡢ��ѧ�����磻������ѧ��ϰ�����ƣ�������ѧ�ߣ�δ�в������ѧ��������Ҳ����������ѧ��ϰ���������ڣ��ţ���̫����1906���ᳫ���Թ��⼤�����ԡ�������1908��ġ��������͡�һ���У����ǽ����⡢��ѧ������������Ϊ����ͬ��ʲ��õġ�
������̫�ĵ�����ԣ��ȷ��𱱾������ݹ�ѧ�
����л��������ƽ����ʦ�ࡢ�����ʵȴ����ijɶ���ѧ�ݣ��������ѧѧУ����ѧר��ѧУ����
���������δ���������ѧר�ݣ�
����1908�꣬�������١����ڻ����˴���ġ���ѧ�ͱࡷ��
����1911���ڱ�����1914�����ձ�������������ά����ġ���ѧ�Կ�����1911��2�£�����άΪ����ѧ�Կ�������������������������������ѧ�����б����ģ��ԡ�������Ҷ����˵��ʤ��������֮�䣬���й�֮����ѧ������ȫΪ��˵��ͳһ�ӡ���Ҳ��ʾ��������ͬʱ�������տ��¡���ɡ��屾����˼��ʱ����������ѧ������������Ի��ѧ���¾�Ҳ��������Ҳ����������ѧ�ʣ�������ѧ��ʷѧ����ѧ�����й�֮ѧ�����������֮������֮ѧ���ҹ��������֮�������߹������ܶ��������й�����ʵ��ѧ֮����������ѧ��ѧƫ��֮��������������ѧʢ���ʢ��˥���˥�������ȿ��������ƶ����Ҿӽ���֮����������֮ѧ��δ����ѧ���˶���ѧ�����ߣ���δ����ѧ���˶���ѧ�����ߡ������Ƕ���֮���ܲ����ߣ��治֪������ѧ�������ӡ���������ά��������ѧ�Կ����������ü��֡���������ά���ҹ��������ѧ��ѧ�Ʒ����ѧ�ʼҡ�
����1914���ڶ����������ɳ¶�������ѧ����˴���Ĺ�ѧ��Σ�缰����ѧ����־��
����1915�����Ϻ������˱����˴����Ĺ�ѧ�������롶��ѧ��־����
��������Ҧ����˴���ġ���ѧ��ѡ���ȡ�
������Щ��֯�Ľ��������Ա�����ѧһ���Ѿ�Ϊѧ������ͬ��ֻ�Ƕ����ں��������в���ȫ��ͬ��
����1919�� 3���ɱ�����ѧ�ĿƱ༭����ġ������¿�������ʦ����Ϊ�˿��������ʡ��й��������ÿ����Բ����й�����֮ѧ��Ϊ��ּ�����˺���ʦ��д����ѧ�������棬����ѧ��һ�ʳ�Ϊ���˶��й���ͳѧ����ͨ�ơ���ʵ˵������ѧ�ߺΣ�һ������֮ѧҲ����(��ʵ������ѧ��ϰ�ǡ���������ѧ������2���7�ţ�1906��8��9�գ�
������̫�����Ϻ����ڹ�ѧ�ļ�¼�壬�ɲܾ����������顣ϵͳ�����˴�ͳ��ѧ����ѧ������ѧ������ѧ�����䡢�Ը�ʱ��ѧ����չ���ص㡢����������������о�տ�����������ۡ�1922�����ġ���ѧ���ۡ���˵������ѧ���������ڽ�����������������ѧ������Ϊ����������ѧ�����dz��й����е�ѧ��Ϊ��ѧ�����ѧ����ѧ������ѧ��Ϊ���ࣺһΪ����Ϊѧ����Ϊ����֮ѧ����Ϊ����֮ѧ��������̫�ף�����ѧ���ۡ�1922�꣩����ѧ���ۡ�����Ϊ������ѧר��֮ʼ��
����1922��1�£��Ͼ����ϴ�ѧ��÷��ϡ���嵡�����ͮ�ȴ��졶ѧ�⡷��־��
����1923�� 1�£�������ѧ���ʵȴ��졶��ѧ��������־�������α�ί�����Ρ����ڡ��������ԡ���ָ������ݿ����������Ļ��˶����������ʡ�����Ҫ��ɲ��֡�
���������ܽ�ë��ˮ�����ӡ���˹�����1919�����ڡ��³�����־����˵�ġ����ʡ��롰��ѧ�������һ����ȷ�����������ѧ�������ǵ������ֻ�ǡ�����ѧ������д���й���һ�й�ȥ���Ļ���ʷ���������ǵġ����ʡ����о���һ�й�ȥ����ʷ�Ļ���ѧ�ʣ����ǡ�����ѧ����ʡ��Ϊ����ѧ���������ʡ�������ʣ���Ϊ������Ϊ����һ�����������ʣ�������������塣�����ʡ����������⡯�������ְ����������������������˽⡮����������ζ��á����⡯?����Ҫ�����ѧ����������������ǧ��Ĺ�ȥ�Ļ�������һ�е��Ż��ɼ�������ʷ���۹�����ͳһ�С��� 1924��1�º����ڶ��ϴ�ѧ��ѧ�о����ݽ�ʱǿ�����������ʡ��������֣�����̫������������ȴ�ǰ�õġ����⡯�ö��ˣ������壬���й���ȥ����ʷ���Ļ�ʷ������һ�С����������Ҫ��ѧ���ĽǶ���̸���������ʡ������ʵġ���˼�������塷��һ��ʼ�㽫ȫ�ĵ��Ĵ��Ҫ��ٳ����������о����⡢����ѧ�����������ʡ��������������������Ҫ�����������ƽ���ѧ�о�������һ������ʷ���۹��������ѧ�о��ķ�Χ���ڶ�����ϵͳ�����������չ�ѧ�о������ϡ��������ñȽϵ��о���������ѧ�IJ��ϵ���������͡�������˵������ѧ��ʹ����Ҫ��Ҷ����й��Ĺ�ȥ���Ļ�ʷ����ѧ�ķ�����Ҫ����ʷ���۹�������һ�й�ȥ�Ļ�����ʷ����ѧ��Ŀ����Ҫ�����й��Ļ�ʷ���������ʣ���<��ѧ����>�������ԡ�,�������Ĵ�������Ƕ�ͼ��ݣ�1924�꣬��һ��
��������˵�������������ι�ѧ������Ҫ���Ʊչع�����̬�ȣ�Ҫ��Ƚ��о������ġ���һ�������ϣ�����ѧ���о���ѧ�ķ�������Ӱ���ձ���ѧ�����ˣ������ǻ���ڤ����;��ʱ�ڡ����Ǵ�ʱ��Ӧ�����IJ������ǵĿ�ѧ�ķ�������������û������ϵͳ��ϰ�ߡ��ڶ��������ϣ�ŷ���ձ�ѧ�����������ijɼ����Թ����ǵIJο����Ƚϣ����Ը����ǿ������·��ţ����Ը���������������ľ��ӡ�ѧ���Ĵ����ǹ�ª���ţ���ª���ŵ�Ψһ��ҩ�Dz��ɲο��ȽϵIJ��ϡ���
����1918��ף���Ԫ���ڡ�������ѧ�¿��������ʡ���ָ�������о�Ҳ�ߣ���ͽ����ŷ���������ŷ��֮��Ϊ����֮��������ͽ������⣬�����Կ�ѧ�������ҹ���֮���ࡣ�� 1921��ף��ڱ���ѧ�����ϣ���˵��������һ����ע���������������룬һ����ҲӦ��ע�⽫�ҹ����������������1922�꣬�ڱ������25���������ϣ���Ԫ���ܽᱱ����ּ����˵�����γ�һ���棬Ҳ��ı��ͨ���������������Ŀ�ѧ����Ȼ�����������飻�й��IJ��ϣ������й����е�ѧ�ʣ�ҲҪ�ÿ�ѧ�ķ���������������
������ʱ��ŷ��ѧ�о����й���Ӱ�첢������������19�����𣬵¡�����Ӣ�������ȹ��������˺�ѧ�о����������Ƕ���Ӣ���¹���������䡢�����������п��ŷ����ֶػ����顢�����빵ȴ��������������ַ���й�ѧ��ȫ����ѧ���Ŀ��������й������Ļ��Ĺ��ʼ�ֵ�����й��ڱ���Ťת��ѧ�о���������
������ѧ����`������˵��������Ĺ���ѧ�ã�ѧ�����꣬ѧϰ��ĿΪ����ѧ������ѧ������ѧ������ѧ����ѧ���ڽ�ѧ������ѧ��ʵҵѧ�����ѧ��ʷѧ������ѧ������ѧ������ѧ������ѧ������ѧ������ѧ�����֡�ͼ�����鷨�����롢���µȡ���������ѧ������3���1�ڣ���
��������һЩѧУ�ܴ�Ӱ�죬Ҳ���衰��ѧ���ۡ��Ŀγ̣�Ǯ�µġ���ѧ���ۡ���������1926����1928��������������ʡ������ʦ��ѧУ�������ݣ�����ʡ��������ѧ���ġ���ѧ���ۡ��γ̽����������ɡ�Ǯ����Ϊ����ѧ�������硣����ѧ��һ����ǰ���У�������ֲ�������Ϊһʱ�������ʡ��䷶Χ����������Ӧ�й�ѧ���������ʵ���б𡣡���Ǯ�£�����ѧ���ۡ����ԡ���1926�꣩Ǯ��ָ������һ�����κ�һ��֮�����������Գ�Ϊ֪ʶ��ˮƽ������֮�����䱾��֮��ʷӦ������֪��������ν�Ա���������ʷ������֪�ߣ��ȱ��渽һ�ֶ��䱾��������ʷ֮�����뾴�⣻������ν���䱾��������ʷ��һ�������뾴���ߣ����ٲ�����䱾��������ʷ��һ��ƫ�����������壻�ġ�����ÿһ���ұش������߱������������������࣬����������з�չ֮ϣ������
����20���͵�20��30������ǹ�ѧ�о��Ķ�ʢ�ڡ����ʵ����ᳫ�ġ��������ʡ���ʹ��ѧ�о���Ϊʱ�У�����Ϊ���������о��������������������ѧӻԾͶ����������㷺��ע����־�ʹ���׳��桢�����Ͽ��ٹ�ѧר���ȵȣ�����������ѧ�о���˵��������֮�⣬��չ����������������������ۡ�
������ 1922�걱����ѧ�����Ŀ��о�����ѧ��֮���廪�����š��ྩ����³�Ͷ��ϴ�ѧ��У����齨��ѧ�о������ѧԺ�����ʡ����������������ġ��й�����³�������ԺУ������ѧϵ���ѧר�ơ�
����1928���ٿ���ȫ�����������ϣ����������������ںϲ������л������Ļ�������Ҫ����ں������Ļ����֣����̹��͡������취�е�������һ�Ǵ�ѧԺ������ѧ�о��������������ʣ�һ��ȫ������ѧ�����ѧר�ƣ��л������ѧԺ�ࣺ��ȫ���������鱨�桷����182-184ҳ��
������˹��˵���������ʱ������ǹ��⣬����˵������һ���������ν��ѧԺҲ������һ�������Ĵ��ѧ�á�������˹��:��ë��ˮ<���ʺͿ�ѧ�ľ���>��ʶ��,���³�����1��5�ţ�1919��5��1�գ���������˹����1940��ʱ˵:������ѧ'һ�ʣ������ҽͬ�䲻ͨ���弾����ν���ѧ�ã����Dž�������֮�������������ӡ��Ժ���̫��̸���ʣ���ʤ��ǰ�ӡ�Ȼ����һ�ʣ���Ϊϰ�ã�������֮�ƹ�Ҳ����̫��������壬����νҲ����ĩ��������Թ�ѧ����Ϊ���ף����ù��ʣ��Թ�ѧר��֮�������ͣ������ʸ�ͨ�У�Ȼ�˹��ߣ�˽��֮�Ŵ�Ҳ������ ��˹��������� (1940��7��8��)����̨������Ժʷ��������������ʼ����Ϊ��ѧ���ǹ��ʡ�
�����¶�����Ϊ������ѧ��ʲô������ʵ�ڲ�̫���ס�������ν��ѧ��ң�����֮��������ѧʷ����̫����������ʷ����������ѧ�������������ǽ�ʯ����ѧ����������������ѧ������Щѧ���⣬����ʵ�ڲ�����ʲô�ǹ�ѧ���� ����ѧ����һ���ʣ�����������һ����Ҳδ���ܵõ���ȷ�Ĺ����Ϊ����ѧ�����Ǻ����Ϳ����һ�����ʡ��� ����������ѧ����1923��7��1�գ����¶�������ѡ����2����516��517ҳ��
����֣������Ϊ������������ѧ�������Ǻ���ͳ�����ǣ�����ѧ�˶����Ƹ����˲������⡣��һ��Ȱ���о��ż����˶���?����Ȱ���о�һ���й���-----���۹Ž��³£�ֻҪ���й���----�Ļ���˼�롢ѧ������ѧ��ʷ�����������Ρ����ã������й��Ĺ����ԡ����ط��ķ���ϰ�ߵ�һ���˶���?ǰ�߶��ò���Ȱ�������۹��������ˡ�����֣����:��������ѧ��(��)��,�������ܱ���35�ţ�1924��1��6�ա���������Ҳ��Ϊ�������롮��ѧ��������֣�ʵ��̫���죬��������ʵ�ʵ�Ӧ�á��������ִ������ѧ����ֵ��1926��4��11�գ�
����������廪��ѧ�о�Ժ��Ҫ����ߺͿ���ǰ�ڵ������ߣ� ����ȷ����������У�о�Ժ���й�ʵ�����٣���У�籱����ѧ�����ѧ�о�����Ȼ��֯�취���в�ͬ�������ϸ�����ָ�����廪�Ĺ�ѧ��ȡ����ŷ��ѧ���о��������Լ��й��Ļ�֮�ɼ������ֱ�У�о�Ժ֮���ڹ���֮�о���ѧ�ߡ�������嵣����廪�����о�Ժּ֮Ȥ�������������廪��ѧʷ��ѡ�ࡷ��1����374-375ҳ��������Ҫ��������ѧ���۵����о��������й��ľ��������¡�
�����ɷ�����Ϊ���¹�ѧ�˶����ˣ������ࣺ��1��ѧ�����˶���ѧ���ޣ��˲��ò��ݹ�ѧΪ�³��ߣ�2��������ѧ������ѧ����������˳˻������ߣ�3��ä���ɣ�����һ���˶�������֮����������������Բ�ͬ��Ȼ�����Ǵ�Ϯ���˵ķǿ�ѧ�ľɷ���˼������ҫһʱ��ȴ��һ���ġ�Ҫ��ȡ��ѧ�ķ���Ϊ���е��о������Ƕ�ȱ�ٿ�ѧ�����������ǵķ�����̬�ȣ������dz�Ϯ��ʱ�Ŀ��ݼҡ�����������Ȼ�����о�����������������һЩ��ǰ������Ŀ��ݡ������ɷ������ѧ�˶����Ҽ���,�������ܱ�����28�ţ�1923��11��18�գ��ɷ�����˴������������
�����ܾ�����Ϊ������ѧ֮�о�����ɺ�������ϣ�����ѧ���֣���Ϊ���������֮��������������ѧ֮��������������֮�淶��������ѧ����֪���о�֮����Ϊ���ģ�����ѧ����֪���о�֮����Ϊ���ʡ�������ѧ����֮�����Ǿ�����֮���ǣ���������ǰ��Ϊ¡Ȼ֮�Ų�������֮Ի'��ѧ'����(�������ʱ������֮Ի���⣬������) ����������һ�����ӣ�ʵ֮���Ҳ������������������������ʹ������������ᡱ���ܾ�����������ѧ�����١�����ѧ��������Ī���ѧ֮ʵ�ʣ������Թ�ѧ����ߡ���֮��������ѧ��Ϊ����ѧ֮�����ˡ���ѧһ�ղ�ȥ������ѧһ�ղ�������������������'һ�¶��ۡ������б�����ѧ֮��ѧ�о���������֮��ѧר�ݺ��Ϻ�ͬ����֮��ѧר�ݣ����߽ԡ���'��ѧ'Ϊ�ġ���Ω���ߡ���ͬ��һ�ġ�����ʵ���ز��ܲ��������ʡ���ѧ֮Ϊ�����Ϊһ��ʵ��Ϊ������������ǡ�������֮��ѧ�����������ǡ���������֮��ѧ�������Ϻ������ǡ��������֮��ѧ�������ߡ�������֮��ء������ܾ���:������ѧ֮�������ֵ���������׳�����֮����ѧ��1925��12��)
������ʵ������Խ��ܡ���ѧ����һ���ʡ������ۡ���ѧ�����ʡ���˵������ѧ����һ�������γɵ�ѧ�ʣ���ѧ�������Ա��ڲ�����ѧ�ʵ�һ�����ʡ��������ġ���ѧ����ʵ�ʾ�����������˵�ġ���ѧ������ʵ��Ҳ��Ϊ����ѧ������������Dz��ֹ���ġ������й���δ��������ǰ�����о���γ�ص�ʥ���ʹ������������а˵��ˣ������Щ��������������������Ȼ�����������ص�Ӱ��Ҳ�ƺ����ڿ������£�Ȼ����������Ʋ���Ž������ѧ�ʵ��Ƿ��ƶ�����ⲻ�ۣ�Ϊ��������������ѱ���������ѧ�ʽ�����ѧ����ȴû��ʲô�����Եġ�������ʵ��:����ɫ����Ŀ��,��������������
����1923�꣬��ʵΪ����ѧ�Կ���д�������ǡ����������ǡ�������Сѧ����ѧ��ʷѧ�����ӡ�������ࡰͳ��Ի��ѧ�����ڡ��ƻ��顷����˵������ѧ֮��Χ��������ܼ����ա��ټҡ����������ǹ��ڵġ����й��������ּ�¼֮�顱������������������ձ����ʡ�Զ��ŷ����������й��������ּ�¼֮�飬�൱������֮�С�������ʵ���������ǡ�,����ѧ�Կ�����1����1�ڣ�1923��1�£���1926��4�£��������������Ϻ�������֯���й���ѧ�о��ᡱ�������桶��ѧ���֡�ѧ������ʵ���������ʡ�ʱ�����Գ����ǽ����Լ�ǰΪ����ѧ�Կ�����д�������ǡ��ļ�����ǰ�߽�ΪһУ�������������Ϊ�㷺����ʵ���������˹�ѧ��������Χ���绯�����⡣
��������˼����ѧ�綨Ϊ��������һ����ѧ��ѧ������ѧ����һ����ѧ���������й����ͽ����й���ѧ������Ȼ�����й���ѧ�����Ǿ����������ˡ���Ȼ�����������Ǿ�����ƫ���ˡ��˽�֮ѧ�ߣ����Թ�ѧΪ��ָ�л�����֮�ᾧ˼��(��ܾ���)�����Թ�ѧΪ�й���������ѧ(��������)��������ʷѧ�۹�ȥ�۲�һ�е�(����ѧ�ϡ���̫��)���Լ����Ϲ�ѧΪ��ָ����(���������ö��)���й���ѧ��(����һ���ѧ�����й���ѧϵΪ��ѧϵ)����Щ�˽Խ�����һ�壬����δ�����ȫ������ȴʼ����Ϊ���й��Ĺ����Ļ��������ܳ��˹�ѧ���ַ�Χ�⡣��������˼�����й�ѧ����١���5ҳ���Ϻ�������֣�1931��)
�����Ŷ�ݥ��1934��ʱǿ��ָ�������������ʡ�������ʹ��ʵ�ںܴ����������ʲ�����֮��ֻ�˽��ѧ���ˣ���Ϊ���DZ����������������Ϊ��������һ�У���ȻҪ��������ѧ�и������ˡ�����һ���������ʵ�������ȫ�������ˣ����ǰѹ��ʵ���ŷ��ѧ���о�����������ͱ����ڽ�һ����������ֱ���й��Ļ�������������ǧ��ĹǶ���������ν��ѧֱ�ǿ���ѧ��������Ը˵һ������Ļ��������ȴ�Ŀ�����е��������ʵ�̬�ȣ�Ȼ������������������������������������������ν���ʣ���Ȼȫ�ǹǶ������� �Ŷ�ݥ�����ִ����й�����Ҫ����?����ԭ�ء�������¿�����
�������ݱ��������õ�20����20��30�������ѧ������˵�Ĺ��ڹ�ѧ��Դ���������ں������ܽ�Ϊ����Ҫ�㣺
һ����ѧ��ԭ���ҹ����е�һ����������ܳ���ʹ���ˣ���������ʾ����ѧУ�ͽ����ƶȵ�ר�����ʡ�
�������ҹ����ű�������ǿ��������ѧ���������֮�£��ҹ����е�ѧ���Ļ�˼�뱻��Ϊ��ѧ��ʼ�С���ѧΪ�壬��ѧΪ�á�֮˵����ѧ��ʼת��Ϊ��ѧ�Ĵ��ƣ���ѧ�ͳ��˺���ѧ������ѧ���ѷ����ϵ��һ��ѧ�ʡ�
�������ŶԹ�ѧ���о�������ѧ��Ӱ���£���Ȼ���ѧ�Ʒ�������⣬����Թ�ѧ�о����������⣬Ҳ�ͱ�Ȼ�����ؾ��ɺ������ɵķֻ����ؾ����ӹ�ѧ���䱦����������������������֮����������Ҫȫ���������ⳡ˼��������ȻҪ��˼����ѧ����־õؿ�չ��ȥ��
������������Ҫ�������ϣ�
��Х�� �ࣺ������ѧ���ۼ���Ⱥѧ��1927�ꡣ�Ϻ���꣬1991��Ӱӡ�档
����꣺����ѧ���顤���������������� 1991��12�µ�һ�棩
ɣ�������������ʱ�ڵĹ�ѧ�о�����ѧ��������ʷ�о�����1996���5�ڣ�
��־���������ѧ�����弾������ڡ���ѧ����˼����������������꣬2003�꣩
¥���ң����й���ѧ�о��Ļع���չ��������ѧ���Ľ�ѧ��Դ����2005�꣩
¬ �� ��������ѧ���������ʡ���������ѧ�����������������弾����������Ǩ��������������Ͼ�����ѧ��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