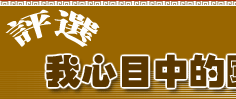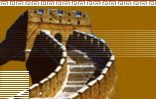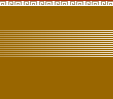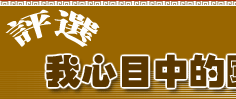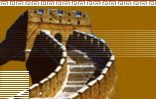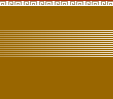�����ϸ����;�ʮ��������ԡ�ѧ�ˡ��ij���Ϊ��־����ѧ��ʷ���о�������ѧ���������������š���ѧ�ȡ������𣬱��ֵ����й���ʷ��û�ѾõIJ�������ѧ�ߣ�����ѧ��ʷ�о�̽����Դ֮�����״����ǵļ����������������ѧ���硢�����������ý��ע�⡣�����봫ͳ�Ļ��������ã���֮�����Ժ��С����������淢�ͣ����ǣ�һ�㱻���������⡱֮����Ĺ�ѧ��λ�ոߣ���Ȼ�������⡣�ڴ˴�֮�£�������Щ��������ѧ�ߵľ���ȡ��ѧ��ʦ�С�רҵ��Ұ����ѧ�����ȵȷ��棬ȴδ��������ϸ���棬�������˾���һ�ɹ��ԡ���ѧ��ʦ���ijƺ��ˡ�
��������ѧ��ʦ�������ӣ����������²�������֮�˺��ڣ���Ͳ��ܲ���Ϊ���Ǽ��ȹ��ĵ����⡣���������ڲ��ٴ�ѧ�����ڿ��조�Ŀƻ��ذࡱ������ѧ�ࡱ��������ʦ�ࡱ������������������ķ�ӳ����Щ���ࡱ�ٰ��������ӣ����Ч��Σ�ʵ����˵�����������ţ�Ԥ�����ߵ�����Ӧ�������ġ����ҿ�������ʹ����˵���ࡰ�ࡱ����ʧ�ܵģ���ô������Ҳ���뿪����Щ���ࡱ�ij��Ժ�����ֵ�����Զ������жϵ�Ȼֻ���Ҹ��˵Ĺܼ�����Ҫ����ȴҲ����������ô���ס�
���������˵���ƺ��������ı䡣��һ����У�ġ���ѧԺ��������˵��֮����Ҫ���衰��ѧ�ࡱ������Ϊ������һЩ��˾�ļ�����Ҫ����˵���ܶ��˾�ԡ���ѧ�ࡱ��ҵ��������Ȥ�����һ�ӭ�����պ�ǰ����ְ�����ơ�����Щ��֪���ơ�������ν��������治֪��Ӧ����λ�Ӧ�����ԣ���ֻ�������ش�����ǰ���ɷ��ҵļ��ߣ�
������ѧ�Ŀ���������ȷ���������ڵ����Ƕ���ʷ�������ȵĹ��У�ϣ������������Լ�����������Ļ�֮����Ѫ���������ڡ��ռ���ѧ������������ѧ��ʦ����Щ�������ҵĿ����ǡ����Ŀ��壬��־�ɼΣ��뷨��Ц��Ч�����ɡ�������ÿ�����Ҷ����Լ��ġ���ѧ������ȻҲ�����ٴ�ͳ���ִ��ij�ͻ���������������ģ������Ƕ��ѵ��ر�����������Ҫ˵ʲô��ѧ�ġ���ǰ�������������Dz����ܵģ��ҿ�ֻ�ܡ����ȴ���
������Щ��ίʵ�Ȳ����ֲ�׳���ض����в��١���־֮ʿ������ΪȻ��Ȼ��������ô˵��ȴҲ���ҵ����ɡ���Ҫ���Ļ���Ӧ��������Ū���ס���ѧ��ʦ���������������������İɡ��Ȼ�Ǹ�����Ŀ��⣬������һƪ�̶̵���ʾͿ���˵����ġ������������������Ӱɡ�
����һ��������һ���ˣ��Ҳ����������Ƿdz�ңԶ�Ĺ��ˡ�����һ��������1913/1/19 ��2001/10/23�������Ĺ�ѧ������ѧ�����˲�������������ڹ����ѧȡ�ò�ʿѧλ���������Ĺ�ѧ������Ҫ�ǵ���8��������ʦִ�̵ļ��Ӿ�ѧʮ�����ξ���������ġ�һ���տΡ��������ģ�
�����飺��ǡ���
�����飺Т����ʫ�����������
�� �飺��ÿ���ڶ��Σ�
�� �飺����ͨ����ÿ���ڶ�������ʮҳ��������Сѧ��ÿ����һ�������ҳ����ͬ�ú�ʵ������в��������������
д �֣�������ʮ�֣�ÿ��д����˵����ʮ�֣�ÿ����һ���壩����������Ϊ����ѵ����ͥ����ÿ���ڶ�������������ֽ��д����
�������ʣ����컹�ж��������е��˽⡰�����¡��������������𣿵�ʱ���ܼ�ִ�̵Ĺ�����ѧ�����������ʢ���������������������꣬ѧ�и��ܡ��������ܡ�ʵ��ͬ�ڽ��췺����̸�ġ�����������ǰ�������������ƽ�棬�����й���ͳ����ʽ��Ӣ�������ִ��ռ�ʽ���ڽ�����Ұ֮���ڡ����ֽ����Ĺ���������һ�����⣬���Ƕ���������ѧ��ʦ����ʵ��Ч�ġ�������ʷѧ�������������ڡ���һ���������������dz�ƽʵ���ᵽ���������������Ҽ��ֹż������С������ż��ǡ�������������У�����ģ�����β���Ǹ�֧����������ʮ��ͷ�����������Ķ��鷽��������ġ���ƽ�졯�Ķ�����ȣ����Կ�����ͬ�걲�������ѧ���IJ��졣��������֤֮һ�������������������䡷������ģʽ��Ϊ����ѧ���������𡱡������ҡ����࣬���������⡣��˵Ҳ����û�����⣬��˵��ѧ��ʦ���ؾ������ҳ��������ǣ����ҵĽ���ģʽ���Ļ���Χ�������������������Ĺ�ѧ��ʦ��ȴҲ�Dz�������ʵ��ʱ�����գ����һ�������ʽ�Ľ������ѻҷ���������̾��Ƥ֮���棬ë���ɸ�����
������һ�������ǻ��������Ƕ����������廪��ѧ�о�Ժ��������Ҳ����̫Զ�����й��ִ�����ʷ�ϣ��ɹ����ں̵ܶ�ʱ��������������������ϻ��߽ӽ�����ѧ��ʦ�������˲ŵĻ���������Ωһ��һ�ҡ��о�Ժ��������һ�����ŵ�ѧ�������ˣ���غ����������ġ��廪��ѧ�о�Ժʷ�������Ʊ��������������Կɲο�����IJ���˵��������嵡�����ά��������ݵġ��о�Ժ�³̡�������������ּ�����ˣ����о�����ѧ�������ר���˲š���Ŀ����ʵ��ȷ����Ŀ��ר���������������˲ţ���һ��������Ϊ������ҵ�ߡ�����������ѧУ֮��ѧ��ʦ����
�������о�Ժ�³̡�֮�����о����������Ǿ�����֣�����Ժ�Է¾�����Ժ��Ӣ����ѧ�ƶȣ��о�֮����ע�ظ������ޣ�����ר��ָ��������鲻��ѧ�ƣ����Խ��ڸ���Ϊ������ʹѧԱ����ڹ�ϵ�쳣���С���������������ָ��֮ѧ�Ʒ�Χ���ɸ������Զ����¿ɳ���ƽ����ѧ֮�ĵã�������ר��֮��Ŀ�����ɻ��֣������ظ���ͬһ��Ŀ�������н�����λ����ָ������Ϊ���š���������ѧԱ����ʱ�д����ѣ����¹�Ħ�������ɶغ�����֮ѧ�磬���ս���Ѭ��֮Ч����������ר�ν��ڵġ��격���ѧ��ר��֮ѧ�ߡ�����������������ά������㡡���Ԫ�Σ������Ǿò���ѧ��֮�ڵ��ˡ�
������˹Ժ����˹ʦ������˹�ţ�����֮ν��
������Ը��������ѧ��ʦ���������ߣ��Ƿ�Ҳ���Բο�һ����������������أ�ֻҪ����Ϥһ���ִ�ѧ��ʷ���˶�֪���������������Dz��������ġ����죬����ھ��ѵij�ԣ���棬������ȥ���пɱȣ����������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