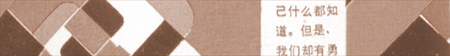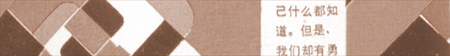��ʷ��ѧʷ����
�������л�������Ļ���ͳ�У���ʷ����ѧʼ�����Ų���֮Ե������������ʽ����ѧ������һ����ʷ�����µIJ��˵������ƾ���ʷ���й���ѧ������Ҳ����ϰ���ڰ�������ʱ����������л��֣���������ѧ��������ѧ��������ѧ��������ѧ�ȵȡ��й��������ʶ������ѧ�ķ�չ��ʱ���仯֮��Ĺ�ϵ�������ڡ����ĵ�����ʱ��ƪ����˵�úã���ʱ�˽��ƣ����Ĵ��䡱���ԡ��������ơ���������Ԧ��������εӳʮ�����Dzɾű䡱�����ǣ�����һ����һ��֮��ѧ����˵�����Ͳ����������������й���ѧ��չʷ�ij��û��ͬʱҲ��Ϊ��������о�����Ҫ˼��ָ����
��������Ҫ˵����ѧ����ʷ�Ĺ�ϵ����ԶԶ������˼���ѧ�IJ����뷢չ������������ʷ�ı仯�������ݺ���ʽ��ʱ��Ҳ��ʷѧ���֣�������ʷ����ʷ���ġ����й����Ϲ�ʱ���༴����ʱ�ڣ��ԡ������������Ϊ�������й����ڵ���ʷ������ͬʱҲ�����dz�֮Ϊ����ʷɢ�ġ���Ի��ʷ����ѧ��������������ʫ������������ѧ��Ʒ��Ҳ����ʷ�о�����Ϊ�������ɿ����Ϲ���ʷ���ף�������Щ��Ʒ��ֱ�ӱ�������֮Ϊ��ʷʫ��������ν��������ʷ�������������ġ������˺����Ժ���Ȼ����ѧ���ķֻ���ʹ�й�����ͳʷѧ����ѧ�Ĺ�ϵԽ��ԽԶ����������ѧ��������ʷ���߰���ʷ��Ϊ��ѧ��ĵ�����û����ʧ����Զ�����صġ������Ӵ����������Ӵ����ʼ���γɵ���ʷ�Ӵ���ͳ���������Ժ���εΪ��ۣ�������Ԭ������ƽ�ġ�Խ���顷�����ʵġ���Խ����������ġ�����۹��¡�������ġ���Ů������һϵ���������ɴ˶�����κ���ϱ�����������С˵�������Ժ�����ʷ���ﴫ�棻�δ��н�ʷ������Ԫ������ʷϷ�磻��������ʷ����С˵���������ʷ��ĵ�˵�����ֵ�������ʷ����¼����ʷ��ĵĵ�Ӱ�͵��Ӿ�ȵȡ����ǵ������ǡ���ʷ���ģ���ʽ�ǡ���ѧ���ģ����ġ��롰ʷ��������������ˮ�齻��һ�㣬��ԶҲ�����ֿܷ�����������һ����Ҫ���й��Ļ�����
�����ź����ǣ�������������Ȼ�ڶϴ���ѧʷ�ͷ�����ѧʷ���о��в��ϵ��漰������������һЩ��Ʒ��Ҳ�Ǵ�ͳ��ѧ�о�����Ҫ���������Dz�û�а����ǵ���һ��������Ļ���������ʶ����ȻҲû��������ʾ�����������ʣ������ķ�����չ���̽�����ϸ�Ŀ��졣�����ȫ�����ʶ�й���ѧ��ͳ���������ܲ�˵��һ��ȱ�ݡ������������������ѧ���۹⣬��������һ��ѧ�������Ҫ�ԣ������ȶ���չ����ϵͳ���о���������һ���͵���ѧͳ��֮Ϊ����ʷ��ѧ������һ�ζ��������ʽ����˾��п�ѧ����Ľ綨�����䷢����չ����ʷ�����˴���������������д���˵�һ���й�����ʷ��ѧʷ��������������������������һ����п���������Ĺ�����
�������й���ʷ��ѧ�����й���ʷ����ѧ��������ϣ�����������ѧ�ıʷ���д����ʷ����������ʷ�¼�����ʷ����Ϊ��ĵ���ѧ��Ʒ����������ʱ�ھʹﵽ���൱�ĸ߶ȣ������������л�������Ļ����������������������������й��������ˡ�������ᡱ��ԭ��ʮ�ַḻ���й���˵����������𣻶�ʷ���Ļ��ķ�����ʹ�й��˺�����γ�����ʷ�Ĵ�ͳ����ʹ����ʱ�ڵ��й�û�в������ϣ��������ƪ��ʷʫ������ȴ������ϣ����������ʷ���������˵������Ϊ��ϣ��������ʷʫ�ij��ֲŻ��������ѧ�ṩ�ˡ��ḻ����������⡱���Ӷ��춨��������ѧ���Ļ���ͳ����ô���й���Ҳ����Ϊʷ���Ļ��ķ����ʹ�����ص���ʷ��ѧ��Ϊ�й�����С˵��Ϸ���ȵ���Ҫ�Ļ�Դͷ��ʹ��ʷ��ѧ��Ϊ�й���ѧ��һ������������Ϊ�����������Դ�Ϊ��������о��й���ѧ�����������൱��Ҫ�ġ�������Ϊ�й���ʷ��ѧ�ı��ʸ��趨�ԣ�д���˵�һ�����п���������й���ʷ��ѧʷ�����һ���һ���µĽǶȽ�ʾ���й���ѧ���صķ������̡���չ���ɣ������ڴ������Ļ��ķ�Χ�������õ���ʶ�й���ѧ��������ʽ�Լ���������������ɫ��ȷ���й���ѧ��������ѧ�еĶ��ص�λ��
��������֪�����й���ѧʷ��Ϊһ���µ�ѧ�ƣ�����������ѧʷ�۵�Ӱ���·�չ�����ģ�������й���ѧʷ���ɵ���ʶ���ڲ�֪������Ҳ�ܵ��������Ļ������۵�Ӱ�죬��ʹ���������൱����һ��ʱ���ڣ�ϰ���ڰ�������ѧʷ�ķ�չ֮·�����ۺͺ����й���ѧʷ�ķ�չ���������ʷʫ������������ѧ���Թ�ϣ���ij�ƪʷʫΪ�����϶��й��Ŵ�û��ʷʫ�����������������й��Ŵ���ѧ������ı�־�������۶���Ȼ�Ǵ���ģ����Ҳ������һЩѧ�ߵ�ǿ�ҷ��ԣ�������Ϊ����ʫ�����еġ�������������������������������ʫ�������й��Ŵ���ʷʫ��������Ȼû�й�ϣ��ʷʫ�ij��ȣ�����ȴ�߱�ʷʫ��ȫ��Ҫ�ء����ֽ�����Ȼ���е����ġ������ݻ��ԣ�����������������ʷʫ�ڹ�ģ�ĺ�ΰ�����ݵķḻ��Զ���������ʷʫ��ȣ����Դ������бȽϣ���Ȼ����˵�й��ĹŴ�ʷʫ��ͬʱ�ڵĹ�ϣ����ʷʫһ��ΰ�����Dz������Դ���Ϊ�����й��Ŵ���ѧ�Ƿ�ı������Dz���ƽ�ġ���Ϊ�����ֱȽ��У����ǻ����ڲ��Ծ���������������ѧ��������ϵ����Ȼû������������ѧ�����۵�ƫ�������������ڵ��о�����ȫ�������й��Ļ���ͳ��ʵ�ʣ����Գ�ֵ���ʵ˵�����й���ѧ����һ����ȫ��ͬ�������Ļ���ͳ�Ļ����гɳ������ģ����Ŷ��صķ�����չ֮·��������ͬ����������˵���ҹ��Ŵ���ʷʫ�IJ������������˵�����������Ļ��ġ��̴��������罫����Ϊ���������Ļ���һ���ص㡣�й���ѧ���Լ����صķ�չ��·���й�������չ�����ٵ�����ѧ���ں���ʷʫ��ʱ��Ҳû�в��������д���ģ������ʫ�����й��ڵ�ʱȴ�ҵ���һ���µı�����ʽ��������ȫ�桢�꾡�ط�ӳ��ʷ��������������������˺���ʷʫ������ˣ����Dz���ҪΪ�й�û�в�����ϣ�������ij�ƪʷʫ���Ա�����Ӧ��Ϊ�й�������ƾõ���ʷ��ѧ��ͳ�������������վ�����緶Χ��ȫ�������ȷ����ʶ�й���ѧ��ɫ������ʾ�����Ǽ���ġ�
�����й���ʷ��ѧʷ�ǰѡ��ġ��롰ʷ����Ϊһ��ľ����ۺ���̬��һ���µ���ѧʷ���������������Զ���Ļ����ݣ�������ʢ��˥����������������������о�Ҳ�ͱ���������Ļ��Ĵ��������ۣ����й��Ļ�����������̽Դ��ʼ������ѧ��ʷѧ�Լ�������ʶ��̬����״��ϵ������ͷ�����ӷ����ӵ��й��Ļ�������ȥ�����䷢չ���硣����˵���й���ʷ��ѧʷ��д����һ��ȫ�µĿ��⣬Ҳ��һ���ϴ��ϵͳ���̣����Ѷȿ����֪���������ھ���������ڷ��о���������壬����д�����ⲿ��ʮ���ֵľ�����ȫ���Ϊ���й���ʷ��ѧ�������������й���ʷ��ѧ�ķ�������й���ʷ��ѧ�ij��족���࣬���ڡ����ԡ��о��й���ʷ��ѧ�����ʼ��䷢չ��������˿�ѧ�Ľ綨���Ҫ���������������е��������⣬���������������������������ʷ��ѧʷ�Ŀ���µ�һ��չ�������ġ�������������Ϊ������ʷ��ѧ�Ļ��������Ǽ�����ʷ��ѧ����ʵ��������ԣ�������ѧ�ĵ������������ԡ����������ر�����ʷ��ͬʱ���ڱ�����ʷ�Ĺ��������ֳ����߶���ʷ�Լ���ʵ��˼������������ۡ�����һ���ԼȽ�����ʲô����ʷ��ѧ��ͬʱҲ�綨��ȫ�������ķ�Χ����Ϊ�����ʷ�ı��������۵ķ������������õĻ������������ڻ�ָ�������й���ʷ��ѧ��չ�������������й���ʷ��ѧ���ʵ��γɼ����ݻ���ֻ�а���������һ�㣬����������һ���������й���ʷ��ѧ������չ�Ĺ켣�������켣Ҫ�Ϻ��й���ʷ��ѧ���ڵķ�չ���������ǽ��й���ʷ��ѧ���ʵ��γɡ��ݻ������й������ʷ������ȥ���Թ���ʱ����ᷢ�֣��й���ʷ��ѧ���ʵ��γɲ��������ķ�չ����ϵ��Ҳ���й���ѧ������ݽ�����ϵ�����Դ�Ϊ�������������ڰ��й���ʷ��ѧ�ķ�չ���»���Ϊ�ĸ������ʷ�Σ����Ϲŵ���Ϊ��һ���Σ���κ������Ϊ�ڶ����Σ���Ԫ����Ϊ�������Σ������ġ��˶��Ժ�����Ϊ���ĸ��Ρ�������ÿ���εIJ�ͬ�ص㣬�ֱ�����dz�֮Ϊ��������ʷ�ĽΡ�������ʷƫ���ĽΡ�����ʷ�����ĵĽΡ��͡���ʷ���ݵĽΡ�������Ϊ���������ڵ���һ��������ʷ�ֶ��Ƿ����й���ʷ��ѧ��չ���ɵģ������Ҳ���൱ȷ����������ѧ����������ģ���������������ʶ�й���ʷ��ѧ�ķ�չ���̣���Ϊ�Ժ���о����������õĻ�������������������ָ����ʷ�Ŀ�ܣ�����������Ȼ�Ͱѹ�ȥ��ѧ�о��������漰�������������漰ȴ��Ϊ�������봫ͳ����ѧϵͳ��������ܽ��������о���һЩ�������硶ɽ���������������Ӵ����������Ӵ��������ӡ���������һ���������й���ʷ��ѧ�ķ��룬���������趨��һ��ȷ����ѧʷλ�ã�ͬʱ�ó���һЩǰ����δ���Ľ��ۡ����⣬ȫ��ḻ�����ݡ���ʵ�����ϣ�����������٣��Լ�һЩ�������۴��������������������������̵�ӡ�����ij��֣��ǽ������й��ŵ���ѧ�о��������ϲ�����ջ�Ҳ��������21����ѧ�����һ�ݺ���
���������������ҵ�ʦ�֡�1984��ף����ǹ�ͬ���붫��ʦ����ѧ����������¹�����ʿѧλ����ͬ��һ�ҡ������ֲ�����ѧҵ�ϸ����Ծ�İ������������ϸ���ͬ���ֳ�һ������������Ĺػ������ǹ�ͬ���飬��ͬ�������⣬��ͬ�ܲ��ʹ���Ҳ��ͬȥ���ͳ������µķɻ���ʮ�µ���ѩ�������ij�Ϧ�ദ���������ޱ��������꣬Ҳ������������������Ļ��䡣��ʿ��ҵ������ȥ���ൺ������������������ȥ�˴�������Ȼ���������������֮��һֱû���ж�ѧ���ϵĺ����뻥����һ����������д�ˡ����ش���ѧʷ��������������ѧʷ������ͬд�ˡ���ʮ�����й��ŵ���ѧ�о�ʷ�������ൺ�ʹ��������ĺ����������������ж��ٴεij�ҹ��̸�����߱�����˼������ѧ���ϵ����ѣ����������е�����Ҳ��ͬ�ں���ʰ�����ı��ǣ�����ѩ���˻�������Щ���У�����ѧ���ϵ��ڷܣ������������˺ܺõİ�����ʮ���������������ǹ�ͬ�ĺ���֮�⣬���Լ���д�˶ಿѧ�������ͽ̲ģ�Ϊ����ԺУ�Ľ����������ش��ס���Ȼ������Щ���ѧ���о��У�����Ͷ��Ļ��ǹ����й���ʷ��ѧ��˼�������ڹ�����ʿѧλ֮ʱ�����Ͱ��Լ���ѧ���������������ԡ�����������͡�ʷ�ǡ���Ϊ������������������ʷ��ѧ�ϡ��ⲿ������������ʮ���������й���ʷ��ѧ�����о���˼���Ľᾧ����������ڸ������ڽ���˷�˶�ijɹ�����Ϊ�������ܵ�ѧ�ܣ������ܲ�Ϊ���ķ��ն��ж���
�����������͵ĵ�һ�꣬��һ�����ĵĴ��գ������������˸����������ⲿ��壬������д���仰Ϊ�� ȫ���зḻ�����ݺ;��ٵ��������ѷ�����֧�����ܾ��ԣ��������ܹ�����ס���ߵ����к���ʷ�Ŀ��顣�ڴˣ�����д�����ԣ��Ա������ȶ�Ϊ��ĸ��ܺ����飬һ��Ϊ�ҵ�ѧ����ȡ�õijɹ���ʾף�أ�����ҲΪѧ�����������͵Ŀ�ʼ�Ͳ������������д�����ʶ�����������ˣ���Ը���������ٽ�������д��һ����ͨ�Ž����ʷ��ѧʷ��
�� �� ��
2001��3��15���ڱ�������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