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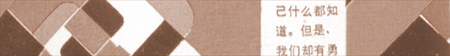 |
|
|
��Ԫ������һ�����ʮ��
|
|
|
|
|
|
|
||
|
�����¡����������죬�����ͬ�ɡ��� �����������ݵ����� ������һ�ֶ����ʵ����Ч����������˵���������У��������ں��������������ұ������Ҳ����˵��������˵����벻��ʵ�֣���Ҫ�����ڴ���Ȼ�������������������Ȼ����ʵ���Ҳ�����·��Ҳ�ͺ���Ȼ����������֮;������Ȼ���������˵ģ�û�г��������ӣ�Ҳû�йٳ������ǣ�ʫ�˵ĸ߽���־�ܹ���֮��г��������ˣ������ɽ��ˮ���������顱�������顷������������Ҳ����ɽ������⣬������������ͬ�ϣ���������ȫ�����ڴ���Ȼ֮���ˡ� ����ʮ���������ݵ�������ںڰ�������п�����������������ij�����ʹ���������һǻ���ߵ���������Ϊ˼��֮���������־Ȥ������־ʫ�������������˼���ˣ�������ݻԣ�Ը��֪�����������������������ʫ��ϣ���ڹŴ��ĸ�����ʿ���ٵ�֪��������������ǧ�أ����㷢�����֮�顣��ʥ��ʿ���ޡ����������ֶ�������ʹ��д�����ġ������顷������ �����ԶȤ����Ȼ��Զ���Ϲ�������ʿΪ֮���ޣ�����������ǧ��Ҳ�� �֡�����־�����Ӵ�������֮ע����ϲ������������ ¼�Ϲ�����ʥ�����ݣ����������ߣ���Ϊ���ޣ��Ի������ڹ�������һ��һʮ�о��ˣ�����֮������֮�ڣ�����֮��ǧ��֮�����ӡ� ���ⲿ��������һ��һʮ��λ����������ʿ������־ʫ�����������Ѩ�����ݣ��������ʦ�������������ݵ��ж�ʮ�����͡�����ʫ��Ի�� ���۸�������{��ά�����v��������������n�����ǰ�����Ϊ���ɡ��֣����գ�Խ�ò��飬˼�ѳ��֣�����ɽ�ء�����ѳҵ�����ܷܷɡ� ʫ�����������������˹�����־Ը����ϣ�������ڳ��ַ�ݣ�������ɽ��ˮ�ģ�����Ϊ������ѳҵ������ֻ����{ϵ��ˮ��һ�������ܸ߷�Զ�㡣�������ʫ���ס������� ���˴������������飬��������ѳ�������м��飬���� �ںڰ�������������Ѳ����أ�������ʷҲ�����壬��ѵ�ѡ����˳������֮�������ֵ����𣬸ߵ�Զ�С�����������������ʱ������˵�� ��ޱɽ����ɢ����ᶣ���Х�������������١������ķ�ʫ���� �ն���˵��������ɢ�����ķ�ʫ����֪�����ӣ���������Ի������ޱɽ����ɢ����ᶣ���Х�������������١��ߣ�����־֮����Ҳ��˾��������ɱ��ɢ���ڣ�ʹ����δɱ֮ǰ����֪��ɨ���������˼䣬������֮Ͷ��Ҳ����ޱɢ�������������գ��������С���Ϫ�����Ի�������һ������κ�����ϡ����ն��½�����λ�ʮ�־��ʣ�������ȷ��ʵ���ϣ���˾���������Ļ���֮ͽ��������Ϊɱ��һ����������ڵġ������������ʷ�У�����ƻ������ܴݲ����ԵĶ����������Σ��������������ľ�����Щ��Ū����Ȩ���ļһ��������˵����ʹɱһ�������������ʲô������ʱ���ĸ����ڡ�������һ������������˵������������֮����ϣ�ţ�����ţ�����֮���ȰΣ�����֮�����ۣ��˻��������ӡ�ͽ�Ժ������ӡ��������������������������ں��ˣ�������ڴ��١����������顷����������������̵�ָ��������������ԭ�� ���������й����ڵ��������������ɽ��������ʮ����֮�ã������ֱ����Ӷ���������־�����Ӵ�������֮ע����κ�ϴ���� ��Ԣ�Ӻ���֮ɽ���أ������������ٿ��������о���֮�ԣ��ִ��Ӳ��ƣ���֮�Ӷ������Ʊ��������� ���͵�ʱ��������ʿ��������н�������֮�����ꡣ�Դˣ��������������Ѿ��ᵽ�ˡ� ������ݵ��ж�Ҳʮ�����͡���ӽ��ʫ������ʮ�ģ� ������ʿ����־��ƶ����Ҷ����٣����ͷ������������࣬���˭��ѳ�����ܷ���ż������Ǽ��ס���������£�ȥ��ζ���档�����ſ��飬���澫���ɿ��߽ڣ��Ӵ��ʺӱ��� ʫ��ָ������ĩҶ�������٣�С�˳��𣬱�ʾҪ��������������Щ�Ŵ��ĸ�ʿ����ָ��е�־�ڣ����ݺӱ�������������ν�����桱����һ����ѧ�����������ʫ��Ի���������ɽ��������Ҫ�����������������ң������Ҫ������ɽ���롰�������Ϊһ���ﵽ�������ڵľ��硣����־ʫ���ס���һ�������������ˣ����������ۣ��徲����Ȼ���ٻ�����Ϊ��������ʫһ�ס�������ӽ̫�أ��������顣����ϳע����̫�أ����飬����ȻҲ������ת���Դ��ϡ�������Уע����ҳ77����Ȼ�����ǡ��������������桢�����������߱��塣����ʫ���������彽���ӣ�ǰʶɥ����������ɥ��Ȼ�������ѿɺ͡���������ν����������Ҳ�������˵�ġ����桱�������û�д������ʿ�����һ��Ϊ�٣�����Ԥ�������Ⱥ��εĹ�ְ��̫ξ�������ɡ��ξ���˾���ϵ������������������ɡ����ںɢ�ﳣ�̡���ƽ��Ͳ���Уξ�������顷����˵����������£���ȥ��ְ�����θ��ڣ���������ɡ������ھ�Ԫ���꣨263������Ϊ֣��Ȱ�����㡷����������֮ƽ����������һЩ��������˶�����Ʒ����Ķ��ʡ�Ҷ�ε�˵��������ȫ�ڽ���ֱ���總˾��ʦ��������Ӷ���ʷ����֮ʿ����֮�����˾������ȫ֮���Դ���֮�����Ǹ�˾��ʦ��δ�����ѻ�Ҳ������ѡ���ؽ��á�Ȱ������һƪ���˼��������������ˣ����������Ϊ!�����۱�����֮ʿ����Ϊ��ʭ�����T�У���ί����˾���ϣ������T�к�?������ʯ��ʫ�������£�������ʫ������ҳ434��Ҷ�ϵĹ۵�Ƚ��д����ԣ������������DZ����������û�����������⡣���˾���ϼ�������ί�ߣ�������������ȡ���ض������ݷ�ʽ�����ġ����飨ҳ109~110������̸���й�ʿ�˵ġ����������⡣��κ��ʱ���������ݼ�ɽ�֡��������Ϊ���ݣ��Լ����С�¶���˼������Ϊ���ݵ����ⷽʽ����ϲ��������ʫ���ס������� �������ﻯ�����ײ��ɰ������ؿ����Σ��α���ɽԭ���������ᣬ������·�ѡ�������ʱ�ʣ�DZԽ���ˡ������ص��ӣ��ñ䰲��Ǩ������ȫ��ʫ����һ�� ���ַ�ݣ���Ȼ�����ߵ������������ζ��أ�����ʿ���ľ���������֮�У��ʧ���˵��Ƕȡ��������Ե����𣬹ؼ������ܷ����ص�������������μ����档�����顷����ν���ڡ�������⣬�����κ���ʱ�˶�ν֮�ա�����֪����һλ�������εġ��ա��ˡ�����˵������ݡ����� ���»�ڶ�ɽ����Ȼ���£��������ڻ��������������Ҿ����Ҿ�Ի�����˾����������裬���֮��ڤ�����Թ��ˣ�
�� ������Т��ע�� �����ӡ�Ի����������������֮������ʧ֮������������֮��ֻҪ�ܹ��������ڻ�����Ҳ�ͺϺ����˵������ˡ��ڶ���ʱ��������������������Դ���ʿ�������������������������ӹ��ٹ�֮�£�����������֮�ġ����������顷�����塶���������������ԣ�����泤����ͬʱ������Ҳ�������ߵ���̬�����ٵģ���Ϊ����Уξ�Ͷ�ƽ��������������˵����һ�㡣��һ���棬��������Ҳ�������ֻ��ĺð취�������������������˾���ϣ������ܾ����ˣ�Զ��ɽ�����������֮�γɶ���������ɱ��֮�������ڳ�͢����ְ�����ܷ����κ������������ǻ�õ����ݺͱ����ġ���Ϊ���ʿ���������ܸߣ�˾����������£��������ʾ�Լ��Ŀ�����ȣ���ɴ˵������ա�������������˾���Ϻ������ԴǼ��ң���â��¶����������ɨ���������˼䣬����Dz���������֮�¡�˾����ν��ҹ�����������������˵���Ʒ�塷��һ����ָ�˶��ԡ���������Ը���������ô���ң�������Ʒ֮������ͬ����ߡ�ΰ��ġ����˷�����˵������ɢ�����Ա���Ϊ˾���������伣��ͬ������Ʒ���졣����������ղ�ԡ���������0����������Ϊ��̡����ʡ� Ȼ���������ľ�ɽ�֣������Լ����У������ܳ�Խ�ڰ�����ʵ���ڵ�ʱ���������һ����������ʿ�Dz����ܵġ������Գơ��������DZʫ����֪������忲��������ӣ�Ȼ��δ��ƽ���ģ���Ϊ�����Ƿ���з����������ж�������Ҳ������������������������ļ�Уע����ҳ258�������Լ��ǡ�����֮����������Ȼ־���������Խ��ʵ�������ĵ�ʹ��ȴ�����ѡ���ˣ������ھ����Ϲ�����һ��������翵��������磬һ����������������֮������������������ס������ ����˷������ݣ��游���ﲨ�����������ѣ����������Σ����������⣬��������ϼ�����������ۣ���ң��̫�ͣ����Ѽ����������ٵ���裬���� ����ʫ��˼��˵������˷�����Կ���Ϊ�ܻ�֮�����游��ϲ���Ʋ��������˶�;����������Ϊ�ѣ������ݱϾ�ʮ�����ѣ��ʲ�������������֮���ã��������������֮�⣬�����̫��֮�У�����������֮�ϣ������ٶ�����裬����֦������ϼ�������ǣ��û���ˣ����з�����ʧ�ˣ�����ʲô�����������������?����������ʫ������������ʾ���ߵ��������������������������ѣ������÷����ԣ����³�����Ҳ��������������Уע����ҳ64���ӱ����Ͻ����;����ɵ�����������һ�ֽ÷����Ե��ж���ֻ�����������ʥˮ����˳Ӧ���Ե�������ϴ�������ʹ�࣬������������ѡ����ӽ��ʫ������ʮ�壺 �ּ��������������顣��֪�����棬������̫�壡 �����л��֣�Ҳ�б��������ۻ��ֻ��߱���������ʹ����ƣ��ڣ�ֻ�����̫�壬�������һ�г��ۡ���ӽ��ʫ�����ʮ�ˣ���ϵ�����������忥ͬһ�b�������Ŷ�Ŀ������ȥ���ǡ���ʫ��Ҫ���ŷ��������Ѻڰ����������ֵ�������������������е�����֮�飬�����ɵ������������ó������š���֮����������������������һ��ǿ�ҵ���ʶ���Ǿ���Ľ���ɡ� �������ǿ�����������˼����������棬��������������������ʱ�����������Ƕ�������˼��Ŀ��죬������һ�ִ��Ե��������������Ժ���������˼���ȫ���������������ݺ����ɣ���һ˼������Ҳ������ȫ���εݽ������������ֳ�һ�ֽ��ڵ�״̬��������˼��ĸ�����Ҳ�����ڴˡ� �� |
��ѧ��վ����Ȩר�У�����ת�أ�ע��������������ã���Ϊ��Ȩ��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2917824
010-62917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