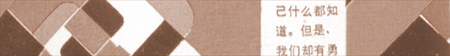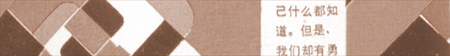�����Ȿ�ļ��㼯���ǽ�����������һЩ���ĵ�����ʣ���һ�����Ƕ��ģ��ʵ������ɡ��ڶ����ֳ�Щ�����������ࡣ��Ȼ������ͬ��Ҫ���۵����ⶼ��һ�ࡣ���ܽе�����ʣ�ȴû�ж��ٽ������˵���Ҳû��ʲô�μǣ�������ָ����·ȥ��һ����Ϊ����ѧ�����ó�ָ·�������ж���һЩ���뷨����Ҫô�Ǵӵ��������������뷨��Ҫô�����뷨���ҳ��ĵ������ݡ� ����
������������뷨���Ҹе�����Ȥζ���Ⱳ��ײ�������е��У�ȴҲ���������Ⱳ����ʽѧ������רҵ��һ���ǿ��ţ�һ���ǵ�����ȷ��˵�����ĵ�������ʷ����������������רҵ������ѧʱ���⣬������ѧ��ȴ��Ȥ��Ȼ������ѧ����ʷ����ѧ�������֮�������ǵ��������Ѱ�����ĺۼ�����Ҫ��̤ʵ��˵������������������������ѧ�ʵĻ�����������ʵ������ʵ�ù��ڡ��ɰ͡������ƾ���ʶ������Ŷ�����ԭʼ���棨���ŷ��桢����־�飩�����˶���пࡣ��ʵ��˳�Ż��������ߣ�������ѧ�ʶ����ݺᲩ�����侫�ʲ��档 �����õ�����˵������һ�㽻̸�Ķ��ǵ���֪ʶ��������ѧ�������£�������֪ʶ�����й��˼�롢���ۣ��ŵ��������������β��������²����Ļ�չ�֣���ʷ��˼���Ը�����˵����ǣ��������硢�������顣���ⷽ�����棬������չ���о��������������¡� �����ٵ����������£������������뵽�μ�һ��Ķ�������д�����Ļ��˵�һ�������������棬���߱߿��߸ж����������������渡�룬�ܷ������ժ�������ʣ�Ȼ��Dz�ɴʾ䣬������ҹ�������賿��������ƪ������������ģ��������龰���ڵ�·�ӣ��ڡ�������������ǡ��������º��³�����˽�����ġ�����һ�ֵ��͵��й�������Ϊ�������ǵĴ�ͳ�������˵���������ǵ����Ļ���һ���ص㡣������һ�������֪ʶ�ǡ������ģ���������Ӳ���������˹����ֵ���ѧ�ʽС�Сʶ���� ������Ȼ�����ǵĵ����Ļ��л�����Щһ�ص㣬���硰�����Ұ�������ǽ��ι�ƽ���µ���ԣ������硰��ʱ��������������ǽ�������˵����ԡ����������֪ʶ�ǡ�Ӳ���ģ����������ڡ�Ӳ��������������ơ����˹����ֵ���ѧ�ʽС���ʶ���� ���������ǵ�����Сʶ���Ǵ�ʶ�����Ǹ��������˵���Ҫ�Ľ��ȳ̶��������ġ����Ǵ����ɽ����أ�������һ�ף������ྐྵ������ô�����������µĻ��������dz�ס�оͱȶ��������鷳�����࣬�ټ��������֯Ҫ�˴˽�������������Ҫ���������ڵ��ϵġ���չ���Ѿ��ղ�סբ�ˡ���أ������Ǹ��أ������Ѿ���á����ִ����ˣ���˵������ѧҲ���ź��ִ��ˡ�����˵����ν�����ִ�����ѧ�������ǵر�����Ļ����������ˡ�����������һ���������Ļ����� ������Ϊ�Ҹ�������ĵ���������ʷ�����о��У�Ҳ�������ģ������ܾ��ò�����˵����ѧ�ǡ���ѧ�������ĵ������뿪���ˣ������������ɢ���������ĵ�������Ӧ�����ǡ���ѧ�������⣬�������ڴ������棬������ѧȴ���˵���������������Ƿ�ʱ�����ֽײ㣬�����ҵģ����Ե���ѧҲ���Ǵ���ѧ�ʣ������˵�ʱ����ֵ����仯�ں����о����ĵ�������Ҫ�Ȱ��˿��� �����ҵó��ϣ��Լ��Ե���ѧ�����⣬���������˵��������������ĵ���ѧ����ĺܶ࣬�ܵúܿ�������ζ����ʮ�㣬��ȷ������������ѧһ�ߣ������ҿ�ʼϲ��������һ����Ҫԭ���Ҷ����ĵ�����ƫ�ã��Ǹ������⣬û�д�������� ����20 ���� 80 ������ڵ� 90 ������ڣ��ҵ�����ϣ�����ȴ�ѧ��Ҳ��ѩ�Ǵ�ѧ��Ӣ���� Syracuse University ����ѧһ�ء�ϣ�����ȴ�ѧ����������ѧ������ 80 ���ĩ�����м�λ��ѧ����ͷ�ˡ����������ֵ���꣬Ӧ��˵�ǡ�����һ���������ں�����������£����涮������Ӣ��Ҳ���һͷ��ײ��ղķ˹���˿ϣ� James Duncan ���Ŀ����λ�˿Ͻ����Ǽ��ô��ˣ��Ҿ����У����ٲ���Ǯ���£�����������������ר����ѧ�����ε��dz�����ߵ�����֮ѧ������ֱ�ӵġ���������֮ѧ�������������о�����������ѧ��Ӱ�������ǡ����Ļ������������֡���������ͷһ�ſνС� Cultural Approach to Place ��������ε���������������ĥ�˺ü�����ݲŴ������ף�������Զ�����ˡ����������������ĵ���ѧʷ��̤̤ʵʵ���꡶����ѧ�����ѧ�ҡ���������Ӣ������ѧ��Լ��˹�٣��Ȿ�飬�����ڽ����������ĵ���ѧ���������ϣ������ѧ�˼���֮���ұ㲻�ٶ��������ľ��������ˣ��������̻��Ķ����й��Ķ������Ͼ��й��Ķ���������˵����Ѫ���⣬�����������ߵ�� ����ʱ���ˡ����꣬�һص���������ѧǰ��ѧ�ߵķ緶һֱ���Ҿ����ġ���ʱ�ı���Ҳ����£һ���вŻ����������ѧ�ҡ���Ҳ½����ʶ�˱�ʦ��ѧԺ������������ӡ��ݵ����༭�ҡ��Լ���ص�һЩ�������ѧ�ҡ���Щ�˻��������в�����ʹ�Ҹе����ڵĵ���ѧ���������� ��������ʷ�������棬ʱ������һ������ͷ����Ȼ�����Ǽ�λ��������IJ���Ѿ�ʮ�ַ���Ժ��µĴ�ͷ����˭��������˵�ء���ʷ����ѧ���ҹ���Ӧ���Ǵ�չ��һ����ɫѧ�ƣ��й����˲���֮����Ҳ��˵���Ŵ�����֮������������ʷ��Ҳ�ڵ�����ǰ��˵�ˣ����ĵ�����ÿ�������ں������£��й��Ŀռ���ô����ƾ���죬�����ȵ����ĵ�����������쳤��ֻ��һ��С�����ѡ� �����Ҹе����й������������ĵ�������֮�У�����Щ������������������ġ����˵����ĵ������飬�Լ��ڴ˾�������Ϸ�չ���������ĵ���֮ѧ����������һ��˵���飬��Ȼ����Ҫ��������һ���ձ����õġ���ѧ�������ܰ�õ����й������ĵ������ر��������γ��ڵ����ĵ�����Ϊ�����춨���������Ŀռ��ܣ����������������Ƕ�һ�ݵġ��й���˵����Ҫ��д���ǡ��������ĵ�������ŵ���ʷ��ȥ�۲죬�Ǻ�����Ȥ�����顣��Ϊ��������Ȥ����д����ôһЩ���ɶ��ġ��� ����������������̸��ѧ���������Ǹ���ѧ�ʵ��ܸ��ӣ���ʿ��ơ���ѧ��ʿ���� Ph.D. �������ĵ���ѧҲͬ������ѧ�ҹ����ܣ��ҵõĵ���ѧѧλҲ�ơ���ѧ��ʿ��������ϣ�����ȴ�ѧ�����ʱ�������Ŷ���ѧ������������ͬ��һ����������ѧϵ�ĸ���ͬѧ��̣�Ū������Ϊ���죬���ҡ��㵽������ʲôרҵ�ģ�����ѧҲ�ǡ����ġ�ѧ�ƣ������ĵ���ѧ����ϵ��������Ȼ��ǰ��˵�ˣ����ĵ���ѧ�����������ѧҲ��������˾�һ�����ӣ���ô�ܲ������湴���أ� ���������������ﳣ��Щ�����ء��ŵĹ����ϵ�������Լ�ȴ��ʶ��������һ����ʾ��˼·�ٻ��νѧϰ��Ҫ���������������������ٵ����������ڼ���˼·�����ڶ������鼮����⿼��ʱ�����ڼ���˼·������൱���ġ�������㼯�ij����ģ������ⷽ�����dz��һ�ļ�¼���� �������ڡ��������ʱ������ڡ���ӣ�����һ�θе����֮�е��ǹ�ı��ˡ�����ѧ��ʷ����������������ũ������ָ��ܣ���Ϊ���ˡ��ĵ���Ӧ����������ظ��ܳ�������ũ��ɻ�������ڳ�������һ�����������ָ���Ҳ�����������˵���ز�����������ָ�����ͭ���������ܾ������������ûʲô��������������ص���֪�������dz��ܲ�����������˵�����ĵ������˵ľ��飬û�������־�����������ɫɫ�ġ���������ϣ�����ȴ�ѧ��λ�˿Ͻ��ڣ�����������Ӣ�������ˣ�����������ڵ���������������飬���������Ĵ�����飬���϶������ң��������������ʱ����Щ���ס����˵ع�ϵ�����ǿյġ�����ģ�һ�����Ļ�����ʷ�ľ��屳�����ں��� �������˽��й��˵������Ҫ�о��й������ĵ��������Dz����ܵġ������˽�һ�š��й��ġ���ֻ�����й��˵���֫�����Σ�Ҳ�Dz����еġ��й��˵���֫������׳��ȴ�ܴ�������ﳤ�ǣ�������Ҫ���й��ġ����й������棬�������ܲ����������С��������¡�����ââ���ݡ����й��Ŵ���ũ���������С�����һ�塱�ĺ�ۣ�����������������ġ���ˣ������й�������ʱ�������ĵ���������ѧ���в�С�����ۡ� �������������ĵ����������ܶ࣬����һ�������Ǵ�ǧ���硣���۹����ۣ���������Ļ�����ʵ��������ǣ��ḻ����������ı��ʣ�û��˭��Ψһ�ġ������ˡ���ֻ�л����������һ���������١����Ž����硣 �������������������ϴ�����⣬������ļ�����Ƕ�С�����¡���Ϊ�ҳ����е�������������̻�����Ҫ˵����������Ϊ������û�б�Ҫ�����Զ̻��Ͷ�˵�ɣ���ȶ̻���˵Ҫ�õöࡣ
�����塡������ 2003 �� 11 �� 28 �� �ڱ����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