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4.00Ԫ
A5����
ISBN 7-200-04305-2/I��667
|
|
����������"ʫ��"���������ڱ��δ�̳����Լ�į���������壬ί�����������һֱ�DZ��δʵ��������������ѧ�߶������Ժ��̳"ʫ��"����ķ�չ�ݱ䣬�����һ��һЩѧ�ߴ��ھ��δ�˼������ĽǶȳ��������������������š��������ԵĴ��������������������һЩѧ�ߴӷ���������"������"�ĽǶ����ۣ��Լ�����ͳ��Ĩɱ�����ʵ�Ӱ�죬ͬ����ʧ���ʡ���ϸ���챱�δ�̳�Ĵ������䣬���ܷ���������������ȥ��֮��������֮ǰ��̶̵Ķ�ʮ�����Ӱ����ʮ�ֹ㷺����Զ�ġ�
���ʮ�������ǻ�����λ�ڼ䡣���ڱ��˾���һλ�ܳ�����ѧ�ң�������������Ӱ���£���һʱ�ڴ�̳֮����Ҳ���ֳ����ִ������桢�ḻ��ʵľ��档���У������ʷ��������ľ�Ӱ�죬�����漫Ϊ�㷺����Ϊһ�ɲ��ݺ��ӵĴ����������϶��Ժ������ʷ类�����������ڴˡ����ǣ����ڻ���������"��ѧ"�ı����������ⷽ�洴��֮��ɢ���ǣ��ر����ڶ����û�б�������ݵȵ�ԭ��ʷ�϶���һ���մʵ�Ӱ�������Զ����ۡ����죬���ѧ���ѶԱ��κ��ڴ��˵���ƽ�ʹ���������������������Ѽ�������������������������Уע����ġ���ɽ�ʡ������������ġ��˲�֮�ʱ����ע���������������ġ����δ������ס��ȵȡ�ƾ����һϵ������ѧ���ɹ�����϶Ա��κ��ڴ�̳�����ſ����������գ��Ϳ��ԶԻ�������̳�ϵ���һ����̬����һ���
�����������ڻ�������Ӱ�죬�����������ǻ���������"��ѧ"�����⡣��͢�������������"��ѧ"�ڶ��̶���Ӱ����������ʱ����Ŀ�еĵ�λ�������������λ�����������֮Ӱ��Ϊʲô��Խ��Խ�㷺��
һ�����ε�����������Ľ���"��ѧ"
����������ʯ�䷨��������͢���γ��¡������ɵ��������Ǵ����ι۵㡢���е����ߴ�ʩ֮��ͬ�����ݻ�Ϊ���˶�Թ�����ն���ΪС��������˽��֮��Ȩ�����Ĺ��Ķ��ǡ������еĴ��Խ��Խ�пᣬ��ʹ�õ��ֶ�ҲԽ��Խ���ӡ���һ�����Ӳ��ϵĵ�������ب�����к��ڣ��·���һ��������ɱ�����ƻ���ͳ�νṹ���ȶ���"ʼ�Ե����ˣ����Ե��ܹ�"������ʷ����������ʮ��������������Ҳ����˲��ϵ����ִ��ͽ������ӵ�Ƶ�������ں��У���������������һϢ�����ڱ���������
��һ�����������������ִ����ڱ�������Լ����Ρ�����֮ʼ������������������ʯ���ڳ�͢��ȫ�����ֱ䷨�����Ա䷨�ij��������岩��������˾���⡢�����ȣ��ױ����ػ�������š���������������ţ�Ϊ����ͨ�У�Ǩ֪���ݡ����ݵȵأ��ȶ���"��̨ʫ��"������ݡ����ֵĵڶ��ζ�������Ϊ����Ӣ�����ţ�����������ʮ������ǻ���̫��̫����ϴ�������������ȫ�����þɵ����ż��µ���������˻ص���͢������Ҫְ�����Ϊ�ط���Ա��ʼ������̫��̫�����ء��ڴ��ڼ䣬�ɵ����µ����Ⱥ��Ѿ��ݻ�Ϊ��ԭ�������֮�����Ҷ���"������"���ݵȱ����ֶΣ�Ϊ���ڸ��ӿ��ҵ������Ⱥ����»���������ȥ�����������������ڷߺ����ڼ��Լ���ͬ���ܣ������ɵ��������µ����������ֵĵ����ζ���������Ҳ��������������һ�ζ��ˣ���Զ�����ϡ����ϡ��������������꣬��������ȥ����̫�����ϵ������£����ڵ��Լ�λ�������ڻ��ڵļ���£����ݴ�����������ʱ�����ֱȽ�ƽ�ȡ��ºͣ�̫����ʵ�����������ì�ܣ�����ľɵ���ʿ����Ǩ��ְ���������ڻ�Ǩ;��ȥ�����������ֵĵ��Ĵζ���������������Ѹ�ٸı�������Ŀ���Ծɵ�ʵʩ�˸����ģ����Ϊ���ص������Ⱥ����������ֵĵ���ζ�����������Ȼ�Ѿ�����������������ȴ��Ȼ��Ը���Ź���������ʼ����������Ϊ��Ӱ�����ȫ�����㡣
���һ�����ֶ����ľ�������Լ���"��ѧ"�������Լ�������ģ����ڳ���Ԫ�꣨1102�����£��̾����࣬�������Ÿ���Ԫ�v���ˣ���Ԫ�vѧ����ͬ�£�"��Ԫ�v��"�����£�"�����˱��ڶ�����"��"���δ������Ϲ���"��������Ϊ��������ʷ���±�ĩ������ʮ�š��̾��ù������������������£�"گ�ض�Ԫ�v��Ԫ��������а���ߣ���Ϊһ����ͨ���پ��ˣ���ʯ���á������������Ϲ���������ʮ���ˡ�"����������ͨ��������ʮ�ţ�����ȫ�������ؽԿ�"���˱�"���䲼���¡����ǣ���"��ѧ"�Ⱥ��������ĻҲȫ�������������������£�"گ��䭡����������ޡ���ͥ�ᡢ���硢�˲�֮���عۡ�����ļ������������Ƽ���������ի���¡�������ʫ����ɮ��Ө����ɽҰ¼���ȣ�ӡ��Ϥ�зٻ١�"����������ͨ��������ʮ�ˣ����ң�"���±��ٰ�ϵ�������ߣ���һ�����١�"���������ܸ�ի��¼����ʮһ������������������꣨1124������͢����������������������ļ��Ľ�����ķ��֮ͽ��Ͷ�ʵ��뵱�������ã�Ҳ����͢���ԣ��������ϡ����岨��־�������أ�
�����ܳ�����Ӣ�ࣺ����Ӧ�������������̣���һ�����١�گ��֮��ʱ��������Ҳ�����꣬�������У�˾ũ����گ��Ԫ�v��֪���ݣ����¼鳼������������ŷ������������ͤ�ǡ����ؿ���ʯ���Զ�ȡī����Ϊ֮���ţ����ù�ʹǮ��گ�����Ӣ�ų����꣬������Ӧͬ�ơ����ͼ䣬̶�݂y�Ͻ���������Ԫ�v����·����������֮��
һʱ�䣬��Ұ̸"��"ɫ�䣬����"ƽ�����¿ͽԻ�����䣬Ω����֪֮��"���Զ�����������ʿ��������ʮ�������Ӹ������������������͢�Ľ���ƺ��ӿ���������"��ѧ"�Ĵ�����ǣ�۵����Ƕ������ķ��ѧϰ��ģ�¡�
�����������"��ѧ"�Ĵ�����Ӱ��
���ǣ�������ʵ���У���ֽ������ȫ������������Ŀ�б��ܳ羴��������Ҳ���������������ڱ�����̳������Ŀ����ˡ������Ի��������̳��Ӱ�죬���Զ�����ȴ�����ڡ�����ʫ�������ڱ��κ��ڼ�����������������Լ����������ԭ��
��һ��һС���ֶ�����ֱ�������ӵܺ�ʿ��������Լ���������Ʒ�����µľ���֮�飬���ǶԿ���͢���Ļ��������ѧϰ���м������ķ硣����������Կ��ɣ�Ϊ�����ṩ��һ�鴭Ϣ֮�ء�����������������֮����Ϊ��Ϊ��ǿ��������䣬��֮��������أ�����������������Ȼ������ԡ��Զ�������˵��"�����֮ͽ��ʼ�ղ��������������ߣ��Dz��������ˡ�"���Զ�����������ʿ��������ʮ�������Ӹ�����������������Զ����������й�ʫ�Ľ��������������������꣨1121�������dz�͢��������������ڼ䣬���ԣ��Զ�������֮�ǵ����ͣ�ͬ����ӳ������ʿ���������ij���̬�ȡ�"������ѧʿ"֮һ�˲�֮���ڻ��ڼ�λ����֪�������ŵ���Ϣ��������ʹ��˵��"����뺣��������������ർ��ӣ���ľ��ݣ�"��������������ʮһ���������չ��ġ���������䵳�۸����˲�֮�������������ݹ�������Ȼ���⣬��������ͬ�����ۡ�"������ѧʿ"�е���һλ���磬"ʱ֪ӱ�ݣ������䣬����ٺ�ڼ���������������ʦ��֮�����������У����ڷ��ݱ�ݣ����ݰ��á�"�����岨��־�����ߣ�����������Ϊ"���硢�ع�֮��"����D��Ҳ���ļ�����˵��"�����������һ������֮�ģ���ɽ�������Ӣ��֮����"������ʷ�����İ���ʮ�ġ���D������������䣬��D������ȡ�����ӳ��磨�ڽ���ϳ����أ�������ʱ��"������Ի�쳣���ֽں�˷�������Ȼ������ʱ��Ȼ������ʱ���졣"�쳣�н���ʫԻ��"�ʸ�����ʦ���Σ���������ѧ����"�����Hʷ����ʮ��������ʱ����һλ����ʫ�������ϣ���������ʫ������͢��ּ���ٶ�����֮���ٰ��һ�£�Ի��"�ʵ�쫷紵�����������������Ұ���ʮ��ǽ������ζ��ٖ������Σ�"���������ܸ�ի��¼����ʮһ��
����ʱ�����������羴�����ת��Ϊ������Ů�ĺǻ�������֮���չ�����ܻݲ��١��������¼�������أ�"���嵳�Ե�������ӱ�������ޑl������������ʿ����ֲԪ�������Ľ�壬��һ��֮���سٻ���ʦ���ɣ��������������嵳��֮������ĩ������Ϊ����Ծ�ʦ�����Է��嵳��������ί���嵳����֮��磬���������֮�������뾳��������ʣ������Դ�"��֮�����ϱ���֮������Ҫ���ˣ��ʷ���������Ӱ�졣
�ڶ��������Լ���Χ�����š�����������ϲ������ʫ�������ߣ��ڲ�֪������ͬ��������������Ӱ�졣���������������Ȼ������һ�ݶ������ij羴֮�顣�������ζ�������Ҫ��������������"Ԫ�v֮ѧ"�����־�����Ϊ��û�������õ������Լ����ĵ���ͬ�����ԣ���ʵ�ʲ����У���Щ����ʹ���û�б�����᳹ʵʩ����Ҷ�εá�����¼���������أ�
���ͼ���в���ʫ�ߣ�����ʫΪԪ�vѧ���������С�������Ϊ��ʷ��������ּ������������Ԩ������Ŷ��£��Ա�֮����ڮ��³ֱ������DZ�����̡������εȣ���Ϊ���ơ����£���ʿ��ϲ������ʫ����Ϊ�衣�Ժ�ة�����ǰ���첻���ͣ���گ�飬��ʾѵ�롣�������궬��ѩ��̫�ϻ���ϲ�������¾Ӻ�����ʫ��ƪ���ף�ν֮�ںţ��Ϻʹ�֮������ʥ��ʱ���������ܽ���
����ʫҲ����Ԫ�v֮ѧ���Խ�����δ����ơ������Լ�����һλ�Ż����ڵ�ʫ�ˣ�ʱʱ����"����"�������߳˻�Ͷ�����ã�����ͳ�Ϊһֽ���ġ�
��ϸ�������������ڱ���Ҳ��Ԫ�v֮ѧ�и�ϵ���ϵ�����ڳ���"������ꡢ���Ҵ�����������������߽������Ĵǣ���ͼ�������������ƻ�ͥ�ᣬ�ʵv�꣨���ڣ���ͥ�����壬���Գ�һ����"�����С���Χɽ��̸����һ����������������ԭ��һ�ݼ��ߵ��츳���ա���֮����Ϊ������Ʒ���Ի��ڵ�������Σ���ȻҲ����֮����
��
����ϲ����ѧ�����Ž����ж�����֮ʿ����ѧ�̳���������������Ӱ���Ϊ�ձ顣�����м��û������Σ�������У̫��������������Ȼ��������ʱ��ʦ��������������������»¹���ʦ�ɡ�Ȩ������Խ��������ܣ���"��ʫ�ķ������أ��IJ�����Ϊ�ˡ�"�����Ŀ�ȫ����Ŀ��Ҫ����弼���Ҫ�������γ��ܱش�Ҳ����˵��"ʱ��������ѧ�������������У���DZ������Կ��"����������������Ϊ"��ѧ"�ijм��ߣ�"�ơ��š��ˡ��ؼ�û��ϵ��ͳ��������˭�����ң���ֹϮ���塢���价���ѡ�"������弼������ס�������Է���ԡ�Ҳ��ͬ�������ۣ�"�����䣬���ջ�֮ѧ�����ְ���֮����������ö��£����Ӳ���ѧɽ�ȡ�"��ת�������ۡ��Ž�ʻ����Ͼ�����һλ��û��ڻ��ĵ���ѧ�̳����飬���Ӳ�ѫ��˵��"����ν�ȹ�����������ʷѧ��"��������������ʮһ��Ҳ����˵����������������Ҵ�����Դ�Ϊ�٣������Լ�����Ů��������䣬���������������չ��������й�����ϵ����ѫ�ع�˵"�����䣬�������嵳�����������ơ�"����������������ʮ������ԨԴ���������������Բ������ʶ������Ĵ�����Ҳ��Ȼ���ܵ�������Ӱ�죬������������Ʒ������˵��"��Ԫ��÷��'����һ֦б��������캮��ĺ��'�ö���'����һ֦б����'֮��Ҳ������ʱ����ѧ��Ԫ���ֽ��ҳ����������վ䣬����ν�ڶ������ߡ�"��ʹ��������Ż�Ԫ�v����������Ȩ��̾�������Ӳ���Ҳ���˸�������Ȥ������������ʫ������"������������ͥ��֮˵"�����λ�Ҫ���塤ְ�١�����֮һ����������Χɽ��̸��"����Ԫ�v����������һ�����֮�䣬�����丸��Ȥ���������ȼ����Ƴ硣"�����Ŀ�ȫ����Ŀ��Ҫ����Χɽ��̸��Ҫ����
��������ī������͢��ν����ٻ٣�����ϡΪ�������۰ٱ�������û����ڸ��¹ٵ�ϲ�������Dz�ϧ�ؽ����Ѽ��������ķᡣ����侼��š�������������ʵ���أ�
������ī֮��Ⱦ���������۷ٻ�֮�࣬�˼����أ���һ����Ҳ�������ͼ䣬�ڸ������ѷã�һֽ��ֱ��Ǯ������ʦ��������ǧȡ�����ˡ�Ӣ��ʯ��������̷��������Ǯ���Ԫ��"������"�������֡��������ˡ��������ش�ֽ����Ϊ���գ������������������������ϡ������꣬���˷��ڣ����˶�������������һ��֮��Ҳ�������˳��������й���Դ�ң��������ؼ������ᣬ������о����֡�
���ڳ������DZ�����Ϊ����ʵϲ�á�������ͬ���ѽڣ�Ϊ�����ķ�������������˿����еĿռ䡣��͢�Ľ�������ǻ��ھ����Լ��ƻ��ġ�
���������κ��ڣ���Ұ���γɶ������ij��֮���������ʹ��������Ӱ���������ġ����岨��־�������أ����ڼ�λ���꣬�����Ժ��ϱ���"�����꣬�����С�ڣ�����������У����˺�ǧ�������֮���¹�����Ի��'Ī��ɱ�ҷ�'"�����ַ��������ڻ������������²㣬��Χ�ų�͢�ľ����ߣ�Ӱ�������ǵ��жϾ��ߡ�
���γ������䣬����Ϊ�����ԣ�ִ��̳ţ�����ܵ����ײ���ձ��ݣ����ѳ�Ϊ��������һ�������ͷ��С����ֳ�ݺ��������е����ƽ���"����"�ij��ԡ��������������˸�ľ���������һ��������������ġ����ײ�Ի�����䳯���ڰ����ܵIJ�����ʹ���ǶԳ�͢�Ľ������һ���淴�������������ļ�����ݾ������ǶԿ���͢��ij�ֱ��ַ�ʽ������������"��ѧ"��Ȼ"�ĺ�����Ľ���£��Ի�������֮��"
����ʫ���ڵ�ʱʿ����м���Ȼ����ʢ�У��ﵽ���������ĵز��������Թ����ķ�ʽ��������̳�Ĵ������������Ƕ�������ѧ������ϲ�����Ѿ��������Ը��ӵĵز������͡�������ʫ����˵��
��������ۼ䣬���º���ʫʢ�У�������������ŷ�����ޣ����ߡ���ʱ����͢�䳢��ֹ����Ǯ������ʮ�������Զ���䣬ʿ���������ʫ�ߣ��Ծ����������˻�ν֮���ϡ�
���������������̳������Χ�£����̾����ж����������ij���ߡ��������ŵ��̣����е�ʿ�������ԡ���������������أ�
�տ�������������һ�գ�������֮�����ʿ���£��ö�����������ʣ���Ի��"����������ֵ�������·��ϣ�ʼ�"����Ի��"������"��Ի�"����������Ҳ��"�ϴ�����ʹ����֮�����Բ��롣
��λ��ʿ�����������ij���ߣ��ʽ��װ��Ū�����Ըı���ڵĿ�������Լ����������������Χ���ǵ�Ӱ�죬����ʼ�նԽ���Ԫ�vѧ������Ԫ�v���˱�֮���㷲������������꣨1106�����£�"����������䳤����"������"���DZ�ܵ����ţ�گ��ֱ�ԡ���������Ԫ�v���˱���������а��֮�����۴�֮��ҹ��Dz���������û�ʯ�̡�"������ʷ���±�ĩ������ʮ�š��̾��ù�������Ԫ�v�����У�����������������������Ҫλ�ã��ܵ�������Χ�購�Ĺ�ע����Ȼ�̾�ʼ�ս������������ж�����ά�������ĵ����¹�Ҳ�������������ڵij��Ż¹ٸ�ٴ"����������Сʷ�������Ĺ�"���������ʵ�"�ų�֮������������Ǩ��"��"Ȼ�������ϣ�ÿ���ӵ��붼��������������ڡ�"�������塶�����¼�����ߣ�������Ҳ����ά������һȨ����ʦ�ɣ��ɴ��ʸ����ϣ��������������ӣ���Ϊ������ԩ�����ڻ���˵��"�ȳ����""���ǣ���֮�����Գ�"������ʷ�����İ���ʮ�ˡ���ʦ�ɴ���������ʦ�ɵ���Ϊ�������ݼ�Ԫ�v�����ӵܣ����붫Ұ������أ�"����ʦ�����£���ν�������壬������Ԫ�v�����������¡���տ֮ͽ��"�����ܵ��������ŵ���Ⱦ�ˣ���Ԫ�vѧ���Ľ����������ȴ��������↑ʼͻ�ơ�
�²�ʿ�ӡ����գ�������͢��Ϊ���Խ���"��ѧ"�ĵִ������������Ǹ�Զ���뿪�����������ģ�����ν���˻�ٳ���ʧ�����Ը������ɵر����Լ�����������������ж�������Ϫ��־�������أ�
���ͼ䣬��������������ϡ���ʿ����Я�¼����ǣ�Ϊ��������ִ����˾����������һʫ�ƣ�"�����䴦�����������������������á�����ٴ�����̼���Ҧ�硣�˼��������������ں���ʶ�ŷ硣ƽ����ƪ˭��ϧ��������ʰ��ң����"���������ˣ���η�ۼ���������֮��
���������¼���������أ�
�Ž��б�����������������������̫ʷ��ͥ�ᣩ�����Ի"����"����������گ������Ԫ�v����������̫�غ�����ʹ��֮������Ի��"С�˼Ҿ�ƶ����ֹ������ں�����ѧʿ�ʺ���������ů�������Լ���Ϊ�����ϲ������֡�"����֮��Ի��"���գ�ʿ���֮������Ҳ��"���Ծƶ������롣
�������֣���˵�������ڵ�ʱ����֮¡��ʫ������֮�㣬�Լ������ײ�Գ�͢������ձ�ִ��������������£����ǿ�ͷ��Ӧ������һ�ף�������������ʵ��������һ�ף����������������֮����"��ѧ"�ѳ�Ϊһֽ���ġ����ڽ���ķ���̼���������ʹ����ʫ�ĸ�Ϊ���У������ձ�ײ�Ļ�ӭ�����ԣ������Ի��������̳��Ӱ�죬Ҳ���ӹ㷺���������ġ�����"ʫ��"���¶Ի��ڴ�̳��Ӱ�죬�ͷ�����������������һ������Ļ�����֮�С� |
| |
|
|
|
������ ���رմ��ڡ�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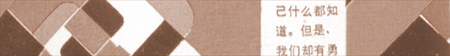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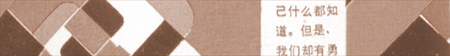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2912896
010-62912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