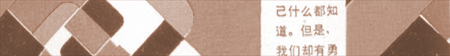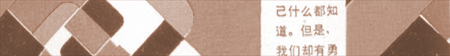1970年代的军营胎记——读何亮长篇小说《兵词·1970》
陈可非
小说是时代的胎记。这是小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一部分,也是小说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据说一个人的胎记乃来自复杂的基因,其本身便像是一个深邃的寓言,隐含了某些有趣而费解的秘密。何亮的长篇新作《兵词·1970》(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就是这样一部堪称为时代胎记的作品。它截取的是1970年代的中国军营这个横断面,展示了这一特殊群体在特殊年代里更为个性和异趣的一面。因为在那个年代,军营在整个中国来讲,是极具特定意义和代表性的。
让人放心不下的结构?
早在十多年前,就听说有老外写过一本叫《哈扎尔词典》的小说,而真正知道这部作品还是在韩少功《马桥词典》出版引起纷争以后。原因是两本“词典”都采用了同样的结构,把小说按词条写,因而引起了一系列争议,有人认为韩少功是在“抄袭”,也有人甚至从根本上否认这种小说文体。口水官司打了几年后不了了之,想必此后再不会有人敢用这种文体写小说了。
可是,事隔几年又来了一人,仍要把小说当词典写,或者说把词条编成小说,这人便是何亮。他为何会这样固执,难道他不怕别人也给他扣上“抄袭”的帽子?他真有这么自信?他这样做总让人有些放心不下。
这些顾虑只有在读过文本之后,才会一一消除。我们看到,一部作品的结构全然是天定的,绝不随作者一厢情愿。何亮对于他的故事为何选取词典方式来叙述,只有在解读作品中,才能得知其良苦用心。这与其说是受前面提到的两部作品结构的启发,毋宁说是在比较或尝试各种方法后必然的取舍。这种剔除了一切铺垫和杂陈的简练方式,让人更加清晰地感到那个逝去的时代留给人们的心灵印记,同时也隐喻了无论多么复杂、热闹、荒诞和光怪陆离的时代,最终写进历史的无非就是那么些简单的词条而已。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比起《哈扎尔词典》和《马桥词典》来,何亮的处理似乎更具理性,仿佛真的是在做一种学术研究而不是文学写作了,但在看过那一篇篇简洁的故事和听过那些颇具哲学味的分析论述后,我们仍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尤其是,他们深奥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作者在自序中说,“实际是把自己由切身经历而来的一些体会奉上,与军中战友和对军营习俗感兴趣的朋友做一次心灵的交流。也算是用这种方式,记述一段在某个视角上才能看到的历史。”读到这些,我知道了自己担心的多余。词典式的小说结构仍有相当的发展空间,相对于前人已有的类似尝试,何亮恰恰做到了避其所短而扬其所长,让结构完全为内容服务,与内容相得益彰。
虚实之间的文化暗示
也许只有经历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人,才能对作品中列举的诸多词条耳熟能详。比如“忆苦思甜”、“斗私批修”、“引路发言”,这些在当下人看来近乎笑话的词语,在当时却被人们一丝不苟地实践着,而没有多少人敢有质疑。作者自己显然也曾虔诚地参与过这些实践,并将其情其境尽量忠实于原貌地传达出来,为的只是向后人提供一面镜子。是时代造就了这些特别的词语。《兵词·1970》整部作品分三个部分来叙述,即新兵伊始、连队轶事、球场日子。从层次上看,这既是作者人生经历的记录,也是其思想成长的写照。正是在这逐渐成熟的进程中,完成了他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和认同,或是质疑和不认同。在《班长》一节中我们看到,“当了兵,见到老兵就得叫班长,这是规矩。”然而,“这个‘班长’却是虚称,相当于承认你在我眼里是‘班长级别’而我只是‘新兵级别’,这跟白纸黑字地被上级任命的班长是两码事。”看似闲淡的叙说,说虚道实之间,却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军营文化的微妙影响。有些“虚”的背后,其实正隐藏着一个更高层面的“实”。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班长”称呼在军营里实在是太流行太普通了,也常有些认真的人士撰文强调应严格按条令规定有关称呼,不应滥叫“班长”,但从来就没有奏效过,却没人认真剖析过这背后的文化原因。还有像《鼓掌》、《比喻》、《典型》、《偷窥》等看上去没有一点奇特的词语,在这部作品里都具有了全新的阐释,产生了与词语自身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的意义。这一切却决非作者杜撰,而完全来自他对军营文化的的仔细观察和深入理解。
在许多章节中我还发现,作者的叙述中还随处夹带了那个年代的另一些特殊“词语”,但不知为何没将它们单独成篇。如《广播》一节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部队基层的思想政治教育,讲究的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除了能占到正课时间一半以上的政治学习和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以及‘雷打不动’的‘天天读’之外,连吃饭的时候也不让人消停——嘴巴可以占着,耳朵却不让你闲着,有人会利用这时间讲述学习体会,表达班组决心,宣传好人好事。”这就是“连个话筒和扩音器也没有,只凭了念稿人的嗓门儿高声朗读”的“饭堂广播”。作者对新兵们为了表现自己的进步而“争夺广播权”的场面描写相当生动。但是,既已提及,却没把“早请示、晚汇报”和“天天读”等列为词条写出,让我觉得不无遗憾。当然对故事性和生动性的考虑或许影响到了作者对词语的取舍。这是该书和前面提及的另两部“词典”的不同之处,也正因如此,《兵词·1970》所选“词语”大都是紧扣住人物或故事,能比较典型地反映那个年代的军营习俗的。一些未加“注释”却也属于那个时代的“词语”,虽令人不无遗憾,仍起到了一定的烘托作用,共同寓示着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文化。
零碎背后的哲学整合
初看《兵词·1970》,其故事是零碎的,甚至有时觉得其主要人物都不明确,这跟何亮过去的作品大有不同。但细细地回过头来品读时,才发现这些被砸碎于“词语”中的故事,具有的是实质性的完整概念。通篇中人物纵横交织,形成了一张斑驳陆离疏而不漏的网,而“我”显然是这斑斓大网的主纲。每个词语背后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有不同人物,而“我”一忽儿是故事的主人公,一忽儿是讲述者;一忽儿是以新兵身份在惑然慨然,一忽儿是用作家话语品评反思。如此这般反反复复,使这部作品平添了扑朔迷离的色彩,使人已无法认清其人物的真实身份,分辨不出哪一个才是作者自己。然而就在这样的似真非真、亦实亦幻中,却让人真切体验到了一种情感的深刻,感受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这样的方法,与米兰·昆德拉不无相似,那些看似与现实无关的人物和事件也来到了作品中,只有细心的读者,才知道这些人和事与作品不可分割的关系,才会发现故事背后隐藏的哲学意味。这有些像中国功夫中的醉拳,看似随意,狂放不拘,其实每个细节都决非妄加,背后更是相当的功力,
《兵词·1970》说的是三十年前的故事,真正揣摩起来,它其实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胎记,而是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它更像是一串串解读古今兵文化或揭示世风民俗谜底的钥匙,或至少是一条条有相当价值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