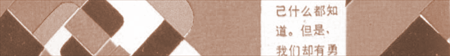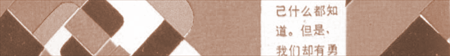|
碰撞与交融:奥林匹克与近代中国
1894年6月23日,这是世界体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努力下,与会的12个国家79名代表在法国巴黎,一致同意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并决定将国际奥委会总部设在巴黎,规定法语为法定语言;推举希腊诗人维凯拉斯为国际奥委会第一任主席,顾拜旦为秘书长;产生了第一批共15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召开了首届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会议决定轮流在世界各个城市每四年举行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同时决定首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希腊的雅典举行。从此,一个规模宏大的以体育为载体的国际社会文化运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正式诞生。如今,它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成为凝聚着人类社会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经验精华的知识宝库。而随着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传入古老的中华大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也逐步融入中国,并不断地与中国社会在多种层面上发生碰撞和交融。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接触或联系是很少的。体育也是一样,它是分散的、民族的,没有“世界的”概念。然而,自从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之后,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大工业的出现,以及它所创造的近代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以及文化,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所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姿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由此,世界各国或民族的体育,也都开始从不同的起点和角度向世界聚集。而作为西方“精神产品”之一的奥林匹克运动,也正是在这一社会条件下,逐渐演变成了世界性的“公共财产”,并逐渐居于世界体育发展的主导地位。
前言碰撞与交融:奥林匹克与近代中国奥运来到中国这个世界有了资产阶级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世界性的统治者。在世界体育文化领域中,同样反映了这种世界性的主属关系。即宗主国体育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体育的关系。看一看中国近代体育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说,它正是中华民族脱离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及闭关自守的孤立姿态的体育,向“世界性体育”转变的历史,也是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日益对接的历史。
同许多被压迫民族一样,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这种体育向“世界”的转变,以及和西方奥林匹克文化的对接,应该说也是从被动和主动两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传统,使中国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身份归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人通过“睁眼看世界”,看到了近代西方体育所具有的那种进步性和科学性。比如,无论是瑞典体操还是德国体操,或是欧美的田径与球类运动,它们都与自然科学,如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等密切相关,并以近代自然科学为主要理论基础;比如,近代西方体育一般都有着较为科学、完整的活动规则体系,这无论是在运动竞赛工作的组织方面,还是在具体的运动活动中,都表现出一定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又比如,近代西方体育具有较强的竞技性、趣味性、娱乐性,这特别表现在球类和游戏项目中。所有这些,既表现了近代西方体育的先进性,也是它富有顽强生命力的主要原因。因而它为世界上许多民族或国家所承认和吸取。
宋太祖蹴鞠图
处于落后条件下的中国也不能例外。这一促使中国体育向“世界”转变、与西方奥林匹克文化对接的被动过程,尽管对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来说,可能有些不情愿,甚至痛苦。因为在漫长的岁月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各族先民,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璀璨的古代文明,其中包括中国古代体育。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在山东的临淄城就开了世界足球运动的先河——蹴鞠;在秦汉三国时期又出现了相扑活动,甚至有女子相扑;盛唐一代,马球运动更是风靡全国,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纷纷参与其中;明清时期,又有了独领风骚的中华武术,并出现了像少林寺、武当山那样驰名中外的武术圣地。但是,当14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和后来的思想启蒙运动,把黑暗的欧洲推进到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时候,中国则从封建之巅不断地向下滑行,最后落后于欧洲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乃至到了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落后并开始认真地向西方学习。这其中包括对近代西方体育的引进、学习和模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极不情愿地退出了在中国本土的主流发展地位。即使像中华武术那样的民族瑰宝,在近代西方体育的冲击面前,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发展道路,考虑怎样地自我改造、与时俱进。
唐章怀太子打马球图另一方面,中国体育在向“世界性”转变,与奥林匹克运动对接的过程中,也有着主动求变的一面。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种主动求变主要表现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潮流的冲击,使沉睡的中华民族不断觉悟并激发起他们也要努力走向世界的自觉要求。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不得不变更祖宗之法,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有关中西方之间的文化直接接触,应该说早在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就发生了。那时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资本主义早期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例如钟表、地球图、日心说、天主教,等等。但东西方文化之间并没有发生尖锐的冲突。清朝皇帝的一纸诏令,便可以驱逐传教士,毁弃天主教堂。而刚刚起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大清帝国的所作所为也无可奈何。当时的清朝还算是强盛的、自信的。但1840年的鸦片战争却最终打破了这种格局。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抢夺中国市场,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而借鸦片问题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如果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来说,则又可以被理解为是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文明,对落后的封建主义东方文明的冲击。这是两种文明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这两个世界的对峙中,除非旧世界能面向新世界,主动接受西方的文明,并以此来对付伴随先进文明而带来的邪恶。否则,先进的近代文明战胜落后的古代文明,乃是不可变易的社会规律。尽管这种古代文明的代表,有着正义的目的以及种种的痛苦和血泪。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正视现实,“睁眼看世界”,并在比较中鉴别和认知西方文化的长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从中寻找出救国救民的道理和途径。于是“救亡图存”,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最强音。要救亡图存,就必然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因此,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独立、民主、富强,便始终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而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近代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也同样是围绕着这一历史发展的主题而展开的。
翻开中国近代的历史,早在清嘉道时期,西方殖民势力就已汹涌东来,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在科技发展水平、军事力量、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就已经拉开。与之相适应的是,西方侵略的威胁也日渐加剧,特别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英国扩大对华侵略与中国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在此背景下,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清廷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利处境,他们深怀忧国之情,想方设法了解世界形势,以图从中找出防范和摆脱民族危机的对策。其中,有提倡“通经致用”的学者、进步思想家龚自珍,他提出了“更法”的见解,主张要留意于“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有坚决反抗侵略,并注意了解外情、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他主张要“向西方学习”。尤其是爱国进步思想家魏源,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编成了《海国图志》一书,更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魏源所说的长技,并不仅仅是指武器装备,还包括了军事训练等多种内容。他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2]正是从练兵之法里面,我们不仅看到了军事训练的内容,而且还看到了体育训练的内容。而当时的体育训练内容,主要就是采用西方的“兵式体操”。所以在我国近代体育史上,尽管一般认为是洋务运动最早在编练新军中引进了西方近代体育,但最早提出这一要求的则可以追溯到魏源。
魏源图
如果说魏源还只是从理想的角度,提出要注重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包括体育的话,那么,后来发生在清政府内部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则是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开始了对西方近代体育的吸收和引进。大概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就开始编练新式军队,以洋操、洋枪、洋炮为主要训练内容。最早对军队进行西方兵操练习的是曾国藩的湘军。有资料表明,在湘军中很早就有每天早晚各做一次体操的要求。“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日斜时演晚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在湘军的日常训练中,跑、跳练习和操练洋枪也都是一些固定的训练科目。据《曾文正公·杂著》卷一“晓谕新募乡勇”载:湘军中每逢一、四、七日午前,均有抬枪、鸟枪的打靶训练;而逢五、逢十日的午前,则是演练连环枪法。[3]每逢二、八日午前,湘军的将士们则要到城外的近处,集体练习跑坡、抢旗、跳坑等类的身体活动。
洋务派新式军队中的兵操训练,一方面是从英、法、美等国的军队中,聘请军官充任兵操教习;另一方面也派人出国学习,以培养自己的兵操教官。如李鸿章在整顿直隶的防务中,曾于1876年选拔年少力壮的中下级军官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1879年学成回国后,他们即以德国兵操训练淮军。
洋务派还先后创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等。这些学堂大多依照外国同类学校设置课程,并聘用外籍教员。其中也设置了较多的体操课程。1894级水师学堂学生王恩溥先生曾在1985年的回忆中说,当时北洋水师学堂的体育课内容,已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比赛、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杠、双杠,及爬山运动,等等。北洋水师学堂最初所学的是德国体操,主要演习方城操和军事操,后来到了戊戌年间,又开始改为学习英国体操。
戊戌变法运动是发生在中国近代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因此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虽然戊戌变法运动不过百日便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所镇压,其实际的改革也非常有限,时间也极短,但它却有着巨大的思想解放的历史影响,对促进“西学”包括西方近代体育,特别是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和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已经能从学校的教育内容上,注意到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的多方面培养。他在《大同书》中说:“本院凡弄儿之物,无不具备,务令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为主。”在他所办的学校“万木草堂”的教育活动中,“体育亦特重焉。”还有梁启超,他则提出了“新民说”,即培养一种具有特色的国民。这种国民应该体现出“民德、民智、民力”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严复则公然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观点。他在《原强》一文中指出:“教人也,以睿智慧,练体力,励德行三者为之纲。”他从强国强种的立场出发,甚至认为:“民之手足体力”,关系到“一国富强之效”。
由上可见,无论是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和传播,还是后来的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都是在当时社会政治变革和救亡图存的影响下而进行的。所以,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一样,中国近代史上体育的发展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传入与传播,也始终都是围绕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而展开的。
所谓近代体育,从本质上看,应该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但从形式上看,它则是古希腊、罗马体育思想与方法,并结合中世纪骑士教育与贵族教育所孕育出的一种混合物。它是14世纪以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资产阶级取得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里对封建文化的决定性胜利的过程中,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身体文化。
近代体育最早出现在学校。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产生了对体育的新需求,身心全面发展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理想,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的教育体系和禁欲主义的身体观,在复兴古代体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萌发了新的体育思想。大约在16~17世纪,西方的贵族教育开始脱离旧的传统,不但文化学习的内容得到更新和扩大,而且体育教育也受到重视。年轻绅士必须身心并重,使自己成为人才。一切能使他们适应和平或战争时期积极生活的身体运动形式,诸如剑术、骑马、打猎、网球、跳舞等,都是日常的训练科目。在这种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人,已不再是旧式的封建贵族,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新贵。
在世界学校体育发展史上,使学校教育冲破贵族的狭小天地从而奠定近代学校体育基础的,是宗教改革时期捷克伟大的教育家夸美纽斯(JAComenius,1592—1670)。他是新教(捷克兄弟会)的著名活动家,曾在捷克、波兰、瑞典、匈牙利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主张普及教育,重视人的现世生活,关心人的健康和幸福,称学校为“造就人的工厂”。他强调教育的作用,认为品德、体力和智力的缺陷都可以由教育而得到发展。他提出了“适应自然”的原则,希望按学生的年龄及其已有的知识循序渐进地指导,主张“人人都应该祈求自己具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存在于一个健康的身体里面”。虽然他从未单独提及体育课程,但正是在他的教学计划中,体育首次成为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夸美纽斯确立了班级制和课间休息制,采用了直观和示范教学法。他规定低年级学生每日学习4到6小时,每学习1小时即休息半小时。青年每天须有8小时用于吃饭、操练和娱乐,通过郊游、旅行、游戏、跑跳和球戏等,而使身体活动,让心灵休息。他同时指出运动要有一定的节制,反对从事一些他所说的“危险”运动,如角力、游泳等。他还很重视体育和游戏活动中的德育、智育教育。夸美纽斯作为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位体育和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所以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学校体育之父”。
进入19世纪后,源于学校的近代体育首先在欧洲的德国、瑞典、丹麦等地,开始逐渐向社会和军队传播。当时广为社会和军队接受的体育内容,主要是那些能直接发展各种身体能力和加强组织纪律性的体操以及户外运动。
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输出逐渐成为扩张的主要方式,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色彩开始减退。同时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和元素周期律的提出,带来了现代科学的全面、长足的进步。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的各种体育竞赛活动开始增多,早期的体育运动组织也开始萌生。如1858年,全美棒球协会成立;1863年,英国足球联盟成立,等等。这些全国性的体育协会组织成立,不仅使原来仅限于学校或俱乐部水平的体育比赛活动获得较大的提升,而且还直接导致了各种相关国际体育组织的诞生。如较早成立的国际体育组织有:国际体操联合会(1881年)、国际橄榄球协会(1890年)、国际赛艇联合会(1892年)、国际滑冰联合会(1892年),等等。
国际体育组织的建立,不仅更加促进了体育竞赛活动的兴盛,促进了体育运动技术的进步和体育竞赛规则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引发了体育的国际化趋势,促进了体育的国际交往。而正是这种国际体育交往,才有可能将西方和东方、强国和弱国、宗主国和殖民地联系在一起。于是,一个宏大的现代国际社会文化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不仅借此而产生,而且也借此一步步走向了全世界,走进了古老的华夏文明。
所谓中国文化,准确地说应该称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这一概念,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如果从层次结构上看,我们认为,它似乎应包括中国历史上先民们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观念的全部。从内容上看,当然也应包括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等。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并不是指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所有文化,而主要是指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形成的、至今还在对我们发生着影响的文化。所以有人将它称之为“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化长河中,中国文化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想打破并代替这种文化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英国传教士杨格非所描述的:这里(中国)的人们通晓他们自己的文学。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们对这些人有好感,把这些人当做神明崇拜。中国人还沉浸于可以感触到的唯物主义世界和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段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而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 应该说杨格非所说的情况基本上是真实的,但这并不代表说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是一切排斥的。事实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也有包容的一面。当然这种包容是在不影响中国文化的内核,并有利于其再生与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同样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这种开放性首先表现为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一种吸纳态度。从历史的发展看,中华民族从来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例如从公元1世纪开始的印度佛学的大量输入,并没有置换儒学的统治地位,反而逐渐促进了儒学的新生。宋明理学正是在吸收了佛学的许多精华后才使儒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正是由于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所以当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尽管它闭关自守的大门是在不情愿的条件下而被外国列强所打开的,其所发生的社会变革也不是源于内在能力的觉醒,而是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不是一个和谐的成长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受挫不断调整的过程。但是它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则依然表现了一种泱泱大国的博大胸怀。所以当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的时候,马上就有了认同的知音:“中国何时能参加万国运动会,又何时能使万国运动会举行中土?兹值南洋赛会之时机,爰邀集全国体育家,订期9月15日,齐聚金陵,开第一次中国运动大会。”这是1910年8月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在南京召开“全国运动大会”《通告书》上所说的一段话。这里的万国运动会就是指奥运会。这次活动被认为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最初尝试。实践证明:充分地吸收外来文化,不仅不会使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中断,而且会大大地促进中国自身文化传统更快、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其次表现为它对外来文化的一种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许多的冲突。如:二者所依存的社会环境不同,一是工业文明下的文化,一是农业文明下的文化;存在着思想理论基础的不同,一是以西方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文化,一是古代东方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文化。但是,这种冲突并没有影响东西方文化走向融合。这种融合的基础便是中国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而“文化传统”是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向。中国文化正是在结合时代精神的文化流向中,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通过不断地寻找相互共同的契合点,而促进外来文化在本土的生长、发育,并最后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体系。例如,中国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上,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促进世界和平”找到了契合点;中国文化提倡的“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公平竞争”找到了契合点;中国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更快更高更强”找到了契合点。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成了奥林匹克运动能够在中国传入和传播,并最后走向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文化基础。
注释
[1]《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
[3]其法为6人一组,两人一层的立体式放枪法。即6人中两人取卧姿、两人取跪姿、两人取立姿,然后6人同时放枪。放完后,左人左后转,右人右后转,至队末。第二组6人前进一步,再放枪。以此类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