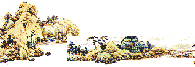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ǼǺţ�21-2001-A-(0656)-0115
|
||||||
�Ź�Դ��֪�Źⴺ���˹��縱��ǣ���һ�壬���١���һ���������ν���˵������Ϲ���ˣ�ѡ��ȥ������ǡ��� �ν���˵������զ���ܵ����� �Ź�Դ˵��������˵Ϲ������ �ν���˵�����¿�˵Ϲ������Ҳ�DZ��¶����� �Ź�Դ˵�������¶����� �ν���˵������˵�Dz��DZ��¶�����˵˵���ԣ�����û�����ţ��� �Ź�Դ˵�������˲��������¶����� �ν���˵��������˵��ʤ����Ǻ��˻��ǻ��ˣ��� �Ź�Դ˵������զ�����������ϣ���ʤ���զ�ˣ��� �ν���˵�������Dz���Ҳ��˵�ٻ����� �Ź�Դ˵��������˵ɶ�ˣ��� �ν���˵���������ˣ�������������ɽʱ�����˵�ġ���ʤ���������ǰ����һ����Ķ���������һ�š���ʤ�����IJ�����Ȼ���Ž�ʿ���ʿ���������Ķ��ӡ�����ʿ��Ҳ���������췴�ˡ��� �Ź�Դ˵������զ�ܸ���ʤ���ȣ���ʤ����Ǻ��ģ������Ƕ��⡣�� �ν�������˵���ˡ� �Źⴺ������ɽ�ߺδ���������ӷ����м���һ�Ƚ��ӣ����ﰵ�����ˣ��������ε���һ���ˣ�����Ը����Ҫʵ���ˡ��δ����鲻�Խ����������֣�˵�����ߣ������ѣ��� �δ��������˴Ӵ嶫���������ӹ��������ϣ�һ��һ���˵ú�ϸ������û�д���ջ����ǽ�ϰοŶ����ǼҴ��¼�������ܹ�������Ҳ����������ء��ѵ��������ʱ����֪Ϊʲô���δ�������ֱ�����ȼ������ͣ�����Щ���¡����µ������������á���ʱ���δ����������˰������Ӷ�δ��ס���ӵĶ���������ð����������ͷ��ƣ���������������̣����ھ�ɥ��ʱ��ԶԶ������һֻ�����Ĵ�⬣���֪����զ�졣�δ��������ʼ���ǰ��ԥ��Ƭ�̣����ǽ�������Ŷ��� �����������������������������������˽�Ժ��������ӭ����Ц��˵�� �δ�������Ц�ݲ��õ������飬ͻȻ�н��������ֽŶ�����ô��Ȼ�ˣ������ƵĹ��ؾص�����Ժ���һ������ϡ� ��ɩ�ӣ�����ʵ������Ⱥδ���С���꣬�δ�����������Ϊ��ɩ�ӡ�������Ϊ����������˺ν������������ܺν����и硣��ˣ�����������������DZ���С�������ý������顰ɩ�ӡ�������������������ǵķԸ���С��ֻ�Ƿ������£����е���ɩ�ӵĵط�������ɩ�Ӷ��ԭ�¡��� ���Ѱ��Ѱɣ����ÿ�����մ�����Ķ����ߡ�����������Ȼ�ǿ��˿�� �����С�����ɩ����仰��С�ܾͷ����ˡ��� �δ���������������������������һ�����������Ů���軨���������ң��δ���̫��Ϥ�ˡ��軨�����������ã��ν��������Ź�Դ���Ƶ���ɽ�����⣬һ�����ؾ͵�ʮ����¡��ν������ڼң��δ��������������������ǣ�һ����ȥ��Ҳ���Ǹ����ˡ���ʱ�����������ᣬ��Ҳ���úÿ���Բ���������ۣ����������������ź����������ۿ��˵��ʱ�����Ľ�ë�������������ͬʱ��˵�����������䲻�ߣ��������С������˵������ظ�����������ʱ��������С������һ����һ���������鷿��˭���˶�������Ƿǡ��ر����ǰ�ͬ���������ˣ����è�Ƶľ�����������ƨ�ɺ�ͷ����ǰ�ܺ�Χ����ת����ס�ظ������������Ƽٵ���Ц��ɩ�ӣ��ܲ��ܽ���Ҳ��һ�أ�����������Ҳ����������ȻЦ��˵��������ĸ��Ľţ������������û��Ȣϱ����С����˵���Ͻ�����˵��ϱ����Ȣ�����ˣ�����զ�ž�զ�ţ���զ����զ��������ЩȢ��ϱ����������������һ�������Һ����࣬��Ϲ˵������ϱ�������ˣ�С��˺������죬�����������ն��ӵ��ݶ��ϣ���ʱ��������Ҳ�����ɡ���Щ�����˸�������˵ˣʱ���δ���ֻ�����ţ��Ӳ��������������ȥʱ��������ͷб���ۺ�˵����һ�ۡ������������������һ�������ġ�����������һ��ʱ���δ������۾�������û���뿪�������飬������Ҳ����͵͵���ƺδ������δ���������������˺ν����DZ��ң�������үү��үү��һ��үү�����˼������ˣ�˵�����ر��������δ�����ν���ȥ����ף����ʵʵ���ڵ��¶���Ҳ�������ԭ�δ��������������������Ц�� ����������뻱������Զ���Ͷ�ʮ����ء�ý�˸�����������ʱ���ձ����ӻ�ûͶ������ʱ�Ļ��������Ǹ�������è��û�н�飬�������˻���Ů�ˣ�˭Ҳ������˭��˭Ҳ��֪��Ҫ���Լ������Ǹ��˳���ɶ���ӣ��Ǻ��ǰף��Ǹ��ǰ����������ݣ���Ϲ��ȳ�ӣ����������ư͡���������ܴ�������ȡ�����ùõĽ�ѵ�����ùõĻ����ǵ��͵ĸ�������è������ǰ��δ�����Ǹ����ˣ���ȥ�ˣ���֪���Ǹ������Ǹ��ưͣ����ù�һ��֮�£����»�֮ҹ�ϵ��ˡ���ˣ�ý��һ���ţ��������˵�������ɵ�����������û�����������һ��Ҫ����ǰҪ���������һ�棬�������Ͳ��ޡ�ý�˾Ͷ��˸����ӣ��кν������������ȥ���ף��ν���һ���������է�ˡ�Ҫ˵������Ҳ���ͣ����Ҳ���������������Ϸ��˼������ӣ�����ô�������ν������ȥ�����������ĵ��ý�˸����˸����⣬˵Ѱ������ν���ȥ�ࡣ�ν����ĵ��;��ҵ��˺δ�����Ҫ˵���δ��������ġ����࣬�����Ⱥν���ǿ�������������Ⱥν����������Ⱥν����ס�����ѡ�кδ���������һ�������Ǻδ������顣���죬�δ�������ý��ȥ�ˡ�·�ϣ�ý�˸��δ���˵���ǹ�Ů���ڴ���ͷ�ڶ��ң��ų���������СԺ����ֱ�ӽ�ȥ�����ˣ���Ҫ�¡����������ң����˵�ҵ��˼��������˴��������ǹ�Ů�Ҳ�Ҫ��˵�������˷��Ͻ��ߡ�����������X���˼��䷿�ӣ���Ͱ�������������˵��ý����������ؽ�����һ�������ºδ���˵���졣ĩ����һ�ζ��̣����С�ĵ㣬���˵�������˷����ߡ�����ý�˽����ú���ϸ���δ������ﻹ�����������������δ����������º�ˣ����ȥ�����˼ҵĴ��Ů���δ�����������ׯ��ֱ���ߵ�����ͷ�����ŵڶ������žͽ�ȥ�ˡ�����ӭ��������һ����ʮ�����Ů�ˣ��������ſ϶���������������Ц�Ž���һ�������������ӹ������ϵ�����--���Ǻν����Ҹ�������Ʒ--����������һ���������£��ܿ����������һ�뼦���衣�δ������꣬����������������г������δ��������档��ʵ����������������������ˣ���������Ժ����δ����Ů��˵���仰�������������ȿ�����Ը�⣬���ﺰ��ʱ���ͳ�������Ը�⣬��˵ͷ�ۣ����������档��������δ���˵��ʱ����һ���δ������������Ǹ��ˣ������˳��ò�����������ġ����ԣ������ﺰ��������һ��ʱ�����ܿ������������ǰ����ɫ糺���к��δ����������ˡ��δ�������վ����ǰ�������Ů�����ﲻ��һ���������Ůȷʵ���úÿ���ԲԲ�����������ۣ�˫��Ƥ������ë�����ź������Ƶ��������������˵���ƵĶ��ˡ�һ���ִ��ֳ��ڵ÷����Ĵ����˦�ڱ�������·��ƨ��һŤһŤ������������Բ�����ƨ�ɵ��ϲ�ס�ذڶ����δ������۾���Ĵ�����ס���Ƶģ����㿴�˺ü����ӡ��δ���̰����Ŀ��ʹ�����������ø����ˡ����е㲻����˼�ˡ����飬ȥ��ú������Ϲ������ʳ��������������ôһ˵����ʱ�Ӿ����н����˳�������Ӧ�ſ첽�߳����ţ��������Һ��ƺ��Ƶذڶ��ţ�ǣ���źδ���̰����Ŀ�⡣ֱ���������������δ���������һ����ĭ������˵�����ˣ����������������δ�������Ƿǵ�ʱ���������ý��զû�����δ��������η��ѡ�������Ҳ�Ǻν�����ϱ�����ν����Ž��и������뵽��ô���Ĺ�Ů��Ҫ������Ʈ�����ӵĺν�������Ҫ��Ϊ�ν�����ϱ�����ν�������§����Ū���¶�����������ð����һ����ˮ���ǹ���ˮ˳�ź����������ͨ��ζ��������������ɲʱ�鲼ȫ�������е��������dz�����ʭ�ӣ���һ��˵������������������ܵIJ��������֪�����Ů�����������������Ͳ��������ν������������ۿ���һ�����������ʻ���Ҫ�嵽һ�Ѻں�����ţ���ϣ���ʮ����ʹ����������������ʻ��ǻ������������ϡ���Ҫ�������������ʻ���Ȼ���ʻ���ţ����Ȼ��ţ�ࡣ�δ���Խ��Խ����Խ��Խ��ڣ��������Լ��ò�������ʻ�����ڵ�������������������������������������һ���ʳ����������һ�������Ц���δ������ű�ʳ��ͬ����������һ��ζ��Ҳû�У������Ǹ�Ц�����ӡ���˴������������ζ����δ��������ʳ�����ߣ���ƨ����������������������ó��ص�̧���������δ����ֺ������ڲ裬��������һ�����ԵĿ�ɬ����ʵ������������������ʹ�࣬������˿˿�Ŀ�ɬ������������ǡ�������Ͳ�������͵����ſڣ���ת�����ʱ��������Ŀ���飬�������ᣬ����Թ�⣬�����е����鸴�ӵı���Զ�ȸղ���һ�����Ц�������⣬��ʹ���Ķ��������������ҡ�� ���죬�δ���Ҳ��֪���Լ�����ô�ص��ҵġ� ������˺ν�����������Ϊ������ϧ��Ϊ���鲻ƽ����Ȼ�������ڸ�ͷ���ҿ�������ɬ������̧��������ͷʱ����ʱɵ���ˣ��������ͷӿ���������ۿ���������������ת����ǿ���ţ������ջ���û����ס��˳��ԲԲ�����������������ν������ˣ�ʲôҲû˵�������ײ���������ɶ�ᣬ����ӿ����һ������֮�С�����ҹ������鲻�ν���������Ҳ���ν����ϴ����ν������ڵ�������һ��ϯ������һ�����ӹ������ϣ������˴��µ�С�����ؾص�˯������컹û�д��������������ˣ����ų�ͷ�µظɻ�ν����ӵ����������������˳Զ˺ȡ������ʳ���������ϴ��ƵĶ���������ʵʵ��վ�ڲ�����ǰ���Ȳ�˵��Ҳ��������һ�Σ����Σ����Ρ����������ڴӺν������Ͻӹ����롣�������������£��ν���û��մ���ıߡ������������ν�����ʵ����Ҳ������������������Ĺ�Ȱ������ŰѺν����ı����õ��˴��ϣ�С���ڲŹ��˷������ һ�죬�����鵽�ӱ�ϴ���ѣ������δ���������Ͱˮ�����ߣ�������������������һ�ۣ�˭Ҳû��˵���������˶��ӶԷ���Ŀ���ио�����ʲô���δ����ĸо��ǣ��������Ŀ������Թ�к�Ҳ�а�����������ĸо��ǣ��δ�����Ŀ����ֻ��һ��ʹ�ࡣ��������һ��������������������������ĵ��Ǵ�������������δ�����ԶҲ����������������ʱ���ֺ���������Ŀ�⣬������Ҳ��Զ���������δ�����������������֮�顣һ������ʹ���ʱ��������õĹ�ȥ�������ʹ�ࡣ��ʱ���δ�����������������ʹ�����ʵ��Ʒζ���۵Ĺ�ȥ�����������˿������Σ��������ܡ��δ�������ͷ���ˣ�����������û�п�·��ˮͰ������һ�����ϣ�����ˮ��ȥ��һ�롣ˮͰ�ڹ����ϵ�����ز�ס����ת���δ������������Ӷ��������أ�ˮͰ������һ�٣��ý�һ�ţ�����ˮͰ���ˮȫ�������˵��ϡ� ����������զ��ˮ�����Ƕ������Ӻδ�����ǰ·���ĺν���������ʡ� ���������������δ������ش�������׳���һ��ν�����Ҳ�벻���IJ������ɵ����ɵĻ��� �ν��������δ����������¶���û�и�����˵����������µ�ȥ�ˡ� �δ������������¶��������������أ����ν�����Ҳ�������飬�����ֺ���˭Ҳ�����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