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ع�ϵ������ǰ���������Ҫ���á�����һ���塱���ϵ��о����������ƴ����е�����ѧ����̽�ӣ�������ѧ��չ���й����ԵĹ��е����Ļ�����ʿ���һЩ��ʷ��ʵ�����������Ա�������ѧ�ķ�����������ڹ�ͣ��ڴ˻�����Ϊ�ƴ�������ѧ���ж�λ��
��ν�˵ع�ϵʵ���Ͼ������������������Ȼ�����������õĹ�ϵ���������ĵ���ѧ����֧�Ļ�����ѧ����Ҫ�о������Ļ�����ѧ�о�����һ�������ռ䷶Χ�ڸ����Ļ����صķֲ��ṹ���γ��������Լ��Ļ����ۡ��Ļ���̬�ĵ������硢�ݻ���չ�����ݣ���ǿ���Ļ����ŵĿռ���ϻ��ܺ͵���ϵͳ���磬ָ���ر����������Ļ�������˵ع�ϵ������̵�Ӱ�졣�����Ļ����ۡ��Ļ�Դ�ء��Ļ��������Ļ����������Ļ������о�����Ϊ��Ŀ�ļ���������ݣ����Ļ�����ļ��𡢶���ͷ����������Ļ�����ѧ�о��Ļ�����
����ѧʷѧ�ƵĽǶ��������Ļ�����ѧ���˵ع�ϵ��ʵ���Ͼ��dz�����ѧ�͵�������������ԡ����������ҵ����ĵ����ò�����ҷֲ��ĵ������硢��Ʒ�ĵ�����Ǩ�������������ľɷ�ʽ��ͻ�ƣ�һ����Ȼ���������Ļ�����������ʶ����ҵ��ۺ�Ӱ�죬�ɷ�����������������ɵ��Ļ������ڴ����ϵ�Ͷ�䣬��ѧ�Ĵ������������µĵ�������Ϳռ���ĵ��������⣬�ɵ����ԵĿռ��������Ե�ʱ�����ݽ����̵Ĺ��ɵȵȡ�
��ν������һ���塱�о����������Ļ�ʷѧ��һ�ֲ������ɣ����ݱ��ߵ����⣬ʵ�����ǽ��Ļ�����ѧ�����ʷ���϶��γɵ�һ�֡����о�����
�����ƶȻ�������ƶ��Ǵ�ͳ�й�����һ��ͻ�����硣����������仯��Ȼ�dz���������ǰ�ִ�����У������ߣ���Ȼ������һ���ԣ���������ᡢ���Ρ����á��������Ļ���������ѧ����Ӱ�����ã����κ��˶������ϵġ�����˹.Τ�����й�Ϊ������ṹʽ����ᡱ����R��Ǭ����������Ϊ�й����Ĵ����ʣ����ԱȽ�˵��ӡ�ȵ�������ᡢ�����ľ��ֲ���ᡣ
���������Ϊ�����ʷ�ҵ�һ�ˡ���Ǯ��꿣������ʷ�����������������ˣ�Ի�ߵأ�Ի���ƣ�Ի���塣Ǯ�����˵���ߵؼ���ʷ����ѧ�����ĵ���ѧ�о������弴�Ļ�����ѧ�����ʷѧ�еļ����о����������Ϊ�й���������֮�ƶȷ������磬���й�ʷ�о��У���������춵���������ϵ��̽�֣�
���Ժ���ѧУ�ƶȷϳۣ���ʿ����֮����ֹϢ�Ժ�ѧ��������춼��壬�����帴��춵���κ�������ϱ���֮ѧ�����ڽ̽�����塢�������㲻�ɷ��롣��¤һ�����Ծ�������ĩ����������������֮�������ܱ��溺����ԭ֮ѧ���ߣ�����ǰ�����Լ��������֮���㣬����֮��������ѧУ֮�ٷϣ�ѧ��֮������춼��壬̫ѧ��ʿ֮���ڱ�Ϊ���˸���֮��ҵ����ν�ϱ���֮��ѧ����Ҳ����ѧ��֮���ڼ���춼��壬������ѧ��֮��ϵ����ǰ��֮��Ҫ������ԭ���Ҿ�������֮ʱ��������֮������ά�ֺ�ƽ���������֮ѧ����ý����Ŵ�������ʯ����֮ʱ����ԭ֮��ϤΪս����������һ����ǰ���������Ժ��г��ΰ������䱾������֮ѧ���ȿ��Ա��棬��������֮��Ӣ��þ�֮���ڣ���ʱ�Ⱦã����Ļ�ѧ���콥�ߵ������ʣ��˺�¤����֮�������뱱���������Ļ�ѧ��֮ȫ��������֮���й�ϵҲ��
��ѧ����˵��������һ��ѪԵ����֯����ѪԵ���ݹ���Ļ�Ԫ������ھ��е�Ե���磬���忤�������ǡ�ѪԵ�Ŀռ�ͶӰ��������Ⱦ���ѪԵ���Ե��˫���ԣ������������ʵ��������ص����϶�Ϊһ�ġ��ڵ����Ļ��о��й˼�����������أ�Ҳ�ͳ�������Ӧ��֮�⡣�������������һϵ������������˵�Ǹ������ṩ��������ʵ��ʷ�ϣ�����˵�Ƿ����۵�������ϡ���Ȼ����ڱ�硢Ǯ�¡��������λʷѧ��ʦ�ԡ�����һ���塱�о��������Ķ�������Ҷ���ʾ���Եijɹ��������ж��н辵��¼��
�����������ἰ�����۱������о������������й��Ŵ���ѧ���ر����ƴ���ѧ���о���״�����߷����������ص㣺
���ȣ�����ѧ���������������ϵ����ʶ����Ϊ���룬��Ϊ�ϱ������䷽�������γ����ϱ��Ļ�����ѧ�IJ����������ͳһ��ʹ�ϱ��Ļ���һ�������ںϣ�����ѧ��������Ȥ�ͷ����ֳ�һ���ں�ͳһ״̬�����ε�ͳһ���Ļ��Ľ�����Ȼ�������������һ���̶������ڵ����𣬵������ܳ���Ĩ���������ɲ�ͬ��
������������ɵ�����������������Ʒ��������ƴ���Ȼ���ڣ������ڴ˺����Ԫ���塢�����ֵ�����ѧ����Ȼ���ڡ����Զ�ͳһʱ�ڵ���������ӣ�����ʹ�о���һ�����
��Σ��ϱ������ȻΪ��Ҫ���Ļ����֣����������������Ǵӵ���ѧ�����Ļ�ѧ������������ͳ�����������й��С�¤ʯ�����������塢���ԡ���³���Ϸ������еľ�������Խ���������ϵ��Ļ�Ȧ����������ͬһ�´������˴˵IJ���Լ����ֲ�����ѧ��ϸ����Ӱ�죬����ѧʷ�о������Խ��١���������ѧ�о����ԣ������ϱ��Ļ��IJ���ͳһ���еļ�ֵ������ͬʱ��˶����Ķ����뻺�ͣ�����һ�����뵽���ϡ��ض��������������Ȳ�ͬ�����У�̽��������ѧ�����Ĺ�ϵ�����������塣�ȵ�ָ�����ǣ����е�����Ϊ�������ڣ����е����Ļ������磬����������Ļ����Ķ��������Ļ������磬��ν��Ԫ֮��ϣ�����֮���飬�������ѧ��Ӱ��Ҳ���θ��ӡ��������ָ��������֮ʢʱ��������ѡ���ߣ���ֶ��ؽ���Ҳ��������ʫ��������ʫȡʿ��˿��֮�أ��������ȣ��Ĺ쳵�����ۣ������䲻�ܣ����ɵ�Ҳ������ʦ�����ڡ���ʫ�볤����һ���У�����ר�Ų������پ������Ա���д�����������ࡣ
�������Ӽ����Ļ��ĽǶȹ�����ѧ���������Ѿ�ȡ�ó���Ľ��������κ���ϱ���ʱ���ŷ�ʿ���ƶ����Ļ�ѧ������ѧ�����Ĺ�ϵ�о���ӿ�ֳ��������з����ijɹ������а���һЩ˶��ʿ���ġ�������֮�£����ƴ������ʿ������ѧ�Ĺ�ϵ���о������Եúܱ������Ѿ������ijɹ����١���ʵ���Դ����������������ݵ����硣������Ӧ�롶ʫ�������������ƴ����ӡ��ֵܡ���������ѧ���������ڣ����ҷֱ���ӡ��ֵܡ������ֵܡ�����������������������˵������Ӧ�뻹�����ָ���������������¡�¬��Τ��֣֮�࣬�������£���������������������Ԫκʱ����Ϊ���壬��ʢ��������ʼ���Ļ�����Ⱥ��Ʒ�����壬ʱ�Դ���Ϊ��һ���ú������ˣ�ʷ�����飬����ʫ֮ʿ���ڣ�����Զ����Ҳ����������֮�������д�����ʫ�߽���ʮ�ˣ�Ȼ���ܽ�˵��������֮�ڣ�ʢ��֮����֮ἣ�����֮³���Խý��㵱��ġ�����ʫ����֮��ռ����ʮ֮һ����νʢ�ӡ������ϵľ�����ۻ�ɽ�һ���̶ң�����������������Լ���������ӽǣ���������з����۵����塣
ְ��֮�ʣ�������ͼ̽���ƴ�ʱ�ڹ��е���ʿ���ݱ�����ѧ��չ�����ֹ����ԣ���Ե�˶��ƴ�������ѧ�����Ļ��ӣ������·�������Լ���һЩ������
��һ����������Ļ�����ķ��룬ָ�������Ļ�������ָ���е������γɵ��Ļ���ͳ���ǹ����Ļ������еļ�ֵ������ռ����ݡ�ͨ���Թ����Ļ�����Ľ�������ͼ�����ƴ�������ѧ�����̳����Ļ�������
�ڶ����ӷ��������ĽǶ�����������ѧȤζ���������Ž�������������γɴ�Ȥζ��ԭ���Ļ�����ѧ�Ĺ۵���������ѧȤζ���γɣ�ʵϵ����֮�������������Ļ���Ҫ������ʷ�����л������ɡ�ͨ���������Ž��������γɵ��ݣ������ƴ�������ѧ�������ѧ��Χ��
������ʿ�����й�����һ����Ҫ���磬���й��ƴ�ʿ���״������ѧ���翴���Ϸ��硣���߳��ƴ����ʿ�巢չ��ת���ڣ�ʿ���˥����������ĩ����Ĺ۵㡣������ضԡ����п��ա��͡�����Τ�ţ�ȥ����塱����������в��ͣ���ʾ�������������ķḻ���Ļ��⺭��
���ģ����������ѧʿ�壨����ѧ���ң��ķ��룬�����������������ƴ�������ѧȺ����γɡ����ȣ���ʱ��ά�������������ѧʿ������ˣ���Ϊ����ʿ�徭����һ�����ĵ��䣬�����䵽�ģ����Ӿ�ʷ���ҵ�����ǿ�ڣ���������ǿ�ڵ���ѧ���ҵ�������Ǩ���̡���Σ�������ѧȺ��Ĺ����ĸ��ӣ��͵����������������
�ֱ��й��б�������Ⱥ���Ӷ����պʹ������ռ��˹�����̳�����Ϻ�ɽ��ʿ�˲�Ǩ�����ߵȼ�������ɡ�����һ���Ӵ������ɢ�Ĵ���Ⱥ�壬����ʿ����ɽ��ʿ�ˡ�����ʿ��һ���������ɫ���ʶ���֮�ƣ���һ��������Ǩ���������ٳɽ����ںϡ�
���壬ָ���ƴ���ѧ��˥����˽ѧ�����·�չ������ʿ�����Ӽ������������ǿ����ѧ������
������ѭ�ˣ�����������̳�ϵġ�ţ�������һ�ش��¼����м�⣬ͨ��ͳ�Ʒ��������֡�ţ����������ɺ�������Ŀ����ֲ��������Եĵ������硣���Ա��Ҫ��ɽ������ʿ�壬��ţ����Ա��������춹�¤ʿ�壬ţ�����������֮��������ʿ��֮��ġ�Ȧ��֮������
���ߣ��ֱ���մ�����ĸ����Ԫ���������ѧ����Դ�����������������������Լ��Ŀ�������ͼͨ����ѧ��������Ĺ���ʹ���Ƕ��ƴ�������ѧ�и����ε���ʶ��
����ǰ����Ϊ���ۣ�����Ӵ����ۣ���۰��ա��ˡ��š�ʮ��Ϊ���ۣ���������㵽���������漰�������һ�㿪�������롣��¼����������⼰���ϵĿ�֤���������������۹���Τ���������ѧ��һ�£�����δ��壬�����������鶩ʱ�ٲ��롣
������ƫ����ʷ�Ļ��о�������Ŭ�������۸������ı�������ʷ�Ͽ�֤���ϵ�ѧ����ͳ���ڲ��ϵ������ϣ���ע��������Ŀ����⣬���Ķ����⺣�⺺ѧ����о��ɹ���ʹ�����ȷ���۵��������ȱ����ظ���ͬ���ַ�ֹѧ��ʧ��֢����ͼͨ����һ�йص�����ѧ����Ŀʵ�����������ʷ��������ѧ�о�����νӶԻ���
��Ȼ�������Ƨ������һ�磬��ȡ������ѧ���³ɹ�����Ѷ�����ܵ����ޣ����ԣ����ߵ�����Ŭ��������˵��һ�ֳɹ�չʾ������˵��һ��ϣ������
���е���ˮ����������ѧԨԶ�����������������Ȼ���������춴����⣬�ҽ�����������������������ų����ָ��ź��ջ��������ۣ�ѧֳ���ޣ�ֻ�ܽ���һ�����ijɹ��ύ�����������һ������о����ԣ�������Ȼֻ��ȡ�ƴ�һ�Σ�������ʿ����ص���ѧ�����У�����Ȼֻ������ľ�dz���������������Բ�ڵ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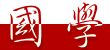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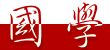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