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科学的历史与人文的历史、通与专、守旧与维新、开放多元与自我坚守、客观之严谨与理解之同情五个方面论述了钱穆学术思想中的“中和”,并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钱穆的史学思想对于现代史学发展的意义和价值。[1]
绪论
“博大真人世共尊,著书千卷转乾坤。公羊实佐新朝命,《刘向、歆父子年谱》司马曾招故国魂。《国史大纲》陆异朱同归后案,《朱子新学案》墨兼儒缓是初源。《先秦诸子系年》天留一老昌吾道,十载重来献满樽。”[2]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村,一生从未进过大学读书,更未出洋留学,全以自学名家,弱冠之年,初等杏坛。由小学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终登燕大、北大之学术殿堂。尔后又悉心办学,创新亚书院,享年九十五载(1895-1990),终成一代学术大师,桃李天下,贯通今古,可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他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魅力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钱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为出众的史学名家之一。关于钱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历程、为人治学,自然有钱先生自己的自传以及其他评传作一详细的阐述,我这里不便也没有必要多加论及。我这里仅只是就钱穆学术思想作一家之谈。

晚年钱穆
钱穆先生谢世十余年来,研究其学术思想的人可谓不少,抑或一部分学者虽无专论,也在其它场合发表了一些意见和看法。尤其是近年以来,随着余英时、罗志田等钱先生的弟子、再传弟子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论著在中国大陆历史学界激起一阵又一阵热潮,钱穆这个名字也由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唯物史观一统天下时代的边缘地位逐渐进入了人们视野的中心,在这个史学多元化的时代,钱先生的许多治史思想对于我们来说至今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钱穆及其夫人
钱穆先生一生可谓著作等身,其学术思想也是源远流长。虽然总体上有一独特的风格,但也不是铁板一块。因此,在这样一篇小文中要想全面概括钱先生的学术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前几日读《中庸》,突然读至“致中和、天地位焉”[3]一句时,心中顿有所感,觉得钱穆的学术思想虽极复杂,总括起来,却似乎始终离不了“中和”二字。这种折中今古、融会中西的“中庸”思想实在可以称得上是钱穆学术思想的一大特点(似乎用于概括其为人治事也可以说得通,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略而不言)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钱穆一直秉持着这种无过不及、中庸平和的学术理念,这里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科学的历史”与“人文的历史”的统一
有清一代,至乾嘉之际而考据之风日盛,蔚为大观。出现了戴震、阎若壉、崔述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与此几乎同时,西方实证主义思潮和“兰克史学”勃然兴起,似乎此时的东西方的史学不约而同的都朝着一种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无论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所谓“春秋笔法”[4],还是西方基督教传统史学,此时都面临着某种程度上的挑战。而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东西方的这两大史学思潮在中国汇流,20世纪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40年代,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注重史料和考证辩伪的史学流派一直处于中国史学界的核心地位。[5]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际上也是将历史“科学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总趋势,我们不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科学化”的进程。
我们这里之所以要对近代以来所谓“历史的科学化”进程作一提弦钩要式的阐述,实际上是想表明钱穆既然身处这一学术潮流之中,就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与浸润。
一方面,钱穆继承了乾嘉以来考据学“精审”的学风,他早年的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以及后来的《朱子新学案》等都大抵属于这一类以考证史实为第一要旨的著作。就近代学者而论,钱穆虽然与胡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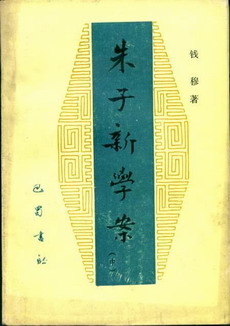
《朱子新学案》书影
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治学思想上存在差异,但如果说早年的钱穆没有受到这一派实证主义学者的影响,或者钱穆的治学思想与这一派人物的史学思想完全格格不入,怕是说不过去的。例如胡适,总体而论,钱穆与胡适一生论学多有不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从一开始就对胡的主张采取了一种全盘拒斥的态度。相反,在钱穆早年的胡适形象中,胡适可以称得上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其思想对于钱穆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四”以来,由于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等人的大力提倡,学术界治诸子之学一度蔚然成风。钱穆早年以治子学入门,其治学方法路径不可能不受到胡适等人的影响。从钱穆对于胡适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上)的评价中,我们于这一点便不难窥见一二。他说胡适的著作“介绍西洋新史学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先途甚大。”尽管其对于胡适的著作也有一些批评,但总体而论,仍然是持以一种肯定的态度。就方法论这一层次而言,从钱穆早期对于墨家、易学等的研究中也不难发现胡适的一些治学方法对其的影响。
应该说,钱穆的史学思想是具有一种科学的精神的,但是却没有陷入“科学主义”与“科学万能论”的泥沼之中。关于这一点,余英时先生有过精彩的一段评论: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不一一具备。他自己便说道,他的疑古有时甚至还过于顾颉刚。但是他不承认怀疑本身即是最高价值。他强调:“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不能决。一味怀疑则必然流于能破而不能立,而他的目的则是重建可信的历史。许多人往往误会他是彻底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事实上,他对于所谓“科学精神”是虚怀承受的,不过不能接受“科学主义”罢了。我们试一读《国学概论》最后一章,便可见他确能持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文化的争论上,他并不同情梁漱溟的武断,反而认为胡适的批评“足以矫正梁漱溟氏东西文化根本相异之臆说。”[6]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钱穆“科学的历史”以外“人文的历史”的这一面。这种人文主义的情怀,我认为集中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怀与尊重,一是对于历史的语言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钱穆的旧学功底深厚,家学渊源流长,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
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他晚年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以及邓尔麟教授所著的《钱穆与七房桥世界》中可以窥见一斑。这里由于篇幅的关系,不容细谈。
钱穆出生在一个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时代,当时的中国已是满目疮痍,岌岌可危,处在之“三千年来前所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之中。亡国论调和民族虚无主义甚嚣尘上,西方文化大潮如巨浪般奔涌而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7]钱穆晚年在其《师友杂忆》中回忆道:“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进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钱)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8]钱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同情以及对于民族、国家的一种忧患意识贯穿于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这一对于本国历史和传统的态度在其代表作《国史大纲》里有着精彩的论述:“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9]他的一生,包含着对于中国以及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余英时在他的书中将这一点概括为一句话——一生为故国招魂。我们暂且不论20世纪的中国到底是否失掉了这一“魂魄”,但就钱先生这一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拾民族自尊、自信这一理想而论,无疑是可堪敬佩的。钱穆曾经说:“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10]正是因为钱穆具有这样一种对于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种“温情”,我们才不能不谓之一富有人文精神的历史学家。
还有一点,我在这里尚需强调一下,历史学一贯是以求真作为基本准则的,但是钱穆先生的学术论著不仅体现了一种严谨务实的求真精神,也不失为美文的典范。杨树达在提到钱穆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曾特别指出“文亦足达其所见”这一点,是十分具有眼光的。“因为钱先生在此书中每写一家必尽量揣摹其文体、文气而仿效之,所以引文与行文之间往往如一气呵成,不着剪接之迹。但读者若不留意或对文字缺乏敏感,则往往不易看得出来。”[11]。这便是在真与美的统一,钱穆的文章之所以好看、耐看,就是因为其做到了这一点。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12]钱穆之文实在可以称得上“真实性”与“艺术性”统一。
综上来论,钱穆的史学思想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既是求真的,又是求美的。在二者之间,钱先生中和有度,无过不及,实在是难能可贵。
通与专的统一
有人称钱穆先生为一代通儒,甚至有人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中国最后一位读书人”[13]这种说法虽有可待商榷之处,然而从钱穆独立担任北大中国通史教程、编著《国史大纲》等事例不难看出,钱穆的确是一位胸中有大丘壑的通博的历史学家。近代以来史学专门化、精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钱穆这般如此注重通博而又功底深厚的学者的确是十分鲜见的。如果我们略为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史,就不难看出,钱穆的通博的历史观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衣钵。“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自有其分类和流变,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整体的观点。”[14]但是,钱穆并非是一味的“通”,其所处的时代,西方学术的专门化趋势已经向中国的学术界袭来,梁启超等人也提出了历史学专门化的命题。尤其是五四以来,由于胡适之、傅斯年等人的推动,注重实证的史学勃然兴起,这一思潮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史学研究向着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精彩的考据文字。(如傅斯年对于“性、命”这两个字的考辩)在这一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折冲之际,如何沟通与融合成为了当务之急,一时无法解决。如果单纯地依照西方的分类,各人选一专门的范围去进行窄而深的断代研究,当然也会有成绩。但在熟谙中国传统的人看来,总不免有牵强和单薄之感。如果过分注重“通”的传统,先有整体的认识再去走专家的道路,事实上又是研究者的时间、精力、聪明都不能允许的。钱先生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15]现在大家都把他当作学术思想史家,其实他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史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国史大纲》中“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三章尤其有绝大的见识,显示了多方面的史学修养和现代眼光。[16]以上我们从其著述和思想源流论证其学术思想中“通”与“专”的关系,而仅从钱穆对于其弟子余英时的指导中,我们也可以窥见钱先生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一九五三年钱先生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创办研究所,这是新亚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三四个研究生,我也在其中。但我当时的兴趣是研究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由钱先生任导师。钱先生仍一再叮咛,希望我不要过分注意断代而忽略贯通,更不可把社会经济史弄得太狭隘,以致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配合不起来。”[17]这里讨论的仍然是“通”与“专”的关系问题。
以上主要强调了钱穆思想中“崇尚通博”的一面,然而在一个学术专门化已经成为一大趋势的时代,钱穆并没有对此采取完全拒斥的态度。他曾经说过:“今天的学问已是千门万户,一个人的聪明力量,管不了这么多,因此我们再不能抱野心要当教主,要在人文界作导师。所谓领导群伦,固是有此一境界;但一学者,普通却也只能在某一方面作贡献。学问不可能只有一条路,一方面,也不可能由一人一手来包办。今天岂不说是民主时代了吗?其实学问也是如此,也得民主,不可能再希望产生一位大教主,高出侪辈,来领导一切”[18]关于这一段话,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里也有精彩的阐述:他的“通儒”并不是和“专家”处于互不相容的地位。现代学者首先选择一门和自己性情相近的专业,以为毕生献身的所在,这可以说是他的“门户”。但是学问世界中还有千千万万的门户,因此专家也不能以一己对策门户自限,而尽可能求于其他门户相通。这样的“专家”,在他(钱穆)看来,便已具有“通儒”的思想境界。但“通儒”又不仅旁通于其他门户而已,在旁通之外,尚有上通之一境。钱先生常说,治中国学问,无论所专何页,都必须具有整体的眼光。他所谓整体眼光,据我(余英时)多年的体会,主要是指中国文化的独特系统。[19]总之,钱先生在中国学问尤其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一方面注重“通博”,破除门户之见;一方面又尊重现代专业的发展和研究专门化、精细化的趋势。这样一种“通”与“专”的统一,同样的体现了钱穆思想中的中庸融会着一特点,这也使得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类,既有《朱子新学案》、《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等精彩的考据著作,又有《国史大纲》、《国学概论》等纵观今古、上下千年的宏大文章。可以说是“见树又见林”,我想这也许就是钱先生何以在中国史学研究的众多领域、众多时段,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联系当下,今天的历史研究我们所涉及的材料、信息,较之钱穆的那个时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我们在这浩如烟海的材料当中又何以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创见呢?在这个学术专门化已经达到空前程度的时代,我们是否还需要一种“通”的精神呢?我以为这仍然是我们进行史学研究应该遵循的,“通”从今天的意义上来说,更多的指的是一种境界。所谓“未之逮也,而心向往之。”也许,我们无法达到真正意义的“通博”,但只要有此一精神,我们的研究就一定不会是“见木不见林”,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谈到:“道欲通方而业需专一”,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人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吧!
守旧与维新的统一
“守旧”与“维新”这一命题,似乎不仅贯穿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始终,而且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密切相联。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学人到底应该是固守旧有的传统,还是改革维新,这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以往,在中国的学术话语里,似乎“新”的总是超越于“旧”的,“维新”的总是超越于“守旧”的,这一论调实是在一种长期持续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惯性。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将所谓的“守旧”与“维新”放在一个平等的境地,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对其有一个较客观、较全面的评价。
对于钱先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守旧派,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的确,钱穆一生笃信儒家的文化传统[20],以宣扬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为故国招魂”作为自己毕生的责任。这种对于传统的留恋不能不让人将其与所谓“守旧派”联系在一起。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么?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钱先生自己是怎么说的。钱穆在1988年为《国史新论》所作的《再版序》上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亦可谓为余治史之发踪指示者,则皆当前维新派之意见。”[21]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可以这样来理解,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倘若固守陈说,不乏新论,又何以有不平之鸣、新巧之论;又倘若作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又何以旁征博引,成一家之言。故而史家为史,必有守旧,也必有维新。这一点本不必割裂来看待,就钱穆个人而言尤其如此,他个人治史的路径,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中国传统史学这一路体系,但是就史学研究的方法而论,其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也受到了西方兰克史学、实证主义思潮等的影响。而就其在历史结论上敢于求新而论,则更是如此,《刘向、歆父子年谱》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驳斥以及与胡适之等人关于《老子》一书成书年代的论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倘若将钱穆武断的划入“守旧”的历史学家一派,实在是有失公允的。
谈到这里,我还想就当今史学的发展趋势和钱穆史学思想对于我们今人的启示谈一点看法。应该说从讲求实证的历史学(包括新实证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历史学,从兰克史学到后现代史学,历史学近二百年来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姿、快速发展变革的局面。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这样一个史学多元化的局面,有人谓之“以色列已没有国王”(语出《圣经》),有人谓之“群龙无首”(语出《易经》)。尤其是所谓后现代史学的兴起,似乎使得人们产生了某种隐忧:历史学本身是否有被解构的可能?在新的世纪里,世界历史学的发展将向何处去?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史学的基本纪律并未发生根本的动摇。因为无论何种史学,也无论这一路史学家自身是否承认,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建立在以往经验基础之上的学问,经验知识的取得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客观的证据。余英时说:“西方近一两个世纪所逐步建立起来的鉴别史料、检察证据等一套研究程序早已取得高度的稳定性。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基本纪律。今天的史学家可以在解释和观点层面自抒己见,但是,如果他在基本纪律方面犯了严重错误,那么,他的史学家资格便会受到怀疑。”[22]余英时在其的《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中具体举了“亚伯翰事件”作了一个有趣的例证。亚伯翰的最终离去(被逐出美国史学界)向我们证明了一点:现代史学有着自身的基本纪律和研究规范。如果这种纪律和规范本身并不存在,亚伯翰也就根本无错可认,那些暗中同情亚伯翰的史学家们也就不必有所顾忌了。今天的美国史学界有一部分学者由于受到欧洲一些后现代和解构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把相对主义发展到主观的绝境”[23](余英时语)有人甚至认为史学根本无客观可言,史学和虚构之间并没有一道明显的界限。(例如海登怀特)这样,无疑就把历史学由一个极端(所谓纯粹的客观主义,或者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带入了另一个极端(即非理性的、纯粹主观主义的倾向)中去。现在的一部分学者,不重视基础的研究,不做严谨的考证功夫,以一己之见,在后现代史学、结构主义史学、元史学、“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旗帜下作“百犬吠声”,玩弄西方名词、抽象概念。这一现象在西方的汉学界存在,在中国的国内历史研究中也不鲜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历史研究提倡多元、提倡百家争鸣式的发展。但是,我们决不能容忍所谓“体制外的改革”,因为这样的趋势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可能最终导致历史学的崩溃,我在这里并不是在今天这个历史学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时代里做什么“盛世危言”,实是不能不重视这样一股暗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虽然现在这样一种倾向还只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存在,但如果不能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势必会对今后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产生极端不利的影响。但是,我这里还有必要申明一点,所谓的基本纪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规,一旦这样一种定规成见强大到了足以框缚一位历史学家的思想的程度,则一种文化的专制主义随即席卷而来,历史研究领域也将变为一潭死水。
所以,过犹不及,钱穆的在“守旧”与“维新”中求统一的死穴思想未尝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能再这样一种史学多元化倾向与基本纪律或者研究规范中寻求一种内在的平衡呢?
余英时在这本文集里还集中讨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这一命题,他认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24]而且直至今日,“思想激进化的历程仍然在持续之中。”[25]我们这里由于篇幅及核心论题的原因,不可能就这一问题展开进行论述,我这里所要强调的只是,在这样一个“后激进化”的时代里,如果我们反躬自省,扣问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我们会发现我们似乎可以从那里找回我们失落的某些东西。这种对于“传统”的眷恋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而是一种对于近一百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这样一条激进化道路的再思考。“保守”与“激进”,“传统”与“现代”,其中的褒贬不是所谓落后与进步所能界定分明的。受进化论的影响我们已经太过习惯站在历史的最高点上,似乎一切传统都被踩在了我们的脚下,成为了已经死去的过往的追忆。然而,试问,倘若我们的脚下没有传统的沉淀,我们又何以能立足于当下呢?当然,正如余英时所说:矫枉不能过正,我们决不能提倡用“保守化”来代替“激进化”的潮流。无论是爱因斯坦也好,是ALLANBLOOM也好,他们都主张“保守”和“激进”或“创新”是需要随时随地相平衡的。中国百余年来走了一段思想激进化的历程,中国为了这一历程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今后这一代价是不是可以变成历史的教训?
也许现在力图回答这一问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从钱穆哪里获得的这一份在“守旧”与“维新”中求统一的中庸之道,是否能对于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有所借鉴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开放多元与自我坚守的统一
余英时先生在其文章——《犹记风吹水上鳞》中谈到:“钱穆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26]这充分体现了钱穆学术思想中开放多元与自我坚守的统一。因为“多元”,所以能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因为“坚守”,所以能独立门户、自成一家。
这里,我仍然选择余英时先生问学的例子作一说明:大概在一九五〇年秋季开学不久,我为了想比较深入地读《国史大纲》,曾发愤作一种钩玄提要的工夫,把书中的精要之处摘录下来,以备自己参考。我写成了几条之后,曾送呈钱先生过目,希望得到他的指示。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课外向他请教。钱先生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你做这种笔记的工夫是一种训练,但是你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他的闲闲一语对我有很深的启示,而且他透露出他自己对学问的态度。《国史大纲》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对一部中国史的系统见解,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充分承认别人从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论点、初学的人则应该在这些不同之处用心,然后去追寻自己的答案。用今天的话说,钱先生的系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27]对于这样一部钱先生倾注大量心血的著作,钱穆始终保持了一种学术的宽容与雅量,着实令人佩服。除此一例意外,我们还可以透过钱穆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与顾颉刚、胡适之等人的争论中对于这一点有更为深入的了解。[28]
然而,钱穆先生终其一生,其治学思想始终处于一种所谓的“边缘地位”,没有得到以胡适、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主流学术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家的广泛认可。但是,这一点并不能妨碍钱穆对于自身学术思想理念的一种坚守。说固执也罢,说冥顽不灵[29]也罢,他始终一如既往的坚守着自己的路向。对于这一点,他的亲炙弟子余英时先生有这样的评价:“他并没有陷人相对主义的泥淖。他相信,各种观点都可以用之于中国史的研究,然而学术价值的高下仍然有客观的标准,也不完全是时人的评价即能决定,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了吸尘器中的灰尘。”[30]
儒家之神髓,贵在“忠恕”,钱穆对于自身史学路径的坚守正是其“忠”,而他对于其他学术思想的包容则正是其“恕”。开放多元与自我坚守在钱先生这里达到了一种和谐统一的境界。陈寅恪先生有一句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31]钱穆先生最终能够得以不入其流而终预其流,大抵也应得益于此。
客观之严谨与理解之同情的统一
关于历史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可谓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论题了。中国古代的所谓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尊德性与道问学实际上就是对这一问题在某种层面上的反映。而自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尤其是理性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兴起并占据主流地位以来,似乎历史学已经成为了一门科学。虽然这样一门科学较之物理学、数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而言当归属于所谓等而下之的社会科学一类,但是毕竟也是“科学化”了。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于科学的反观也日益兴起,科学到底是福还是祸[32]、科学到底能否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与挑战,一股新人文主义的潮流已经在各个领域涌动发展。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里,一切普式的解决之道似乎都成为了一种徒劳的努力,尤其是在人文科学(例如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对于这一点,余英时先生这样评价道:最近“解释人类学”和“诠释学”的流行使文化研究转而注重内在“意义”的寻求,诠释学家更有人强调“传统”的特殊重要性。在人文研究的领域中,“传统”正是内在理解的关键所在。因为凡是有生命力的“传统”都必然是变动而开放的,研究者自觉地深入一个文化的“传统”之中,才能理解这个文化的种种外在象征所显示的内在意义。总之,今天研究文化,客观的实证和主观的体会两者不可偏废,因此研究者必须一方面出乎其外,即苏东坡所谓“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必须入乎其内则是元遗山所谓“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出乎其外的道理,人人都懂得,因为这是实证论者所一向强调的。人乎其内的说法,今天才获得较多的人的重视。人类学家所说的“being there”便是要求研究者“亲到长安”。钱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正是主张由内外兼修以求主客统一。[33]钱穆这一当时实属非主流的治学思想在今日的史学界却成为一种发展的方向,所谓“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实际正是体现了钱穆史学思想中主客统一、内外兼修这一大特点,对于我们今人也是不乏借鉴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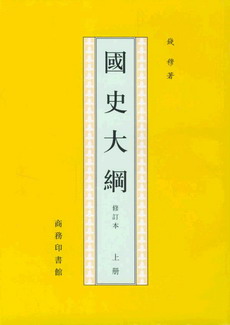
《国史大纲》书影
为了让读者更加深刻的体会钱穆的这一理念,我这里还想举一具体事例加以说明。钱穆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曾经参与了当今风靡一时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论战,这一论战大体分为两派:即以胡适之为代表的《老子》早出派和以梁启超、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老子》晚出派。而在所谓《老子》晚出派当中,对于《老子》其书的具体成书年代,又有诸多说法,并不十分一致。钱穆主张老子应处于孔、墨之后,甚至《庄子》之后,并为此作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和《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两篇专论,后合成一书,取名《老子辩》。而钱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时代背景法、思想线索法和文体研究法等,就是对于从主观和客观两端对于历史问题作一详细推究的尝试,虽然后来胡适之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中对于钱先生的这一探索作了一种方法论层次上的批判,但不能不承认,钱穆在将客观之考订与理解之同情相结合,来力求拨云见日,发现历史事实的真相这一尝试,在史学方法论上是有着重要价值的。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随着西方阐释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的兴起和对于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钱穆这一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出来了。[34]
这一主观与客观的论争问题,用另一种方法阐释,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个“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辩证问题。“有我”“无我”这一精彩阐释最早恐出自王国维《人间词话》。而如果我们将这里理念引入史学领域,钱穆的史学到底应该归入“有我”一派,还是“无我”一派呢?
在就这一问题作出结论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余英时在《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中的另一篇文章——《〈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关于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由于与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没有太大牵涉,我们这里不作具体的说明,只是就文中谈到的胡适之提出的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一解读。此文中谈到的徐复观等人对于《周礼》及其作者的考辩,就带有这样一种先入之见,先设定这样一个目标,随后照此进行进一步的考证,无论其考证再精审,也不过是为了更好的验证这一“先入之见”,而往往很多对于自己的这种“先入之见”不利的信息就被忽视甚至是有意的剔除掉了。这样所谓“大胆的假设”便成为了“妄测”,胡适之深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断不可作此妄语。如果说后人对于胡适之这一句话作如是观,则实在是对于胡适的一种误读。钱穆深谙此道,故而在其毕生的史学研究中,从未做如是之“大胆假设”[35]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来看,钱穆当属“无我”一派
然而,钱穆终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始终以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己任,那么它对于国家、民族,又何以不怀有一种脉脉温情呢?他所处的时代,这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都受到严峻挑战的时代,全盘西化的论调甚嚣尘上,似乎一切中国固有的传统都是落后的代名词,都是中国之所以屡屡受到列强凌辱而无力反抗的根源。不彻底摒弃这一传统,则民族无望,国家无望。而钱穆却并没有融入这一全面批判潮流中去,他始终对于中国的传统具有一种温情。对于我们固有的传统,无论其是好是歹,是优是劣,终究是我们自己的,是民族的神髓所在,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文化符号。日本现代著名的漫画家宫崎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千与千寻》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千寻”在进入了城堡以后始终被提醒着要记住她原本的名字。那么,“名字”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符号。但是,如果我们看了这个故事,我们就不难理解名字对于我们来说体现着一种自我认同。同样,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与其它国家相区别之处,其作用正是这样的一种自我认同。现在有人大谈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试问,倘若我们有一天真的忘记了我们的“名字”[36]我们有何以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呢?到那时,我们的眼里将会是无尽的黑暗与迷茫。对传统文化多一份理解之同情,对古人多一分理解,少一分苛求。站在历史的语境中去走进先人的内心世界,聆听来自远古的跫音,这也许就是钱穆带个我们的启示吧。
在客观严谨的学术规范和方法的指导之下,多一份“理解之同情”,也许我们的学术视野中将会呈现出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
结论

钱穆最著名的弟子之一——余英时
以上,我们就钱穆的学术思想及其对我们今人的启示从五个大的方面做了一简要的梳理和探讨。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中国学术思想史,我们会发现这的确是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无数的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纷至沓来,可谓一浪高过一浪,一波胜似一波。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近一百年处在一个不断走向激进化的时代,中国仿佛搭上了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不顾一切的加速向前。然而,一百年后,我们顾盼神伤,发现已经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在了身后,发现自己充满了迷茫。
然而,当我们考察钱穆的学术思想时,却突然发现,在这样一个迷惘的时代里,钱穆的这一份中庸与平和似乎使我们倍感亲切。正是因为钱穆学术思想中的这样一种“中和”,使得其学术思想在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之后,终于在今日中国这个后激进主义的时代里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传统,重新审视传统史学、重新看待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我们会发现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也许正是近年钱穆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余英时、罗志田等人何以在当今的史学界具有如此重要影响的一个原因吧!
“致中和,天地位”。钱穆先生虽然已经作古,但他的学术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我们这一代人乃至后辈学人一笔宝贵的财富。最后,我还是用余英时在《寿钱宾四师九十》中的一行诗做结,以收束此文:“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37]
主要参考书目:
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书目:
王国轩译注,《中庸、大学》,中华书局,2006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7
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
钱穆,《灵魂与心》(转引)
徐志刚译注,《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赖福顺,《钱穆先生的教学与学术》,见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1990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7(转引)
钱穆,《国史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转引)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史语所集刊》一本二分。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转引)
注释:
[1]由于资料不甚完备,本文主要以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为中心做一简要阐述,如有不周之处,还请方家指教。
[2]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97页。此诗出自余英时《寿钱宾四师九十》,是作为钱穆“先进弟子”的余英时先生对于钱先生一生学术成就的一宏阔的概括。
[3]王国轩译注,《中庸、大学》,中华书局,2006,第46页
[4]寓褒贬于史学写作过程中,如孟子所说之所谓“《春秋》出而乱臣贼子惧”
[5](有些学者径将其概括为“史料派”,我以为不妥,试问那些派史学家不重对于史料的解读,无史料的支撑,又何以谈得上历史学)
[6]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1页
[7]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3页
[8]《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46页
[9]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7,第1-2页
[10]钱穆,《灵魂与心》,第115页,转引自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5页
[11]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3页
[12]徐志刚译注,《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68页
[13]赖福顺,《钱穆先生的教学与学术》,见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第101页,1990
[14]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2页
[15]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2页
[16]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2页
[17]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2页
[18]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7,第302页,转引自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0页
[19]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1页
[20]以致有人径自将其划入“新儒家”一派,余英时先生在其《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对于这一观点作了系统的驳斥
[21]钱穆,《国史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转引自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页
[22]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51页
[23]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54页
[24]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73页
[25]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81页
[26]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0页
[27]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1页
[28]这些史迹在钱穆先生自己写的《师友杂忆》中有具体的描写,这里由于篇幅所限,不能详细展开
[29]白寿彝等人对于钱穆的批评
[30]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3页
[3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史语所集刊》一本二分。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第266-268页
[32]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代表作《全球通史》中提出了这一命题
[33]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8页
[34]可参考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第五章《北大七年》(上)
[35]无论《刘向歆父子年谱》、《朱子新学案》《先秦诸子系年》这类考据见长的微观之论,还是《国史大纲》一类粗线条的宏大叙事之作,其观点都是以充分的论据作为基础的,决不是所谓的“大胆假设”,也似乎少有这样先入为主的定见。
[36]即中国的传统文化
[37]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97页。此诗出自余英时《寿钱宾四师九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