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基本行政区划与《元典章》
蒙古至元八年(1271年),大汗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是为元朝之始。至元十三年灭南宋,三年后奄有全宋之地,完成了旷古未有的大一统。在同一过程中,因军事政治行动的需要,而在各地设置行中书省,并渐渐变为相对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表明地方性的加强。
元代中期,渐渐将地方一级行政区划调整为一中书省和十行中书省的格局。其中十行中书省具体为陕西、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河南江北、辽阳、岭北、甘肃等。
又,西藏地区归中央宣政院所下,甘肃以西又有哈密力、北庭都元帅府、和喇火州之地,皆不属行省。
元代政区层级既多,又采取复式统辖关系,因此而形成一套繁琐的行政区划体系。其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可参考周振鹤教授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一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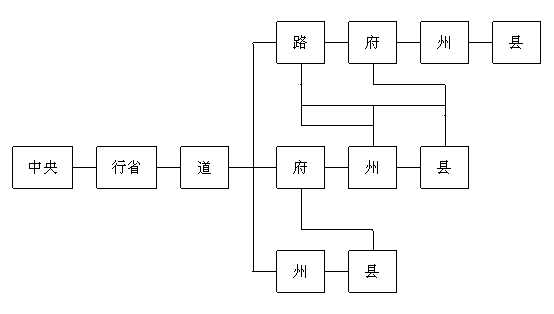
可以说,元代基本行政区划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也很可能是绝后的繁复的典型。
下面说说《元典章》。《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三十九·政书类存目一”叙述“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五卷数”目,曰:
“不著撰人名氏。《前集》载世祖即位至延祐七年英宗初政。其纲凡十,曰《诏令》,曰《圣政》,曰《朝纲》,曰《台纲》,曰《吏部》,曰《户部》,曰《礼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其目凡三百七十有三,每目之中又各分条格。《新集》体例略仿《前集》,皆续载英宗至治元二年事,不分卷数,似犹未竟之本也。”内容、体例介绍得很完整。
不过,目录又指出:“此书”虽然“於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固宜存备一朝之故事。”是优点;“然所载皆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
因此,史学家陈垣在校勘近刻于元刻本《元典章》时,系统地利用其成果总结概括了校勘学普遍现象与方法,写成《校勘学释例》一书,影响很大。
二、对“元代地名误例”条的分析
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元代名物误例”章目中“不谙元代地名而误例”条分为五个条目:
1.所误为历代所无之地名,一望即知其误者也。
2.所误为元时所无之地名,略一考究,即知其误者也。
3.所误为元时所有之地名,而隶属不相应,亦已察觉者也。
4.所误为元时所有之地名,而未指明隶属,则非用对校法,莫知其误也。
5.地名误作非地名,有时亦非对校不可。
其实,这五条可以概括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后人刻抄时将元地名改成其它地名,弄错了地方;第二种将元地方改错了,成了当时不存在的地方或其他名物。第一种可从释例中举一例:“户五五濮州知州元作‘滁州'”,这两地元时都在,只不过相差千里之遥。第二种举“户十八江省行省元作‘江西行省',”“江省行省”当时或后世都不存在的地名,搓得很明显。
另外统计了几项东西:
第一条十六例,第二条十例,第三条五例,第四条五例,第五条二例,共计三十八例。
在这三十八例中,五例为行省名之误,府、路、州二级行政区划有八例,县、府下散州三级行政区划二十三例,基层地名为两例。
由仅此校释类例大略可知:后本较元本错谬颇多,而且比较广泛,大至省、府,小至县及以下,都出了些问题。而其中,而其中,以县一级较小行政区划地名似占错谬的多数。当然,以政令为主体的《元典章》记载必先还小的地名不会很多,而有元一代十大兴盛也会刻错,可能就不应该了。
三十八例中,涉及《元典章》中五纲,具体有:吏部、户部、兵部、刑部、礼部,占了“十纲”中的一半。这些纲目涉及具体公文、诏令,多是上、下层,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公务往来,恐占《元典章》篇幅较大,所以错谬也就不少。“工部”无例,不影响这个结论。其他“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多是中央文书,皇帝诏命,自然准确性较高。
再分析一下这三十八例中地名南北之误例的出现情况。三十八例中,南方地方为十九例,北方地方为十九例,基本一致。不只是陈垣释例拣选时兼顾各地情况,还是《元典章》中本身就“采掇颇详”,汇总全国的政书之要而成。另外,北方地名十九例至少有十一例属于腹里(今山西、河北、山东、京津一带),毕竟政治中心在此,汇编书的作者,与校勘释例者——陈垣,想必也是有意无意地多编了一些罢。
三、造成元代地名谬误的诸因素
有因必有果,有果方有因。《校勘学释例》对于造成元代地名错误的原因归那只是从文献角度所作的探讨。我想,这种产生许多谬误的现象应该是方面的。
首先,应该是刻本不精,简单的刊刻错误导致一些不该出现的谬误。另个角度说,这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如:元本“栾城县”,沈刻是“奕城县”;元本是“邵武路”,沈刻是“郡武路”;等等。这些都是明显的错误,自然是错字、别字,可以肯定。
其次,由于传抄或负责刊刻者对元代史地情况不了解,却妄自窜改,或想当然的去“斧正”。如:元本“湖广行省”到沈本为“广东行省”,后者当时不存在;元本“江南浙西道”到沈本则为“江南淮西道”,后者显然不是当时史实。这种情况,既反映出印刷业存在的一些版本问题,也能看出明清两代的不良学风与某些乱改古籍的陋习。
这种谬误,最可笑的例子是把元本“自李二寺至临清”两地名夹一段运河,改成“自李二等至临清”,或疑为人名,可谓改得简直是莫名其妙。当然,以上这两种错因也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历史原因。朝代更替,时间间隔,尤其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征服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被推翻后,由于民族隔阂、文化差异等原因,不了解、不熟悉这个王朝乃至淡视它,都算是正常的事情。再加上时间推移的作用,出现如此一些不该出现的谬误也是在所难免。
具体的一些典章制度的差异,不同时代的约定俗成,也正是这样产生的。比如:明清两代省下是府,称府已是习惯;而《元典章》中略同于“府”级的路,后来的刻本也称其为“府”。如“重庆路”便称其为“重庆府”。而同路级官职“彰德辅宕”也自然而然地变为“彰德府宕”。
末了提一下,可能还有种简文的想法在里面。“漷州”的“漷”元时用,也许后来想规简一下,就是“郭州”。文字的简化,或用字的流变,在细节上应该也有影响,却是误而有理罢。
总之,分析“元代地名误例”条,对于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自我探究,是有益的。考虑一些材料,与材料背后的制约因素,很有收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