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旨在对《太极图》的作者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首先,本文从比较《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对“五行”思想的不同表达入手,指出二者所论的“五行”思想分别属于不同的流传系统。其次,本文较深入的比较了这两种“五行”思想的异同之处,进而指出:基于这一矛盾可以初步判断,《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决非一人所做。
关键词:周敦颐;太极图;太极图说;五行
作者简介:曹树明,男,1977年生,河北徐水人。哲学博士,200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2005年至今任教于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工作。
《太极图》是否出于周敦颐之手?这个问题讨论了近千年,至今未有定论。似乎论战双方都没有提出一锤定音的证据。不但认为其本源出自道教者的所谓“真脏实据”每每令人怀疑,而且认为《太极图》系出自周敦颐本人之手者的证据同样不能让人信服。前人多已指出,周的好友潘兴嗣所做的《濂溪先生墓志铭》更应该是被读为“……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而不是“……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即它恰好说明周只是写了《太极图易说》(即《太极图说》)、《易通》(即《通书》)两书,而不是像朱熹、李申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太极图》、《易说》、《易通》三书。同时,《宋史·道学传》则更为明确的说:“千有余年,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春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1]显然,这些证据都倾向于认为《太极图》是为周敦颐之外的人所做。那么,到底《太极图》是否出于周敦颐之手?本文拟从比较《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对“五行”思想的不同表达这一内证入手,为解决《太极图》的渊源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一
认为“《太极图》乃周敦颐自己的作品”,那也就认定了《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出自一人之手,则它们两者之间就不会有思想表达上的矛盾之处:“度正把图与说视为一体,传图者必传说,决不可能前人创图,后人作说……这个意见,是可取的。因为《周氏太极图》的意义并不在于那几个圈,而在于那些圈所表达的内容。”[2](第14页)。但事实上,虽然《太极图》和《太极图说》都涉及到了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但在这同一个问题上它们的表述却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显然,这是我们推断《太极图》作者问题的一个真正的突破点。
最早提出《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上有很大差异的是朱熹的弟子胡广仲,他在给朱熹的信中首次提及:“《太极图》旧本,极蒙垂视,然其意终未能晓……及五行相生先后次序,皆所未明。”[3](卷二,第15—16页)。朱的回信对胡的其它疑问都有明确回答,但对其改动旧图的五行问题却只字未提,颇为耐人寻味。其实《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上的不同始终是困绕朱熹的难题,乃至于朱熹不得不绞尽脑汁的通过对朱震在其《汉上易传》所录之“旧本《太极图》”(见附图一)的改动来调和这些矛盾,而他这一改动的目的无非是要使新图能够迁就和迎合《太极图说》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从而弥合二者之间的原有矛盾。
要找出《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上的差异,不妨先从旧本《太极图》说起。本文同意毛奇龄的观点,以为朱震在其《汉上易传》所录之“旧本《太极图》”(见附图一)最接近周敦颐所传之原图,而经过朱熹改定的通行本《太极图》(见附图二)则融进了朱熹的个人思想,不能代表《太极图》的原貌。这是因为,尽管朱熹一再声明他在对“旧本《太极图》”的改动时都“皆有据依”(同上),但朱熹显然对旧本《太极图》的改动根本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改动并没有任何版本上的依据,而且还因为旧本《太极图》所表述的“五行”理论从本身来说是自足的、没有改动的必要。他关于旧本《太极图》“阴静”图先于“阳动”图的序列是不合理的观点(同上),就只是其基于儒家立场的一家之言,其立论的前提是《太极图》一定代表儒家的立场(这无形中是在承认《太极图》就是周敦颐本人所作)。事实上,这一立论前提恰恰有待证明。相反,该图与道家(包括玄学在内)静体动用的基本思想的一致性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由于并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表明朱熹对《太极图》的改定确实忠实于原图的基本思想,本文仍以旧本《太极图》作为比较《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理论异同的底本。同时,本文也力图指出朱熹对旧本《太极图》的改动仍然没有彻底的弥合《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上的差异,反而制造出了一些新的矛盾。
旧本《太极图》的第二、三层图专论“五行”,而要准确把握该图的“五行”思想,需要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该图的第三层图所表达的思想只是对其第二层图蕴涵思想的具体展开,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也是我们把握《太极图》所表达“五行”思想的基本立足点。在该图的第二层图中(被后人称为水火匡廓图),其左半部的阳抱阴(为二)的半环与右半部的阴抱阳(也为二)半环再加上中间的虚无圈子这五者共成一个整体,而这正是第三层图中“五行”的雏形。显然,该图中的上述五者之间是彼此共在的关系,一损俱损,一存俱存。尽管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同层次上两两之间的相互蕴涵、相互转化的关系:就每一半图而言,生者为母,成者为子,母子之间又总是在此消彼长,相互转化;而在整体上左右两半环又形成了更高层次上的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的关系,乃至于循环无端。进而,在作为这层图进一步展开的第三层图中,上一层图中左半部的阳抱阴在此图中演化为火与木的相互蕴涵与转化的关系;而上一层图中右半部的阴抱阳在此图中则演化为金与水的相互蕴涵与转化的关系;上一层图中心的虚无圈子则对应着第三层图中居无定位,寄体于另外四者之中的土。因此,在第三层图中,在整体上,同作为母的木与金和同作为子的火与水分别两两对待;而在各自的一侧,则是母子之间(木与火、金与水)的各自蕴涵,各自相互转化;而土则把它们相互联系为一个整体。应该说,《太极图》对“五行”思想的表述还是相当清楚的。至少有一点很明显,该图的“五行”之间不能被理解为是从此到彼的单线传承关系。该图以连线的形式把木火金水都与中央土直接连成一个整体是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因为在这里,土本身就只是一个虚位,它就寄身在其它四者中。
可是,作为对《太极图》的解说,《太极图说》中论“五行”的内容则为:“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同上,卷一,第2页)在这段文字中,“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这句话颇值得注意,也是明显与《太极图》本身有矛盾的所在。这句话讲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五行之间存在着合顺序的单线流变关系,一是在强调这种五行流变与四时更替有内在的联系。这种把五行顺次流变与四时更替相联系的做法其实还是渊源有自的。据白奚先生考证,早在稷下学派兴起时就已有了“五行说同四时教令的阴阳学说的结合”的说法[4](第257—268页),见《管子》的《幼官》(即《玄宫》)、《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该理论后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发展,直至《春秋繁露》、《白虎通义》乃趋于定型。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木→火→土→金→水的顺次流变所体现出的生→长→化→收→藏的属性来对应春夏秋冬时间上的自然流变节律,进而把这种顺序绝对化。为了处理四季与五行之间不搭配的矛盾,它又认为“土”为“五行之主”而“兼有四时”,不主一季(五行与四时搭配问题的具体演变过程非常的复杂,也始终是困绕前人的难题。本文只取《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的说法为定论)。以图表示,则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东→南→中→西→北,仁→礼→信→义→智(在这里,五德与五行的对应排序有多种说法,本文只取为后世所接受的《白虎通义》中的说法)和春→夏→(季夏)→秋→冬。至此,该理论在经过反复的变动中已经相当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人确实真诚地以为,五行与四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以上理论是说明五行与四时相配合的唯一“合理”的固定模式。然而,《太极图说》以此理论作为对《太极图》中“五行”思想的解说却显然是不成功的:原图中“五行”所“展现出”的顺序却是水→火→木→金→土(诚如上文所反复指出的,这一“顺序”,本来也并不表示五者之间一种单线式的先后顺序),这应该是说:该图中水火、火木、金木、土水之间都两两相克,难说是“顺布”。当然,它们在整体上也绝不存在与“四时行焉”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恰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不过照数目的次序,每年的四季,应该先冬(水),次夏(火),次春(木),次秋(金)。为什么五行的次序与四时的次序不合?关于这点,他们没有解释。”[5](第312页)事实上,并不是他们没有解释,而是这种五行理论本身就与四时流变无关。在《太极图说》之前也没有人将该五行模式与四时更替进行比附。
显然,旧本《太极图》所要表达的思想原本就与“五气顺布,四时行焉”的说法无关,《太极图说》以“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来解说《太极图》中的“五行”思想似乎是关公战秦琼,不着边际。这一矛盾提示我们,《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不会出于同一个人之手。
二
其实,五行思想源远流长,它的具体流变也相当复杂。在五行思想的发展中,始终有两种五行思想系统各自在独立流传而并行不悖:其一注重揭示五行之间以时间为主线的生克流变关系,它可以和四时更替结合在一起;其二则注重揭示五行在整体上的对待关系,不能和四时更替相结合,而后者正是旧本《太极图》所要表述的“五行”理论。该五行理论以《尚书·洪范》中的五行序列为依托,在今本《易传》中,它以“大衍数”的形式出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易传》中并没有这一段,证明它是晚出的),在两汉之际渐渐形成。《汉书·五行志》有:“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6](第463页)。这一说法抛开其中可能有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不谈,表明在汉代确实存在两种各自独立的五行理论。继而,《汉书·五行志》就引述过这种附在“左传说”之后的“五行说”:“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阴阳易位”(同上,第464页)。这最后一句是说,以上的“五行”生数与五相和变成了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以上的“五行”生数与“五行”成数配合,其阴阳属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该理论中间经过《太玄》的发展,在《周易参同契》中有了成熟的应用。该“五行”理论在后来又发展为突出强调五行之间在数上的结构性与一体性的“河图”、“洛书”模式五行理论,广为道教,风水、相术等理论所借用,却基本上总是游离在儒学以尊德性为本质的正统理论之外,以至于清代学者如黄宗羲、胡渭等人始终视之为异端,想要把它排斥出儒学的正统传承之外。
那么,以上所提到的两种“五行”理论是不是可以合二为一呢?也就是说,《太极图》是否想要在图中把这两种“五行”理论结合在一起呢?诚如前人的一致看法,两种理论一个重在强调五行之间超时间性的,结构上的对待关系、共在关系,而非五行之间“各主一季”、由此到彼的单线传递关系;一个则重在强调历时性的,由此到彼的流行关系。初看二者颇有一言体,一言用的味道,似乎有二者可以结合的理论基础。但事实上,在朱熹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尤其没有想到要把它们结合在同一幅图里。基于它们各自流变顺序和所对应方位上的对立,在不改变各自所对应的图的模式的前提下,二者起码在以图的表达形式上是无法调和的。这也是朱熹不得不去改动旧本《太极图》来弥合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
在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收有署名为前人的《五行说》,其中就提出了这两种“五行”理论的比较:“五行之序,以质之所生而言……则阴阳之气各盛,相交相抟凝而成质;以气之行而言,则一阴一阳往来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几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则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之序若参差而造化所以为发育之具,实并行而不相悖。盖质则阴阳交错,凝合而成;气则阴阳两端循环而已。质曰水火木金,盖以阴阳相间而言,犹曰东西南北,所谓对代(待)者也;气曰木火金水,盖以阴阳相因而言,犹曰东南西北,所谓流行者也。质所一定而不易,气则变化而无穷,所谓易也。”[3](卷三,第81页)。这里,作者只是在泛泛的比较两种“五行”理论的不同,但他并没有提出要在图上将二者结合起来,而朱熹则是明显的借鉴了此说,要把它们融合在同一幅图里。他在对经过他改动过的新图进行解释时说:“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形于天者也。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阴也,火金阳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又统而言之,则气阳而质阴也。又错而言之,则动阳而静阴也。”(同上,卷一,第28页)无疑是这一努力的最好体现。当然,前提是他必须要对旧本《太极图》做出改动,从而使新图能更好的迁就于《太极图说》对“五行”理论的表述。
我们说,朱熹对旧本《太极图》的改动是不成功的。且不说原图的作者是否真的就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是在经过朱熹改定后的通行本《太极图》中(显然,朱熹对第三层图的改定如把原图中由水经土到木的连线改为绕土而过的直线,就是要努力体现出该图木→火→土→金→水单线的五行流变顺序),我们也只能看到一个非常曲折而非“顺布”的五行流变顺序。看得出,虽然朱熹努力想在改定后的新图中体现出《太极图》与《春秋繁露》相一致的五行和四时对应的五行流变顺序。但他仅仅通过改定原图中五行之间连线来体现这种一致性的努力却并不成功。经过朱熹的改定,固然可以体现出“五行”之间单线的流变关系,但是为原图所强调的以土为中心,“五行”之间浑然一体所谓“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的两相对待而又整体统一的思想(在原图,这一思想是通过中央土与其它四者之间分别直接的以线相贯通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却被破坏了,这也导致了太极图第二层图与第三层图在表达内容上的割裂。此诚所谓得之于此而失之于彼。至少给人的感觉是朱熹是在把两套原本无关的五行理论生硬的扭合在一起。
由上可见,在对五行理论的表达上,《太极图》与《太极图说》是不同的,这充分说明,《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不会是由同一个人所做。前人认为《太极图》出于陈抟而非周敦颐的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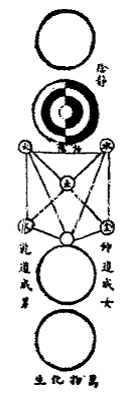
附图一
朱震《汉上易传》所录之“旧本《太极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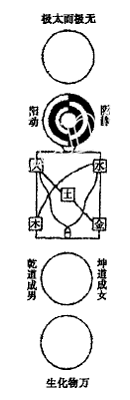
附图二
经朱熹改定后的通行本《太极图》 |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第36册[M].北京:中华书局.
[2]李申.易图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4]白奚.稷下学研究[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班固.前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
原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