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十年(公元433年)谢灵运因游放无度为有司所纠,继而被捕,随后即以欲行谋反之罪在广州被杀。后之学者多为灵运之死鸣不平。然元嘉七年,灵运即被会稽太守孟顗上表告发有“异志”;灵运被诛三年后,刘义康矫诏诛檀道济时又称:“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显然,这才是谢灵运真正的罪名。惜乎《宋书》语焉不详,今为一一考证之。
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二:
灵运之居也,雅不治职。前是,临川内史司马协少子来投义,故灵运舍诸正寝为居,始如酣笑,久而不止,非隐其事,讽主者以黩货劾焉。江州部从事收录运,乃徙广州,敕于南海行刑。
司马协其人《晋书》及“南朝五史”等书均不见载。《俄藏敦煌文献》第四册Ф242《文选》残卷灵运《述祖德》诗所存唐人注云:灵运“于临川取晋之疏从弟子养之,意欲兴晋。后事发,徙居广州。”以此与《建康实录》相印证,知司马协当为前朝东晋宗室。尽管我们不清楚这位复娃司马的晋室“疏纵弟子”前来投义的具体含义是否就是“意欲兴晋”,但这很容易被执政者理解成公然的示威和反抗,因此导致“以黩货劾焉”的结果。“黩货”以及上所云“游放”都不过是托词而已。灵运在临川的遭遇不是孤立的,是这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延续,也是一场极为敏感而又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
明乎此,亦可判别灵运《临川被收》诗等作品的真伪。或以为本诗与灵运的思想和政治态度不符,风格浅露,系当事者的伪造。学界持此说者不在少数。假如我们了解灵运被劾的真相,就会理解本诗所抒发的情绪了。尽管灵运本无意尽忠司马氏,但在被弹劾的过程中,他们的角色却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他“被认定”与前朝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因此,其立场也就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了:既然作了刘宋朝廷十馀年的官还被汉成了不可信任的前朝外人,还有什么理由阻挡他在把自己的情感转回到东晋王朝上来呢?也即是说,谢灵运的“忠义”是特定环境逼出来的!他的《临终》诗绝口不提自己多年事宋的经历,反而深情地追忆被自己久已遗忘的东晋王朝,这使他临刑前胸中充满了悲剧英雄式的高尚情感。诗人是在以他特有的想象力获取从容就义者才有的那份慷慨和激越,以此克服内心的恐惧。至于说“风格浅露”,此诗乃咏怀之作,激奋之下水择辞而出,符合其冲动而易失控的个性,自与其山水诗风格有别。
《宋书》本传载赵钦云:“同村薛道双与谢康乐共事,以去九月初,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先作临川郡,犯事徙送广州谢,给钱令买弓箭刀盾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篡取谢。”灵运以此弃市广州,时为元嘉十年。由于人们误把“去九月”理解成了去年九月,故使灵运最后两年的行迹多有舛误混乱处。其实灵运元嘉九年绝不曾离开临川。“去九月”的去字并不专指去年。灵运《自理表》:“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以稽太守臣
二十七日疏。”去月,即指上一个月。以此类推,则“去九月”实即上个月是九月的意思。如此,知灵运之被收当在元嘉十年八月前后。同样,既云“去九月”欲劫灵运,则此时已是十月,其被斩又当在这之后。清康熙年间吴乘权编《纲鉴易知录》,系灵运之诛于元嘉十年十一月,惜未有论证。但其结论与本言语上述推理相吻合。
承建安文学思潮之绪馀,抒情于人生之意义,其地位空前上升。降及南朝,曹植辈还顾及的“礼防”更彻底崩塌了,对此应视作南朝士人抒情的新特点,两汉以来图精养生观在南朝出现断裂,这是地域文化差异使然,而此种差异自然要落实到文学创作主体来考察。
五、与图精养生观彻底决裂文化背景下的南人之抒情。
这归根到底应从南士儒家经学贫瘠来找原因。南人在文坛凯起,非在深厚的经学氛围中生长的南人,其人生观、人格及生活情趣都表现出与北人不同的特点,情感恣肆,标新立异,更接近于自然本真的生命状态。南朝文学的“抒情”,正是在这样新的文化学术背景下展开。
沈约是南人文学开风气的人物。萧纲的文学主张也可一言以蔽之,曰:突出文学之抒情本体;是宣泄性的,无所顾忌的,他与图精说完全不同;他是凭藉宣泄,以重建心理平衡,并达到各种情感的满足。梁元帝萧绎文学观与萧观大致相同,图精之禁忌,至此一变而成为内心之享受。萧子显讲“委自在机”与“独中胸怀”,抒情便成为文学真生命之所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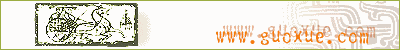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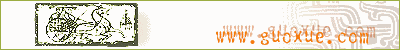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