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쵼��
�δ�����ѡ��ʿ�������������Ϊ���������ͬʱ���ֲ������������쵼���ƶ���ʽ���Է����������������ͣ�����������Ȩ�ض�����ʧ�ء����ּ����쵼�ƶȣ�Ҳ�Ƕ����ˡ������á��ƶȵijм̡�Ȼ�����Ƴ�����û�н���ø������������ƽ�⡢�Ժ����ͻ¹������������Ƶ�һϵ�����⣬�����쵼���ѱ��ƻ����š������������˵ľ����ѵ�����ϣ������ؽ������Ƶġ��������쵼�����У���������Ժ�������١����Ļ���ר����������Ժ���⣬���ԣ������в����꾡���ܡ�
1�������쵼�Ƶ��ؽ������ơ�
��̫��ӹ¶���ĸ���ж����Ȩ���ڲ��������¾���Ȩ���桢�ȶ����ֵ����⣬�ⲿ�ֱ�����Ա��������ơ������ȵ�ǿ�л��ŵ�Σ�Ѿ��棬�ٷϴ��ˡ��������Σ��֮������õ��ֶ�Ҳ����ʱ�Ե�Ӧ����ʩ���������쵼�Ƶȵȹ淶�����ƶȣ���δ�����뿼�ǵķ��롣
���ȣ�̫��Ϊ�˱��ִ����ҺϷ���ȡ��λ����ͳ�м���������������ʱ�ڵ���λ����ʡ����ߡ�κ���֣�ȴ������������Ȩ���������Լ������ĸ��������գ�֮���С�Ǭ�¶��꣨964�����£���������κ���ಢ�գ�ͬ�£����հ��ࡣһֱ���������꣨973�����£�̫������������мӣ�����ֻ�����ն��࣬���ʱ���������ʮ�ꡣ��Ȼ������һ�Σ��������쵼�Ʋ�δ���Խ�����������Ǵ���������δ���һ���ƶȹ����ڡ�
�������쵼�Ƶ��γ����Բ�֪���µ�����Ϊ��־�ġ�Ǭ�¶��꣨964�����£�̫��Ϊ�����ø��֣��Ʋ�֪���¡��������ơ���Ѻ�ࡢ��֪ӡ�����������á��������ࡷ��5�������ն���˥������쵼��Ҳ��Ӧ�ط�չ��ȫ�������������꣨973�����£�̫��������گ��ʹ��֪���»���������ͬ����������ִ����Ȩ�������հ������Ѧ������������Ϊ�࣬��¬��ѷΪ��֪���¡����ˣ��������쵼����ʽ����ȷ����
�����쵼�ƴ��¹᳹����ԭ��һ�������������ơ������ش������������������������鶨��Ȼ���౨�����ڶ������ࡰ����֪ӡ�����������ʡ����ʹ��ÿλ�����ڴ����ճ�����ʱ��������ͬ�ȵ�Ȩ������ʱ����֪����Ҳ��Ԥ���������֮�У��硶���ࡷ��374�أ�����ʡ�ԣ�������ʡ���֣����������������յ��ʡ����ҡ�گ������ةȨ������ӡ���ʡ���
Ϊ�˱�֤�����쵼�Ƶ�˳���᳹ʵʩ��һ��˵����Ҫ����֮�������Ĵ�����ͬ�����ö�λì�ܶ�����ͬʱΪ���࣬��Ȼ��Э���������������꣨1047�����£�����ִ��Ϊ�����࣬���£������Ϊ�����࣬Խ���գ����������Ϊ����ʹ����Ϊ���ɹ���ʷ�ԣ����ִ�������˳����۲��ϣ�����ͬΪ���ࡣ�ʸ����ɡ��������λ�Ҫ��ְ�١�1֮76��
2����������
�δ����ೣ���Ա������ǰ�ڣ�������������ͼ����࣬ʷ��ְ֮һ�㶼�Ǽ��Ρ�ż�����������ʱ���γ���������⣬̫���ڿ������꣨976��ʮ�µǻ�����Ѧ����Ϊ�����ࡢ������Ϊʷ���ࡢ¬��ѷΪ�����࣬Ѧ����ȥ������������Ϊ��������棬���ಢ��ľ���һֱ������̫ƽ�˹����꣨982�����£��������Ͷ��꣨1055�����£������岩Ϊ�����ࡢ����Ϊʷ���ࡢ����Ϊ�����ࡣ�����ڸ��ƣ�����������Ϊ���࣬���ָ���Ϊ̫�����ס�����ة��ȣ�����Ա������Ҳû�г������ˡ�
��֪���µ�Ա�����ڶ�������֮�䡣�γ���һ��ʱ��ά��һ�ࣨ���գ����Σ�Ѧ�����������ס������ţ��ľ��棻Ѧ�����������ס�¬��ѷ�����ڼ䣬�ֲ����֪���£����������������岩�����졢���������ڼ䣬ֻ�г��һλ��֪���£�����һ�Σ����������꣨997��������һ�ࣨ���ˣ��IJΣ������桢�����������������죩����������ڸ��ƺ����������ɡ��������ɡ�������ة��������ةȡ����֪���£�ʵ���������ö����IJΡ����λָ���֪�������ƺ�Ա������һ������֮��ҡ�ڡ�
�δ��������ʡ����Ա������Ϊ�������Ƕ�����Ρ�Ԫ�v���꣨1087�����£�������������˵��������ʡְ�£����������һ�㣬�������ࡢ������������ԱΪ����������ࡷ��403��������������ԼҲ��������������֮�䡣
3����������ڡ�
�δ���������ڣ�û�����Ĺ涨�����ڳ��Ĵ����ʮ�꣬�̵Ľ����£���ʷ��Զ����λ26�꣬������ֻ��4���¡��δ�������������ڶ���1�����ϡ�5�����£�����2��3�����Ϊ������Ԫ�v�������������������������Ժ���̫��̫�����ˣ���˵����Ҧ�硢�έZ����������꣬�������ļ������룬Ȼÿ������ꡣ���������ࡷ��458����������ô��Ƶ��ε�ʵ����˵���������ڵ������Ǻ������ģ���
�����������������ࡣ�δ��Ķ�������в̾�����������������ա������������������������ļ���ʿѷ�����岩���ˣ��������������P�������͡������С���������ϡ���ִ�С�����������ʯ�������ʡ���֮ͦ����ʤ�ǡ����úơ��ſ����Զ�����������˼�ˡ��¿�����ʷ�ơ�������֣��֮�����м���DZ���ˡ�
һλ���ֻ࣬�����������λ������̸��������Ϊ���ʵ۵ġ�ί����ɡ�������ʵ��ʵ������ν������ר�𡱣�����������ࡷ��230�������ڼ�λ�������킠����Ҫ�ȵ����࣬��֮���ɣ�ʹ��������˾���٣���˾������ȡ���������¶����ӡ��������ࡷ��42�������������ԣ������ࡢ���ܣ���֮͢��ί֮�����ɣ���֮����������Ҫ��������Գ�ֵ����κ�ί�Σ������ࡷ��43����Ԫ�vʱǩ������Ժ��������������˵���������ش����˾���������ȥ�ͣ����ﲻ�����������ࡷ��467��������һ��dz�Եĵ��������������ף���Ҳ��������ɽ�ÿ�����������39�������š�������ʷȫ�ġ��������ܽ�̫�泯���˾�����˵��������ʼҲ��֮��������Ҳ��֮�á���֮������С�˲���������ѡ����֮�ã�����Ӿٵ��Ծ���ְ��������١�������֮�ෲʮһ�ꡱ֮�����ӣ�˵�����Ծ��ζ��ɹ�Ҳ���������ࡷ��12���������ڻʵ۵��ɼ�֮�ģ���Ȩ����Ȩ�ij�ͻ���ʵ�������������������������ø��������ʱ��������Ǩ�ƾ��Եù���Ƶ������������������̫�ڶԴ������ǡ���֮Ϊ��Ա������֮�����ˡ��������ࡷ��25�������vԪ�꣨1034��֪��ھ������ʱ����ʮ�顱����һ�ƣ�
����Ǩ����Ƶ����������ߣ���֮���ţ���������̫�涨���£����ܳ����������꣬ʼ�����մ�֮����ʮһ�꣬ʼ��Ѧ���������״�֮��̫����λ��Ωһ��¬��ѷ��������������ա��Ժ�ʮ�����У����������࣬Ȼ������Ω��P���������������������͡��������ˡ�����ʱ�����߾������ң����߾����ʡ���ǽ������࣬�Գ��Ҳ�����ھ�����ǰ������Ǩ�ģ�Ω���졢�����С���������ʿ������������ѡ���������ʮ���꣬����������������ʮ�ꡣ�˶�����λ֮�գ���������֮˵�����Դ�Ȳ��ݣ������䣬��������Ȩ��Ҳ���������ࡷ��114��
������˴���ʵ��������˵���γ������μ������ڻʵ۶���������Σ������Σ����Գɹ���Ϊ���γ������������ε���ͼ��棬��Ҫ�ʵۺ������˫��Ŭ�����ʵ�Ӧ�á���Ȳ��ݣ������䡱������Ӧ�á�������Ȩ����
�����������ͲĶ��������ࡷ�����������õ����Լ���ְ��Ч��˵��
��ʼ��λ������������֮������ʮ�ˡ������������˽�֮���Բ�����֮��Ҳ��Ȼ��ؽ��ؽ�գ����ܳ־á���Զ���塢���꣬���߶������꣬�����ֲ���֮��Ψ���ļ�����λʮ���꣬�м����ն�����֮������������ݣ�ʼ��֮���£�����Ҳ�����ꡣ����֮�ݣ��������ա���������ᣬʥ���������ؽ���Ϊ��Ȼ�������������ʼ��֮�����価�ͣ�����֮��֪���й�����ν�����������䳣Ҳ�������ö���֮�����ƷDZ��¹���֮���������г�����֮���ӣ�����֮������������ɡ�����������һ��֮�Σ�����������֮�Σ��������ӡ��������ڶ�����Ҳ����֪����Ȼ����֮������֮����ʹ����ְ�ӣ��Ⱦ��ӣ��ش�֮�������ɡ������ˣ��������������ɹ��������вģ��ɱ�������֮�̣��ؽ���ǿΪ����������������֮ı�����ε��ͲĶ��־ã���Ң˴֮�����Ѽ��ӡ�����ȫ���ġ���164��
��������һ����ı��ֻ��DZȽ����˳Ƶ��ġ����Ͷ��꣨1055�����£����ڶ��Ӽ��佱�������岩�������Ӽ�Ի�������¼�֪����֮�Ͷ���֮����֮����֮�ᡢ��֮�ã�Ȼ�������ɹ�������һ���Խ�֮��δ������һ������֮������̫ƽ֮����δ�����Ҳ�������ڶԴ˼����ɣ������ࡷ��180��������Ϊ�������ӳ��µ���ں֮�ԣ����ԣ���һ��ʱ�ڶ��������������Ҳ�ͱȽ϶ࡣ
һ��˵�����ʵ��вŸɣ��ܹ�����ס�������ӣ��������������࣬������λ��ʱ��ͱȽϳ������׳�������������������ڱ��γ��ں����ڣ�����ٵ��������Ӷ��DZ���ǰ�ڵġ�����������ʱ��ϳ���1006��1017����κҰ�����ʫԻ����̫ƽ�������������������ʮ���������������¶���ұ��3������ĩ�������������Ѿ�ʧȥ�۱�����������ڣ�������ʵ۵��ɼɶ��Ƚ϶��ݣ�������ΪȨ���ɱε��������ڳ��á����ھ�����̾���������ʷ��Զ�ȡ����ڶ���������ʱ������Ϊͻ��������ʱ��ʷ�ܿ������ʵ������ר�ƣ������¼�λ������ʮ���ˣ�����Լ���ί֮�����Թ��鲻�ݶ�ȥ��������־����������ʷ����385���ܿ���������ʯ�������2ͳ��˵�����������࣬�Խ�¡Ԫ����Ԫ�v���꣬һ����ʮ�꣬����ʮ�ˣ���Ԫ�v���������������꣬��ʮ���꣬����ʮ���ˣ�������ǰҲ����
����רȨ��һ���̶��ϲ����˻ʵۣ���ô��������λ�����ݱ�Ϊ�����ƣ��������һ������̬�����ң�������������Σ�յ���Ԩ����ʱ�����Ȩ����ʧ�أ�Ȩ������ʧȥƽ�⣬���ֵĺڰ���֮����������������·����ڱ���ĩ�������ʱ�ڡ��������ۼ����쵼�Ƶ��ƻ�ʱ�������漰������ʵ����
�����������������������ھ��������������̡��������ı仯���̡�����������ǰ���ʵ�������֮���нϺõĺ�����ϵ��������������ȶ���ʱ��Ҳ�ϳ������������Ժ�������Т��ʱ�ڣ��ʵ�������֮��IJ��ɼ����Ȼ���ֹ��������������Ȩ�࣬����������Բ�����λ��������ѡ����Ƶ�������κ��ڣ�Ȩ�����ִ��������ʧ���������������ʱ��ò���ʱ�����ơ�
4�������쵼���С��Ͷ���ͬ����ԭ��
�����쵼�ƣ�����������ֲ�������ij��֣���һ�Ƕ��������Ϊ�飬�ᵳӪ˽������Ƕ�������������������ݡ��������Ķ��ǡ�Т�������������֮������ĺ�����ϵ����ȡ���ӡ����ӺͶ���ͬ��С��ͬ�����͡�֮��˵����ִ�������࣬�̵��Ͷ���ͬ����������ʷ����391���ܱش������Ͷ���ͬ����Ҳ����������֮�䡢��֪����֮�䡢����Ժʹ��֮�䡢����������Ժ֮��ȵȣ���������֮�䶼Ӧ�������𡰺Ͷ���ͬ����ԭ���Ͷ���ͬ����ǰ��һ����һ��Ϊ����Ϊ�������ǡ��͡��Ļ�����˫����Э����������ϵ���������ܹ����㼺��������ͬ���ͣ��ɻʵ۾��ϵ��ȡ����ƣ�����Ȼ�����������֮��Ĺ���������ϵ��
���������ݡ����Ķ��ǣ���͢�����᳹ͳһ��ʩ�����룬Ҳ����ʵ��͢�ķ�������Ʊؽ��Ͷ����Ĺ���Ч�ʣ���Ҳ�ǻʵ�����Ը�⿴���ġ�������֮����ֲ��ɵ��͵�ì��ʱ�����߰���˫�������������������ֲ��������Ա�֤���������ԺС��Χ�ڵ�Э��ͳһ�����ڴ���������꣨1014�����£�����ʹ����������Ң�ź����ܸ�ʹ��֪�ھ�ա�ԭ������֪�ڱɱ���������Ϊ�ˣ��ڻʵ���ǰ���߳����״������������ǰ�����ӡ���������Ϊ����Ժʹ�����쳣���ͣ�����С�����������������������������ʾ��֮�������ࡷ��82�������ھ��v���꣨1037�����£����������ļ�������������֪������緺Ͳ��벢�գ�ԭ�������ļ�������������ϡ�������������������۵�ǰ������������ļ�����������������ѳ����ɣ������쵼�ƾ���������������һ�𱻰��⣨�����ࡷ��120���������������꣨1046�����£���֪���������Լ�Ҫ��������ܸ�ʹ����Ϊ���������顰���¸��ԣ�������ֲ�����������ǰ�����н�ʧɫ������������ܸ�ʹ���ȵ���λ�á��������ࡷ��159���˺�������Ȼ�������۵�ǰ�����������£��ֲ������������˫˫����ְ�������ࡷ��160�������ڼεv���꣨1060�����£����ܸ�ʹ��ꬰգ�����������ʹ���ԡ���Э����������ʧ��ɫ���������ࡷ��191����ͬʱ����ִ������ʱ�������Ƿ��ܹ�Э������Ҳ�DZ����ǵ�����֮һ��Ԫ�v���꣨1091�����£�����������ة����˾�ɼ�Ȩ�����������Ϊ��������ʷ��ةʱ�������������ɸ�Ң�ᡢ֪ͬ����Ժ�º����壬����������ִ���������ֿ�����̽Է�������ִ���������˵����������Ϊ�ҹԲ����£�������ͬ�ң�����ȻҲ������ʥ����������������֮����϶�����ߣ�������ܡ��������ղ�����ǿͬ�����������¹�Ҳ������ˣ������Ϊ���������ޡ�Ϊִ���������ࡷ��455����
���Ͷ���ͬ���������ϵ�Ǻ���ʵ�ֵģ�����ʱ�ڣ�ż������Ҳ�������������뾰���������ۼ������С�רȨ֮˽���������С�����֮����ʱ������˵������������գ�Ȩר���أ��������½�֮���������£��Ա�ʿ��������¡��������ʹ��֮����������Ω����ֲ��֮�磬���Ҿ�ͬ������֮�塣���������ࡷ��47������ʷȫ�ġ������ǽ�Ϊ�䷶����������Ϊ���͵���������䳯͢�ö���Ϊ���ࡢ������Ϊ��֪���¡���������Ϊ���ܸ�ʹ��ŷ��������˵��������Ϊ����������ع�أ�������������Ŷ����ɣ�������������ֱ����������������������Ϊ�ԣ��ȸ���ͬ����Թ��ھ��ң������������죬�������£����ӡ�������������������£�������������֮������ν�����ع��Ӷ����뼱�ޱ߱��������Ͼ��£����������ز�����������䨣��������֮��������ˮ����£�����������䨶���������������������������䨡����������ࡷ��155�����˾���Ϊ�����Գ�������������ȴ��ͬ��Э������ͬ�����ˡ��������¡�����������ȴ���������ʶ���⣬������Щ���϶�Ϊ����������Ϊ���120�죬�����͡����������ڶ����������꣬��һһ���ų����͢�����磬Ԫ�v��䷶����Ϊ�����䡢����Ϊ������ة������־Ȥ����ϡ�����������㼺��������������䲻����ơ��������ࡷ��429����
����������������ϵ�������Ͷ���ͬ���ߣ�ʱ��Ҳ�Ǻܶ��ݵġ�����ʱ���������ڻʵ۵ĵ��ڡ�������ì���ƺ⡢Ȩ��IJ��ݵȵ��ֶΣ����ֶ������ӵ�Э��������ϵ��
5����֮��Ļر��ƶȡ�
�����ˡ��Ͷ���ͬ���ļ������ԭ�ͱ������һ�п���Σ�������ԭ�����Ϊ���ء��⽨ר����ᣬ��ͨ������£���ȹ���硱ʢ�У�һ�˵õ�����Ȯ���졣�δ���Ȼ���ܸ����ٳ���ȹ���硱��ͳ����Ϊ������������ص������������ͷ�Χ�������ˡ�ȹ���硱�����С����ǣ��δ�ͳ�����һ��ԭ�������������߲��Ա֮�����ʵ�лر��ƶȣ���ֹ���쵼��ġ�ȹ���硱�ͽᵳӪ˽��Ŭ���������ܹ���������ģ��ֲ�Σ���������쵼�Ƶ��������С�
�����Ƕ�����֮��Ļرܡ����渴�ӵ����ݹ�ϵ����һ����ÿ�ζ���������ʱ����ע������߶�����������ְ�ڼ��Ϊ��Ů�ҵģ���������֮�صĴ��������Լ�����˵����Ҫ��رܡ�����������䣬���ܸ�ʹ�Ӽ�Ů��֪��������֮�ӣ������������ϣ������Ӳ��ɹ��¡��������ࡷ��159�����������꣨1043�����£��Ը���Ϊ���ܸ�ʹ��ʱ����Ϊ����ʹ��ƽ���£�������������Ů������������࣬�ϲ��������������ʹ��������������ࡷ��142�����������꣨1070�����£������ʲ�֪��������ʯ������Ϊ����������ʯ�ش�˵�������˳��ҡ����Ծ�Ҫ��رܣ������ࡷ��214�������£��������������Ϊ��֪���£�����ʯ�ٴ�ǿ�������볼�����ӡ������Ǹ������Ϊ���ܸ�ʹ�������ࡷ��215����Ԫ�v���꣨1090�����£���͢����������֪ͬ����Ժ�£�������ĵܵܺ�����֮�ޣ�����֪����Ժ����̵�Ů���������м�ӵ�����ϵ��������������գ����������������ࡷ��439����Щ��ϵһ��˵�����ʵ�һ��Ҫ�Զ���������������������ά�����رܡ��ƶȡ�ȻҲ�лʵ��ر�������ְ�Ķ�������������������ǻرܵģ��������������ڸ���������������̡����ֻʵ�����ſ��߶ȣ���֪�������Ѿ�Ϊ�ƶȵ��ƻ�������������
�ƶ���֮���������ʡ������Ժ֮�����ڲ�����������Ҫ��Ա֮��Ҳ��Ҫʵ�лر��ƶȡ��������꣨993��ʮ�£��Բ���Ϊ��֪���£���Ů������ʱΪ֪��ھ��������ˡ����࣬��֪��ھ�������٣����ƶ�������Ȩ���߹��£������ְ���ϼζ���֮���������ˮ���š���7���������꣨1075�����£�����ʯ�ٴΰ��࣬���ĵܵ������ռ��������Ŀ�����£����ְ�ʯҲ�����������ࡷ��260��Ԫ�����꣨1084�����£���͢������Ϊ�������飬����̴ǣ����ԣ�����ة������֮���˳�����֮�ã����൱�رܡ�����گ�����������ࡷ��345����Ԫ�vԪ�꣨1086�����£����������ɷ��������̽������������ǵ�ʱ��������������Ů�����Լ�������ӡ���������˾������Ϊ���������˽�ӷϹ��顱���������ɺ�ά��Ϊ����ִ�������ˣ����ɡ��������ࡷ��384����Ԫ�v���꣨1089��ʮһ�£������ܶ���ּ�����ų��������ˣ������������������Ů���������Ҳ�����������ࡷ��435��Ԫ�v���꣨1091�����£�������Ϊ�������飬���������ʱ��������ة���ʸ�������Ϊ����ѧʿ��ּ��Ԫ�v���꣨1089��ʮһ�£������ܶ���ּ�����ų��������ˣ������������������Ů���������Ҳ�����������ࡷ��435������ڶ�����֮����˵����������Ҫ������Ա֮��Ļر��ƶȲ����DZ����ϸ��ִ�У���ʱ�и�������⡣
6�������쵼�Ƶ��ƻ���
�δ�����Ȩ��һ�������͵Ĺ��̣������͵���Ȩ���е���������ʱ������ζ�ż����쵼�Ƶ��ƻ���������������ת������£���͢һ����Ҫ�����������ij��֣������ƻ������쵼�ơ�Ԫ�v���꣨1089�����£������䷶���ʳ�֪ӱ����������ֻʣ��������һλ���࣬����������������˵��������һ�࣬����δ������ʥ�ǣ�̫ƽ֮�ڣ�δ����Ҳ�������ʵ�δ���������Ȳ���ʹ����Ȩ�أ��˷��佥�����������ࡷ��430��
���ǣ��ڷ⽨�����Ρ���ᣬ�������쵼��ʱ������Ϊ������Ϊ�����ض������ƻ���������ʱ�ڣ������ƶȲ��ϵش��ڶ���ҡ��֮�У���ʱ�ػ���һ����ϵľ��档
���ȣ��δ�û�д��ƶ��϶�һ��������������෴���ƶ�������������֮���ڵġ����ԣ��δ����ܻʵ���������������ڲ��ݻʵ۵�Ȩ�࣬���������������Ȩ���ƻ������쵼�ơ�����ʱ�ڵ�һ����ϣ������ڻʵ۵Ŀ���֮�£�����ʱ�ڣ���ʱ���ݳ�Ȩ��Ū����ʧ�ؾ��档
��Σ��δ���Ȼʵ�������ƶȣ���������Ϊ���࣬���������������䡢��ة��Ϊ���ࡣ��������Ĵ����������ܻʵ����εģ����ǣ��γ��˼����쵼��֮�еĺ��ġ���ʱ����������������������־���¡�����ǰ��չһ���������쵼����Ȼ������ƻ�����Ȼ��Ҳ�����������ڴ��ࡢ��ͬ�����ߡ����������꣨1070�����£���֪���º��Ϊ����·����ʹ�������������£�ʮ���£��Բ�֪���º��Ϊ�����࣬��Dzʹ�����а�֮�������Բ�֪��������ʯΪʷ���ࡣһֱ���������꣨1071�����º�筰��࣬���ʼ�����������У�δ�����س�͢��ְ������ֻ��ʷ��������ʯ���϶��С�
�ٴΣ�Ȩ���Զ�������˵�����в��ɿ��ܵ��ջ�������������������ͨ�������ֶΣ�����ػ�ûʵ۵��������Ӷ�����ػ�ȡȨ�����������������֮�ϡ��ʵ�Ҳϣ����������֮���һ���̶ȵ�ì�ܣ��Ա��ڲ��ݿ��ơ���Щ�ֶΰ������������ԡ����������µȵȡ�
����������ֶ���ľ��棬ʮ�������¼����쵼�Ƶ��ƻ�����ʯ�������8ͳ�Ʊ��ζ����ʱ��˵��
���������Գ�����ǰ��Ǭ�¶��꣬���ʡ����ߡ�κ���ְգ������࣬��������գ�������ʮ�ꣻӺ�����꣬�����գ���P��λ���˹�Ԫ��գ����������ꣻ����Ԫ�꣬���հգ���������λ�����������ꣻ�������꣬���գ������࣬��������������࣬�����������ꣻ��ʥ���꣬�����գ����ļ���λ������Ԫ����ʿѷ���࣬�ļ���������ꣻ�ʵv���꣬���ԡ����岩�գ��Ӽ��࣬���������ꣻԪ�v���꣬������գ����࣬����գ�������ʥԪ���࣬Ԫ������գ�ǰ�����꣩�����������ꡣ
��Լ316���������ʷ���������ֻ��һλ�����ʱ���140�ꡣ��ʱ������Ϊǰ���������Ŀ�ȱ����ɼ����»�һ����Ķ�����棬������ζ�ż����쵼�Ƶ��ƻ����籱��֮���࣬���ڻʵ۵Ŀ���֮�£��ֱ����������������ִͬ������ʱ��Ȩ����Ȼδ�������࣬�����������������������࣬�纫���С�ʷ��Զ�٣�����ʵ�������γ�Ȩ�����õľ��棬�����쵼��ʵ�����ѱ��ƻ�����Ȩ�����õ�ʵ��ʱ����㣬����Լ10�꣬����Լ17�꣬������Լ12�꣬ʷ��ԶԼ26�꣬���Ƶ�Լ17�꣬��Լ82��ڡ����ն���ʱ�ڣ��Ǽ����쵼�Ƶķ������γɽΣ�������Ȩ����ȫ�����ڻʵ����У�ʵ�����㲻��Ȩ����á�ʣ�µ�Ȩ���������õ���ʮ����ʱ�䣬ȫ�������Ρ�������ʱ��150�꣬���ӽ�һ���ʱ����Ȩ����ã������쵼�������������������ƻ��������Ժ������ʱ�䶼��Ȩ����ã������쵼���ƻ�������
7�������쵼�����׳�ƽӹ֮����
�����쵼����ζ�ż��帺���ƣ��������ƶ��£��в��ܡ��и��Ե�������Ҫ�ܵ����ؼ�����ų�����Ծ����Σ��緶���͡�����ʯ��ʷ�Ƶȵȣ��������IJ����й���ֻ������ƽӹ���ţ�ȴ��ʬ����λ��µµ���ա��ڼ����쵼��֮�£��������׳�ӹ��֮ͽ��
�����Ǽ����쵼�ƽ�ȫ��ʱ�ڣ�Ҳ�Ǵ�����ӹ��֮����ʱ�ڡ���P����λѭ�����أ����¶�ˡ������¡ƽ������4���׳�������������Ϊ�������ļ��Թ�ϢΪ�����Աܰ�Ϊ֪�������ļ�֪���������ݺп�˵����ҩʯ֮�ԣ������Ŵ˳�ʮ������������ࡷ��139���������µ����ڡ��������¡��ڼ䡰�����������������͡������ȱ����뿪�����Ժ�����λ����������������ࡷ��155�����������꣨1048�����£���ʷ��ة����ѯ�ԣ�����ִ������֪ij�¿��У�ij���ɰգ�����Ĭ��������Ϊ��͢���£��������������ѭ�ڷϡ��������ࡷ��163�����������꣨1048�����£���֪���¶��Ȱա���ʷ��۰�Զ��ȡ��������ѹ���������֮Զͼ���������ࡷ��164�����εv���꣨1062�����£���֪������\�ա����\������������룣��Ƕ������ɷ������������Ծ�ֹ���Ц��������������Ϊ��ʵ���������ࡷ��196�������ڳ�������䣬��Ϊ��������Dzʹ�����̳�����������ࡷ��303����Ԫ�v�������£���ʷ��ة��Ң��������ʷ������Ҫ��������峼��̫��̫��˵��Ϊ���Թ����������Ŷ�̫��̫��˵����ִ�����������Թ����ǵ���������һ��һ��Ϊ�Թ�Ҳ���������ࡷ��398����
���ڳ��������죬�����Ծ���λ��ʵ����֣�Ω�ķ��������ߣ�δ��һʩ�У����Դ˱����������������ࡷ��56������ƽӹ��Ϊ�������Ȼ�ܵõ����۵��Ͽɣ�������Ϊ�������ԡ����ˮ���š���3�أ��������ļ������飬�����֪������緱�Ρ�������������ν��Ի���������д�����ʹһӹ��ִ֮���Կ���Ϊ���ӡ��������ļ�Ļ���ȷʵ�����δ��������쵼�Ƶ�ƽӹʵ�ʡ��δ���Ұ����һ��Ҳ�����Ͽ�ƽӹ�ع���ߣ����Ծ���������Ϊ������֮�Աǡ�����ʷѧ������˵�����ҳ����ظ����ߣ��������졢���������������ļ�����������˾���⡢������֮Ϊ�ࣻ�Ƹ����ߣ���������ʯ�����Ӻ̾������롢�ػ�֮֮Ϊ�ࡣ�����Ч���������ˣ����Ƹ����߳ϲ����ø�����Ϊ��Ҳ���������δ��¼ǽ��塷��6�������������˼�����������ư�Χ֮�£�����Ҫ��������Ϊ����ҲҪ����ĥȥ��ǣ������ڣ��۶ϳ�������������ѡ����ԣ��������ڱ��ء�ƽӹ�������ֲ�������ְ��ļ����쵼��Ҳ��Ī��Ĺ�ϵ��
�δ���Ȩ��ǿ�������൱�̶��ϻʵ�Ҳ������ȡ������������Ӧ��˵�����뼯Ȩ�����Ի���ת��һ�ֱ�־�����ͳ���߲���ƾһ��֮ϲŭ��������ó����������ȥ�������������ˡ��ڡ����Ρ�������������һЩ��������ݣ���Ȼ��һ�������������������ġ��ij���������ʷ��չ�����ƣ��δ��ι����������Ĵ�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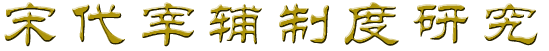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