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δ���Ȩ֮ǿ��
�δ������ж��Ȩ������ǰ����Ⱦ����������˻�����С�ˣ���һֱ��һ����˷��������⡣ʷѧ�����������ֽ�Ȼ�෴���������һ�ֹ۵���Ϊ�δ�����Ȩ��С�ˣ��δ��Ѿ�Ȩ�ָ�����Ժ����Ȩ�ָ���˾�������Ժ�����������֮Ȩ��ͬʱ�����Ҫ����̨�ɵ����ܼල�������������ַ����֪���£���ǣ�����࣬���ԣ��δ������Ȩ���Ѿ�ή���������ѿ��ĵز���Ǯ�µġ����δ���Ȩ���ͳ����֡��δ�����Ȩ�����Ĺ۵�٣��Ժ�ʷѧ�����۴�����Ϯ����۵㣬���ɶ��ۡ���ʮ��������������ѧ���������ű����δ���һ��ʷ�Ϻó���ȫ�෴��������������������ڡ���������¼�о������������ܽ�˵�����ڲ������Ȩ�����У��δ�����Ȩ�ܵĿ��������κ�һ����������Ҫ�������������������̨��������������Ⱥ����ʵȨ�������ݵģ����ʵ��ڶ�������£�������һ�����˰ڲ�������ż����ѡ��������䷲���������γ�������Ȩ֮�ó���Ȩǿ���Ľ��ۣ����γ�������Ȩ��̽��˵���������Ȩ�����������ˣ����Ǽ�ǿ�ˡ�����
����������������Ǵӻ�Ȩ����Ȩ�����ĽǶȹ۲�ʷʵ���Ű��������Ĵ�����ͳһ�ĽǶȿ������⣬��Ϊ�δ��ʵ۵����ͳ��Ȩ��������������Ȩ���ศ��ɵģ����δ��Ļ�Ȩ����Ȩ��������ǿ��������������ܾ������ԡ��������������˵�������º�����ͬ�����£���Т֮�ϣ�ʼ����һ�������������͵Ȼش𣺡���ΪԪ�ף���Ϊ���ţ�����һ�壬���в�ͬ���Ķ��ܼù����������ա����������ࡷ��43���δ�����������������ʱ����ȷʵ�����������ˡ�����һ�塱�����ԣ����ߵĵ�λ��Ȩ�������Լ�ǿ���δ�����ƶ����������������ǿ�еĻ���֮��ȴ��Ȼ�ܴ������ٶ��꣬��Ҫԭ��֮һ���ǵ����ھ�����ͬ��ͬ�¡���������ʷ�ϣ���һ��ʮ�����Ե���ʵ�����λ�����û�к��������ݡ����ҡ��¹���Ȩ����֮�·�����ֻ��Ȩ��ܿջʵۣ���������������������ʵ������ķ�ʽ֤ʵ���δ���Ȩ֮ǿ����
�����δ���Ȩ��ǿ����˥�������������һ�����⣺�����ĸ�������Ϊ����ϵ����Ϊ�Ƚ϶�������ǰ�ڣ�ʵ��ة����ĸ����쵼�ƣ�ة����Կ����Ա�����������ʹ����Ȩ��������ѡ�ó�͢�͵ط�������ͳϽ�ٹ٣����ܿ����ϼƿ��Σ��������ᣬ����ٹٳ������£��ⲵ����ȣ��������гͰ�ǧʯ���ҵ�̫�д����м���Ա������ʷ֮��Ķ�ǧʯ��Ҳ������ն���롣����һ�ε�������ȣ��δ�����Ȩ��Ȼ��˥���ˡ���ͻ�������쵼���õ������Ƶ����Ƶ���ʡ�ƣ�����������ļ����쵼�ƶȣ������쵼���е�ÿλ���࣬Ȩ�ƶ�������˿�������ʱ�ڵ����ࡣ�����δ���Ȩ��ǿ�����������༯���쵼�Ƶķ�Χ�ڣ���Ҫ������ʱ����ʡ�ƶ��µ�����Ƚ����ó��Ľ��ۡ�
ȫ���ű�����ʷ�ϣ����ܷ����δ��ڲ�ͬ��ʱ�ڻ��Ȩ����Ȩ���õ�ǿ��������Ȩ�������ͣ�ȷʵ�����˻�Ȩ������һ�Ŷ��ۣ�����ǰһ�����ռ������λ���γ�����һ���������ȱ����ƾ���仯����ʷ����
��һ��
��ʿ���������
�δ���Ȩǿ���������ԭ���ǵ�����������ʿ��������µľ������r������˵��������֮���Σ�ʿ���֮����Ҳ������֮������ʿ���֮���ߣ�Ω��ΪȻ����Ω����Ů�������ݡ����ҡ�ǿ��֮����������Ϊ������ࡣ�������й��Ļ�ʷ����516ҳ��
�δ����뼯Ȩ����ǿ����һ��Ž�ʷѧ�綼û�����顣�δ����뼯Ȩ��������Ȩ����Ȩ������ɲ��֣�������һ�������л���������һ��ì�ܡ���˫����ͳһ��ռ������λʱ���κ�һ����ǿ�����Ƕ���һ����֧�֣���˫����ì���Ա��ֳ���ʱ���κ�һ����ǿ��������������һ��Ϊ���۵ġ����߹�ϵ��һ��ģʽ�ǡ�ί����ɡ������ʵ�ί�ι����������࣬����ɹ������У��ʵ��������վ���Ȩ�����ͳ��Ȩ����������������������Ȩ���ڳ�̬ģʽ֮�£���Ȩ�ij�ַ��ӣ����ǻ�Ȩ��������֡�
�⽨ר�������Ȩ���ṹ�ʽ������ͣ��ʵ۱㴦�ڽ����������⣬����֧��Ȩ��������Ȩ������ת�����ǣ���Ϊ���壬�ʵ۵�������������ʱ�䶼�����ģ�������Ҫ����ijһȺ���ij����Ⱥ�壬ί�����ǹ�ͬ�������£���ͬ���Ȩ�����ġ�������꣨630������̫�ڶ����r�������ĵ�ʱ˵�����ĵۡ��������ΰ�˾��ÿ�½��Ծ��ϣ�����������Σ�δ�ܾ���������������֪���⣬���ֱ�ԣ��������£�Ω����˳���ѡ������������Ҫ����1�����塷����̫�ڽ�����Ϊһ����ʷ�����ѵ����ȡ���δ�����Ҳ��ʶ���������������˾����ɶ���Ҳ�����������ࡷ��86����ʷ�ϣ��ʵۻ��������ڳ���������ͬ�����ף����������չ��ݣ����������ߺ���������Ȩ�������зֱ���ֻ¹١����ҡ����ݡ�������Ȩ�ľ��档
�δ�������������̷�˼��ʷ�ľ����ѵ����������ʿ��������¡���ѡ��ʿ���Ⱥ����ΪΨһ���������еĶ��������ι����룬�̶�Ϊ�����ڼҷ�����Ϊ�����ʵ�����ѭ����̫�ڶ�������P��˵�������¹������������������߹��ң��Ը����á����������ࡷ��26���λ���گԻ�����˾����빲���ߣ�Ω�������������λ�Ҫ��ְ�١�1֮32��������˵���ʵۡ����볯Ϧı���ߣ�����ִ�����ѡ���������������¼У������7�����岩Ҳ����������˵����Ϊ��ʿ��������£��������������Ҳ�����������ࡷ��221����ʷ����Z������˵�����������빲�������ߣ�Ωһ��ִ��֮�������������ࡷ��285����˾�������Ŷ�����˵���������Ա������빲����֮���ߣ�Ω����ִ�����ѡ������ˣ�����²��Ͷ������ɸ��������ˣ��������ܱ����¶��͡��������ࡷ��370������������ʷ�������и��������Ϊ����������������������Ҫ�ڸ��������������ࡷ��176������һ���ϣ��δ��ʵۺ�ʿ����Ѿ���ɹ�ʶ��
1����ʷ�ķ�˼����������Ļ������ߡ�
�δ��ʵ���������ʿ��������¡��ľ��ߣ�����Դ�ڶ���ʷ�ķ�˼���γ�����֮ǰ���й��⽨����Ѿ���������ǧ��ķ�չ�������˷��Ĺ���ʢ˥����֮�����ѵ���������ǵĵ����Զ��á���ʷΪ�������ƶ���ʵ���еĽ������ι��������ߡ���̫���ԡ��Թ�Ϊ������֪���档�����������顷��97��κ������������������ʶ�ĸ�����
��
�������䡣
�����ǡ���ʷΪ���������Ƕ�ʱ����������һ����������ʷ��������δ�ͳ������Ե��������й�ǿʢ���١����������Ĵ��Ƶ۹�������۹���������������ս���Ұ���ķ����ѵľ��档���������ʮ����������Ȩ����Ƶ�ԣ����Һ���㷽�����ҵ�̨��������ԭ�����������˰��衢ӵ�����ء���Ȩ���������һ������̫���������������ۼ������������ɣ��δ�ͳ����������ͬ����һ�������
�δ��Ľ������ι��������ߣ���������������������ʷ�����ѵ���������ƶ��ģ�����������ϮΪ�����ڼҷ������γ������ٵĵ�һ���������������Ϊ�����������˹��ҷ��ͣ������������͡��������ᶼָ��ʹ����������Ȼ��ijһҹ�ܵ��������ߵ�˽ۡѰ����̫��֪����ʮ������������ᶼָ��ʹ���ʬr����֪����Ѧ����˽���Ƽ���ѡ�����ܾ�������ϲ���գ���Я����ʿ����������������ࡷ��4��Ȩ��������˾������ѫ�������������Ů������Ϊ֮���š����������ࡷ��6����Щ��������û���Ļ�������Ϊ�����ʼ��̫����������˵������������Ű�������������ѡ�峼�����߰��࣬��֪���ݽ�̰�ǣ���δ���䳼һ��Ҳ��������̫����Ϊ����ε��ij�ҲҪ�����䳼�����ԣ�̫��һ��ǿ�����������ö����ˡ����Լ������ࡷ��7������Ȼ��̫���ǽ����θ���������ʿ���
�δ����������ȶ�������߾���֮�ģ����ȡ��ϵ�з�����ʩ�����������Ժ���½ڣ����������һ�����ǡ��������䡱�������������ʿ����ڸ��ָ�λ��ί����ʿ��������Σ������ط�ͳ��ְ֮�������������������Ժ����Ҳ��������ʿ�����Ρ���̫���Ժ����γ����ij���ͳ���١������佫�Ķ�����������ʱ����ֿ���������Ϊ������֮��������˵��������֮������������Ϊ��˧��ר��һ���������ij�Ϊ���ԣ�������֮������Ϊ�ܹܣ���������Ž��٣��ܽ��ƣ�����ս�أ�Ψ��ָ�ӡ����ҳ�ƽ���ж�ʮ���꣬�������£����������߳������Ҳ�������������������顷��238���ν����������������γ����������̵����£����������ȻҪ�����غӡ��ػ����ؽ���˧�������ij�Ϊ����ʹ�����������ܹܣ��䳼һԱΪ֮�������������¡���������ʷ����167��ְ��־��������ʹ��ְ֮���Ƕ������ij����Σ�����������µ�һ�ڡ�����������ʱ����˵�������Ҽȶ��ķ�����ǰʧ��������顢�۱�Ҫ������ܶ��ⷽ�����ij���֮���䳼��ȥצ����ĥұ׳�����״�����֮�䣬���ҿ�Ȼ�Խ����ء�Ȼ�����°�Σ��ƣ��������ij��������������ļ�����87������ͨ����
���������䡱�������ߵĹ᳹ʵʩ�����δ�������һ���������˵Ĺ��������Ƚ�˵����״Ԫ���ڣ��佫����ʮ�ָ��ļ�����ǿ������Į�������ͻ�����̫����������ɼ������������ֹ��顷���֣����ι���Ϊ̫��ʱ����̫����������̫�������������������ڸ��ڡ�Т�����������ϳ������佫֮�ң�������������˵�������ǽ��֡���������ij��ż�¼���Ҽ�����
��
���Ĵ�ʩ��
�δ����������ij��������ι�������һϵ�е��������ʿ���Ĵ�ʩ��̨�����ȣ��δ�ͳ���߸ĸ�ƾ��ƶȣ��ؿ����˵ķ�չ��·���δ��ƾٳ���ȡ�����ŵ����ƣ������ײ�������ӵܶ�������Ӧ�����ˡ�ͬʱ�ϳ����������ƶȣ������ַ⡢��¼֮�����ϸ����ƶȣ�����ȵط�ֹ�˿����������˽�����Ա�֤�ƾٿ����С�һ���Գ���Ϊȥ�����Ĺ�ƽ����ԭ���ʵʩ��¼ȡ����Ҳ�������ӣ�������ʱһ��¼ȡ����1638��֮�࣬������ʱ�ֹ涨һ��¼ȡ��400��Ϊ�ޡ��������ӵ��ԣ��ɻʵ��������֣������߾�Ϊ����������������ҫ�ޱȡ���ʿ���ڣ����ͺ��ڹ٣���Ǩ���졣����ʷ����������������133�����ƾٳ����߸ߴ�123����ռ92%��״Ԫ���ڣ�������ҫ�ޱȣ��ٻ�����ָ�տɴ���������ƽ���꣨1002��������������Ԫ����Ϊ�¿�״Ԫ������ѧʿ�����DZ��������Ц˵����״Ԫ��������һ�����Ų�����������������¼����14��������ʫӽ״Ԫ����˵����������е�һ�ɣ�����ƽ�������졣��������իҰ�ˡ�״Ԫ����
��Σ��δ�ͳ���߿����ʿ����̫���������ı�������ɱʿ�������������ߡ�����û����ɱ��֮�¡�����Ȩ��֮�����ӻ�������Ȩ�����ϡ���͢����Ȱ��л���Ȩ�������¼���Ȼ��ɱ��֮����Ȼ���١��δ������вŻ�����ѧ֮ʿѡ��ݸ��̷��ڻʵ����ң������Ա����ʣ���������ۣ���У�ţ���֮Ϊ�١���������ʷ����162��ְ��־����
�ٴΣ��δ�ͳ��������������λ��Ȩ�����ĵ�����������Щ��ٺ»ʮ�ַ��Ϊ��������Ŀ���࣬����ٺ������ٺǮ���´͡�»�ڣ�����ٺ������ְǮ�����ˡ����������˲�Ǯ����Ƴ��ϡ�н��̿�Ρ�������֧������ѫ��������ְ��ȡ����ԣ����������С�����»֮���������ڰٹ�Ω���䲻�㡱֮˵�١�
��
������
��̫�桢̫�ڳ������飬����ȱ����Ҫ���Ļ���������Ϊһ����������������ȷʵ���н�ΪԶ���Ŀ�⣬��֪�����ϵ����£����������¡��ĵ������ѽ��������ȹ̽�ɽ���ι�ƽ���µ���������������ʿ���̫��ǿ��������������ˡ����Լ������ö��顱�������ڴ������䳼��������ͨ�ε���
������ʷ����3��̫�汾�͡�����̫�ڼ�λ��������ƾ�¼ȡ�����һ��̫ƽ�˹�������������ȡʿ500�ˣ�������̫�泯17��ȡʿ�������ڡ�̫�ڽ��ʹ˾���ͼʱ˵���������Ƴ��й����壬��ʮ��һ������������Ρ�������ʯ�������5����������������ԺΪ����Ժ�����в�ѧ֮ʿ��߬��̫ƽ��ǡ�����̫ƽ������������ԷӢ�����ȴ������飬�����Ļ�����̫�ڳ���ʼ����ʿ����������ʿ���Ѹ�ٻ�ó�͢���ã�����ӿ����������������Ϊִ�Ƴ�������Ҫ�����������δ�����λ�ʵ����ڻ�����Ȱѧ�ġ�˵������������ǧ���ڡ������������лƽ��ݡ��������г�������ء�����������Ů�������������汦�����ף�����һ�в����ǿ�ͷ��ŵ����ʵʵ���ڵ���ʵ�����β���˵��
�������ˣ��������Ĵʽ�������ʿҲ������֮������ʿҲ��Ǯ��֮˾����ʿҲ���߷���˧����ʿҲ������ת��ʹ����ʿҲ��֪�ݣ���ʿҲ����������������22������ҪĿ����
�δ���ͯ������ġ���ͯʫ����ƪ��˵����������Ӣ�������½̶��ܡ�������Ʒ��Ψ�ж���ߡ���̫�桢̫�ڶ�����ʿ���Ŀ������Զ���ij��У��Լ������˵ķ��������γ��ˡ��������䡱�Ļ������ߣ��ݻ�Ϊ���ˡ�����Ϊ��˼����ʶ����������һ������ʶ��������Ľ����������ѧ����֮����ʢ����Ϊ�����ߣ���������ܲ���Ϊ�̣�Ϊĸ���ߣ����������ѧΪ�衣��������ի��ʡ��ıʾ�5������μӹ��ٵ������������ӣ�̫�ڼ�λ��һ�ι���ʱ��977��������5300�˲μӿ��ԣ����ڼ�λ��һ�ι���ʱ��998����������2���ˡ������˳�֮��ҹ�С�ʫ˵�����´嵽���̵ƻ�֪���˼�ҹ���顱������֮ʢ��һ���ڴˡ�
2��Ȩ���������磬��β��֮�ݡ�
�δ�ͳ������������ʿ��������¡��ľ��ߣ������ڶ�ʿ���ײ㱾�ʵ���ʶ��������ʶʹ���Ǽ���ʿ���ײ�ľ��Կɿ��ԣ��������Ⱥ��ֻ���������ң��������ǵ��������á�
��
�����º���������Ȩ��
�δ�ʿ���ײ����ɳɷ֣���ǰ����ȣ��Ѿ����˸����Եĸı䡣�����Ժ��ؿƾ�ȡʿ��Ϊ���²�ĺ���֪ʶ���ӽ�����;����֮�š�����������֮��ʿ�廹���൱���������ǶԿƾٿ���Ҳ��һ���IJ�����������Ϊ��ʱ���Ի�û�в�ȡ�ַ��ƣ�¼ȡ��ֱ����Կ����ġ��δ�������ʿ��������Ա��ٶ���仯������ĩ�����ɨ����ʿ��������Ȼ�棬���Ͽƾٿ��Թ�ƽԭ��ľ���᳹ʵʩ���������²��֪ʶ���ӳ�Ϊ�ƾٿ��Ե���Ҫ�����ߡ�
ͨ���ƾ�ȡʿ������Ҳ����ʶ�����²�֪ʶ���ӽ�����;���ڹ������������з�����Ҫ���á�Ϊ���ܹ������²�֪ʶ���������˽�֮·���δ���������Ϊ�����ڲ�ͬ�̶���Υ���ˡ���ƽ��ԭ���翪��Ԫ�꣨968�����£����ֳ�ּ�b֮�������Խ�ʿ�ϸ����е�����̫�桰�������鸴�ԡ�����گԻ�����Խ���˷���ʳ»֮�ң�ί�������ţ�����ԡ����������ࡷ��9��̫��Ӻ�����꣨985�����£����Եý�ʿ179�����ٵ����318�ˣ���������P֮�����̡���֪����������֮�ӵ��ɺࡢ����ʹ����֮�ӷ�����֧ʹ������֮�Ӵ��ʣ��ٽ�ʿ�Խ���ȡ���Ի�����˲��Ƽң���º���������������������ν��Ϊ��˽Ҳ������֮�����������ࡷ��26�����¶��꣨1005�����£��������ر�گ�����������������������µ����塢������Ϳ������������ࡷ��59�����������Ԫ�꣨1008�����£������ر�����ν�Ƽ��ӵ��ߣ��������ԡ��������ࡷ��68�������ھٲ����ס����������£����ο�ͨ���ַ⿼�Թ�ƽ������ӱ�ߡ�̫��Ҫ�������ӵܸ��ԡ�̫����˵�ġ�ν����˽��������Ҫ��ġ��������ԡ����ǽ�ڣ�������ԭ����Ϊ���º������������·��ͬʱ���ơ��Ƽҡ����γɡ��������꣨974�����£�̫���ڵ���ʱ�Ծ�����˵�������ߵǿ���������Ϊ�Ƽ���ȡ�������º�֮·������νҲ�����������ԣ��Կɷ���ˣ��������֮���ӡ����������ࡷ��16���ѵ�������������˵��һ�������
�ڵ���������ʶ����֮�£����γ��ڵĴ�ٹ�����ӵ����������Ҳμӿƾٿ��ԡ��硶ʯ�������5�أ����������ʵ�ֶ�ӣ�����֪�b����ǣ��Դ��Լƣ������ԡ���»֮�Ҳ����뺮�����������ߣ��첻�Ҿ��ԡ�����8���أ������ƣ�ִ���ӵܶ����Ӳ��Ҿٽ�ʿ���й�ʡ�����Ҿ͵����ߣ���ʱδ�к���֮��Ҳ����
������;����Щ�����²��֪ʶ����Ҳ��Ϊ����ʿ���ײ�����岿�֡���̫��ʱ�����������ͣ�����ƶ��ѧ����Զ־�����������킠����Ϊũ�ң��������ġ������ڡ�����ʱ�������������ٹ£������ٸ���Ԫ����ѧ������������Ϊ�Ĵǡ������������͡�������£�ĸ���ʳ�ɽ���ϡ���ŷ���ޡ���ƶ������ݶ����ѧ�顣��������ˣ����������С����������ˡ���ʷ������������Щ�˶������ƾٽ���ٳ���λ���Ժգ���Ϊ���ҵĸ��Ĵ��δ�ͳ���������κ��и����µľ�������ײ������ʿ���
��һ��������ƶ�����ŵڱ���֪ʶ�����ܹ������쵼���Ľײ㣬�������࣬�����縺���ι�ƽ���¡�����ʷʹ������ȫ������͢�Ĵ�����Σ�������Ƕ������Ҹж����¡�����Ч�ң���ʹ��;������ۣ�Ҳ���IJ��䡣�������ڡ�����¥�ǡ����������ʿ�����롰�����ǣ������ǡ�����������֮�Ƕ��ǣ�������֮�ֶ��֡������֡����˽��ǡ��������Ǻ��֡�����ʶ��Ϊ�δ�����ʿ�����������徫����ǰ��ʿ���������£����߶�������������ʶ�кܴ�IJ��졣�����ͱ��˾������������ǵ�Ϊ�ٺ㿪ʼʩչ�Լ������β��ܺͱ�������������͢���飬���Ա�������ʮ��IJ���Ŭ����������������������и������������������Σ��ĸﳯ������������м�������������Ϊ���Σ����븻����ҹı�ǣ�����̫ƽ�����������ࡷ��150�����������¡���Ȼ�ܿ��ʧ���ˣ�����û�иı䷶���͡����Ǻ��֡���һ�ᾫ�����ͻ�����ؽ�У����ٺ���ˡ����������ʹ����ĸɥ��֮�ʣ�Ҳ������һ��֮�ݶ�������֮�ǡ�����������������8���������ͼ�ֲ�и����������ġ����˽��ǡ��������Ǻ��֡��ľ����δ�����ʿ���㷺�ؽ�����������Ϊ����ѧϰ����ʵ��ģ���Ӷ��ı����������ʿ���ǰܵľ��档����ʷ�������ʹ����Է����͡�ÿ�м��������£��ܲ�������һʱʿ�������з�ڣ������ͳ�֮��������Ҳ�����������͡��������ڣ�����ʿ���������������ࡷ��129��֮������ŷ�����ǡ����ʸվ���������Ϊ���������ǰ������֮���ˡ���������ʷ��ŷ�������������ҵ�Ȼ�������ָм��ܷ����ҳϣ����Ҳ�ᶨ������������һ������ʿ�������ĺ;��ġ�
�ر�ؼ���һ������Щ����ʿ����������û������������Ϊ��ᱳ������Ҳû��������������ʵ����������ʢ˥�������ڵ������У���ʹλ���˳���Ҳ�����������������DZ����в������������˻¾������������Ƕ����������Ĺ������ģ��Ի��ҵ������Լ�ǿ������һ�������⣬�Ͳ��ٶԳ�������Ӱ�죬������ǻʵ۶��ϳ��Ķ��ݣ����������ڳ�͢�в�������̫������θ���������κ���������ŷ�����ʿ���ײ����Ϊ���ྶͥ������ʱ������л�����ҵ�������������ҷ�ͥ����ʹ�������ų�������ͽ������͢����Ҳ��Ӱ�����������������
�δ�����ʱ���Գơ������һ�����������������Ƕ��Լ����ݵ�һ�����ϡ����������ֳ�����Ȩ����Ȩ�ƣ����ǻʵ۵�Ȩ����Ȩ�Ƶķ�ӳ�������������࣬�Ҷ����ʮ�꣬����ν���Ժգ�Ȼ�����Ծ��裬������ӵ�˵�����᱾������ż�����ˣ��ܳ���֣��̵�����������˽��֮�£�����Ԥ�ɡ����������ࡷ��29��Ӣ�ڼ�λ�������£����Ҵ��½�ȡ���ڶ�������ʱ���ǵ�Ȩ������ν����Ȼ��ʱ�IJ�֪����ŷ����̫��˵�������������������ٶ������������⣬����˭�����ӣ����������ࡷ��199��Ԫ�v���꣬˾�����Ƽ����岩���³������࣬������Ϊ���岩�С�����֮������˾����绤˵������Ω�岩��һ���������������б�Ȩ��������η��Ҳ����ʹΪ�࣬����һ������֮��ֹ����һѧʿ�����Դ�ͷ������ȳ�����һƥ�����������֮�����������ࡷ��368�����岩������Ϊƽ�¾������º����Ϲ�������ʿ�������������գ�����Ի����̫ʦ���ݡ���������л������ȥ��ʱ�����ʮ�ӡ������������ż�¼����14������ʱ������ܽ����ǵĽ��˳������ø�ν�������˵�����ܱ�һ��������λ��»��������ã��Թ����ߡ�����һ����λ��»���Ҷ�֮��ȴΪһ����ֽ������Է���Ү����
��㇡�Ĭ�ǡ������ض�ν������̺��е����ԡ����ڼ�λ���꣨1022����̫��������������ν������Ȩ������������ʱ�IJ�֪��������������ν�ļ����������顣����ȴ��ƶ���̫������ν֮��Ȩ��˽������̫���ŭ����֮�������죬��ν�ͱ����⣬����Զ������ν����ı��թ����������������ĩ��Ϊ���࣬Ȩ��һʱ��̫���µ�����Ƭ�Ա��ʹ�����е�Ȩ�Ʊ����߽⡣�ɼ��δ���Ȩ���أ�ȴ��ȫ�����ڻ������С�
��
���������۶ᡱ��ʱ����
�δ�ʷʵ�Ѿ����֤���˵����������ȷ�ԡ�����ѧ����Ӻ�Ƶ��������Խǰ�˵�ʢ�£���һ�ǡ��������ĸ��������������ż�¼����18������û���������������������λ�λ������в�����������DZ�һ���١��ٶ��������������������߸����������ڲ���˵����ب�������ٶ���ʱ�䣬ʼ��û��һ�������������͵�������в���λ�λ���ȹ̡��ձ�ѧ�߹����ж����δ���Ϊ���������۶ᡱ��ʱ����˵�������Ժ㿴�����۶��ˣ����ӵĵ�λ�dz��ȹ̡��������Ժ�˵��ֵ�����ã�Ȼ���δ��ĸ�����ȷ�ġ��δ�����û�лʵ۱���������������������Ϊ�������������������¼�������άϵ��֧������������Ҫ������������������Ϊ������ʿ���������
�����ν�320���������ʷ�����У����й����������ڡ���͢���䡱�Ĵ�Ȩ��һ��ʧ�ܣ����γɹ��������ι�͢���䶼���������α������ҵ����£�ʿ������������������ȹ��������ҵ����á����Լع�һ�¡�
��һ�����䷢���ڽ������꣨1129�����¡�ʱֵ�϶���ʼ�����ڻ�λδ�ȣ�ͳ�ƹ��縵����Ӫ�Ҿ�����ͳ�������������ͱ�����������Ժ�������ڳ����µ�ԭ���ʱ����ҡ���һ�����ҽ�һ���¾ͱ�ƽ�������¸��ڸ�λ������֮����Ѹ�ٱ�ƽ��������������ʤ�ǵİ��ŵ��ȣ��⿿�ſ������úƹĶ���֯���������������һ�ε��͵������������š�����������ҵ�������ʿ�����ʤ�ǡ��ſ������úƵ�����ƽ�ҹ����з����˾����Ե����á��º�ֻ��ʹ�ʵ۸�����������ʿ��������˸���һ������������������������ſ��������ҡ���������˧�ı�Ȩ�������Իٳ��ǣ���ɱ���ɣ�������ʵ�϶��ǻ���֮һ��
�ڶ������䷢�����������꣨1194�����¡����ڴ��������꣨1191��ʮһ��ʼ�������ӳ���ʧȥ�������Ļ����������ܵ��ʺ���ڳ���һ�����ơ�����Т�ڷ�Ŀ����ȻΥ������Т�����¡���ԭ��ʧȥ�ʵ��ι����������塣ì������������������Т��ȥ�������������ڼ�ֲ�ִɥ������Ұ����������ԣ���������������ة���������뾩�ǣ������˴�������������������ڣ����������˳�Ӧ����ıΪ�䡣��������������������Ŀ��Ҫ����3����̬�ķ�չ�Ѿ���в��������λ���ȹ̡�֪����Ժ�������ȶ�������̫��̫��ʥּ�����ֻ��Ӽ�����λ�������Ϊ̫�ϻʵۡ�������˵����ȶ�������תΣΪ��������в�������������ⳡ�粨֮�У���Ȼ������ʿ�����Ȩ�ŵ���ƽ�ȹ��ɡ�
���������䷢���ڿ������꣨1207��ʮһ�¡�����������ԪԪ�꣨1195����ʼר�ó������������꣨1206�����·�������ս���������в�֪��ʱ���ƣ����˽����˫������֮�Աȣ�û�г�ֵ�սǰ���������ý��ñ���ðȻ����ս�������ԣ�ս��һ�����������ξ��ӱ�ȫ�����ܣ�����ɹ����ӣ��������ơ������вֻ�֮��������ͣ�����ִ��Ҫ�ú�������ʼ����ͣ����������߳�ŭ��������עһ�����ٴη���ս����������û�п���ս���ʱ���ս���ij�����Σ�������ҵĵ�λ��������ʺ��볯��������ʷ��Զ����λ��֪����Ǯ����������ı���䣬��ɱ�����У�������ս����������䲻�漰��λ���棬ìͷֻ��Ȩ�������У�����Ľ����ƽ�Ⱦ����������ġ�
������ļع������������������ʿ��������з��Ӿ��������ã�ʹ��̬�����������������ҵķ���չ������ʷ�������������Ļ�λ�۶������Ȼ��ͬ���������±䶼��˵���δ�����ѡ����ʿ��������¡�����ȷ�Ժ�ʿ������δ������ӵ���Ҫ�������á�
���⣬������Ϊ������ʿ�������������������ν�δ���͵Ĺ�͢�����͢Σ����������ѿ״̬֮�С�̫��������ȷ�����ڻ�̫�ӵĻ�λ�̳�Ȩ��̫�ڲ�Σʱ���¹����̶������ڲ������ݣ����֪��������䡢֪��ھ������ı�����������ֳ���Ԫ���Դ�֮������̫��ͬ�⡣�����������ʼ����У����ϣ����ڣ������ԣ����б䣬�������顮���֣���������Ȥ�����̡���̫�ڱ����̶����������ٶ�����������ǰ֪��ı����窼̶���ʹ�����x��̫���ȴ�īگ������֮��ؽ�빬����νԻ����������ݣ������Գ���˳Ҳ�����κΣ�����Ի�����ȵ���̫����Ϊ���գ����ݸ������飿����ĬȻ���ϼȼ�λ����ƽ�����²��ݣ���������������ӣ�Ȼ�ף���Ⱥ���ݺ����ꡣ���������ࡷ��41��������˱��佱Ϊ�����²���Ϳ��������һ�¾���Ȩ�Ľ�������У�ʿ���������������������á��֣�Ӣ�����ⷪ��̴�ͳ�����³ɼ���ʱ̫����ϴ���������Ӣ�ڡ��ٴ��ij��ȣ������¹����ٶ������Ҷ���ߣ��˹�Ϊ���䣬�������϶�������ຫ��ÿÿΪ����ȣ��ֺ���������ʹ���ֵ����ȶ�����������ࡷ��198������֮�������ڼ��ÿһ����Ȩ���棬����������������������ʿ����������ƽ�Ⱦ��ƣ�ƽ�����������������֤���ҵľ��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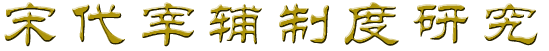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